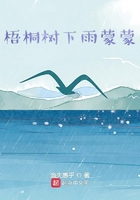清远镇东,有路一条,宽阔坦荡,惯称大道,大道路旁有亭一间,人曰不留,可挡风雨。
清远镇北,有塘一洼,方圆半亩,名唤懒荷,懒荷溏上石桥一架,经年无名,日久斑驳。
清远镇西,有林一片,葱郁深远,谓之四方,四方林中有泉一眼,号之雾沼,四季常温。
清远镇南,有山一脉,巍峨连绵,取名翠峦,翠峦山下有庙一座,尊为八苦,百年有余。
八苦寺内师徒三人,方丈法号引灯,大和尚七盲,小和尚富贵。
1
野果香,山花俏,山坳路长,行人喜笑。
走了一天的山路,却是比那乡间小路还要人多,一路也不知遇见了多少修佛之人。每每见到三人,或赠予瓜果,或问询行礼,闻知路途不熟,还会送上一程,可见此地佛学之盛。
日斜黄昏,百鸟归巢。
“当当”一阵钟声传来,悠扬回荡,良久不散。
抬眼望去却只得满目繁林,古木高耸,见不得寺院丝毫。
“师父,中原大寺的钟有多大啊?这般大声响。”富贵不由好奇。
“和咱们大殿的金佛差不多大小吧。”七盲想了想,又道,“只是不知这些年他们还换没换过。”
“那得几个人撞的动啊?”富贵摇头不信。
“好像是五人一值。”七盲拿过水袋递与引灯大师。
“五人?!”富贵不免又摇头,他们庙子一共才三个人,别人的寺庙僧值便要五人一组,那这中原大寺里是得有多少人啊!
然而不等七盲答话,富贵已是信了。
转过拐弯,就看得一条阔路,石阶百级,直通山上,长目远眺,一座古刹立于正上,山门之阔近乎三丈。
“方丈,师兄,小富贵!”山门下一和尚,逆光而来,声音之大,有若洪钟。
“一时师叔!”富贵忍不住叫了出来,一时哪里还是此前模样,皮肤黝黑,身体壮硕,一双黑豆似的眼睛很是有神,瞧见三人止不住地笑。
“一时为何在此?”引灯大师问询道。
“小僧估摸着你们这几日便要到了,无事时便来此迎候,三位路上可辛苦?”一时扶住引灯大师道。
“我们倒是不辛苦。”富贵想起来路,难免心下翻涌。
“是众生太辛苦。师叔,世间苦,不止八苦。”富贵说得郑重,倒是把一时说得怔了住。
“见得众生之苦,你这一路也不算白行。”一时点头。
“啪!”一戒尺拍在富贵头顶,声音清脆。
“师父!”是七盲。
“你也见了天地之美,世人之慈悲,各色之美食,怎么这会儿却看不见了?我佛让你修行,不是让你修苦!”七盲正色。
富贵咬了咬唇,豁然开朗,紧随引灯大师踏步拾级而上。
空留一时对着七盲,长出一口气,郑重行礼道:“师兄依然好修行”。
“不知师弟过得如何,武僧院可好打理?”七盲笑问还礼。
“一如从前,不如从前。”一时答得模棱两可。
“此前可是彼前?此二者可是同义?”七盲问道。
“非也,非也。”一时摇头,伸出左手做了个请的姿势,快步向引灯大师追去。
2
僧舍之中,富贵犹自在门前整理,众多师兄围拢过来。
“富贵师弟。”为首的沙弥憨声问礼。
“诸位师兄好。”富贵慌忙起身回礼。
“师弟远道而来,小僧有一问题想请教。”那沙弥圆脸圆身,声音憨厚。
“不敢不敢,师兄何事?”富贵问道。
“什么是禅?”沙弥问罢,微微含笑,身后一众僧人皆是无声,静待富贵作答。
富贵却是垂首,只轻轻吐了一个字:“是。”
众人仍是不语,却是表情各异,有大惊,有含笑,有不解,有豁然……
禅在人心,禅在万物,故而什么都是禅。
3
月近圆,星若明,银河暗隐。
富贵抚着肚子叹气。
“饿了?”七盲对着秋月仰望许久问道。
“嗯。”富贵腹中一阵咕噜。
“你的花生和干粮呢?”七盲四下打量,客舍前既无长廊也无花草,只一片石板空地,靠墙处一个小亭,亭中一桌四凳,桌面刻有棋盘,刻迹很新,楚河汉界四字凹槽尤能在月光下反出光来。
“干粮给方丈送去了,花生和豆干被师兄们拿去分了。”富贵摊了摊手。
“这么好?”七盲挑眉。
“师兄们人也不错,一个一个地对着我问询,我初来乍到不好意思,就都分了。”富贵咧嘴笑道。
“好端端为何对你问礼?”七盲好奇。
“我也不知,一位师兄突然来问我‘是不是馋?’虽也觉问得奇怪,可我也不好不应,只得如实作答。他们倒也热情,和我一起吃了些花生,其余的就都送他们分了。”富贵笑得高兴。
“嗯。”七盲蹙眉想了一会儿,抿嘴偷笑,转又问道,“那方才你师叔问你要不要和常住的香客一同用饭时,你怎么摇头呢?”
“师父,我虽然没见过市面,可是我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啊,我不能给咱们庙子丢脸,他们不吃,我们也不能吃!”富贵挺直脊背,坐在蒲团上晃了晃,偏生腹中咕噜声又起,挺直的腰又弯了下去。
中原大寺规矩繁多,戒律严明,单是用餐一事上便有许多的说法,过午不食便是其一。
他们到的时候已入黄昏。
第二日晨钟起时,富贵才明白,过午不食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罢了。
寅时三刻,东方即白,寺内已是人声赫赫,僧值者自是不必说,其他僧人亦是持担提桶列队往寺后山田处去。
富贵随着七盲同去,田间一众僧人,浇水除草好不热闹。那浇水的桶子好生奇怪,上阔下小,难以站立,一旦挑满水便再放不下,那诸多比丘僧也当真是好功夫,两大桶水飞奔往来,如履平地。
“真是好功夫啊!”富贵立于田间良久,看得目瞪口呆,连七盲走开都是不觉。
“师弟既然来了,何不一同练功?来,我的桶子借你。”站在不远处一位高瘦的比丘僧冲富贵喊着。富贵记得他,昨日便是他带着自己搬去僧舍的,法号空白。
“空白师兄,我哪里……”富贵连忙摆手,可话还没说出口,空白的两个桶子已经丢了过来。他刚刚自水边回来,担子在肩,桶中水满,这一抛之力少说百十来斤,哪想竟是稳稳当当地飘了过来,一步不差地落在富贵面前。
可富贵哪里接得住,两桶水落地便倒,滚散开来,撒了富贵一鞋袜。
“哎呀,富贵师弟,对不住……”空白也是吓了一跳,显然也是没料到富贵竟然接不住,口中连连道歉,却也是忍不住大笑。
“空白师兄见笑了,富贵不曾习武。但田间浇水却也做得,富贵这就去担水,只怕是要慢上一些,师兄莫要嫌弃才是。”富贵说罢,弯腰提起水桶便往山下去,满面认真。
这水桶乃是厚木所制,外面又箍了一层铁皮,自重便有十余斤,装满水可达三十几斤,两桶水担在肩上,百十级的台阶走起来,举步维艰。
空白展臂飞跑往返两次,富贵才得以到得田间,一张脸已是憋得通红。如此两次,额头滴汗,如此三次,满背皆湿。
“富贵小师弟,辛苦了。”空白递过毛巾时,亦是大笑,却已无调笑之意。
“师……师兄辛苦……”富贵气喘得严重。
“你们平日不练功吗?”空白抹了抹汗,挑着一双扫帚眉好奇道。
富贵摇头。
“师父不曾教过。”富贵细想,却是不知七盲是否会得功夫。
“也是,你们寺里只得三人,哪里会有武僧?”空白回头环视大寺,满面得意,除去前三殿,大寺内另有千佛殿、法堂、罗汉堂、武僧院、塔林、藏经阁,钟鼓楼等多处礼佛之地。大寺几经扩建,早已是中原数一数二的寺庙,鼎盛时期僧人曾达一百七十三名之多。
每每说及此事,空白便满面骄傲,一双扫帚眉也是扭得恨不得飞上天。
“我师父说,我佛成正果时只得孤身一人。”富贵合十离去。
徒留下空白抿嘴无语。
4
用过早饭,引灯大师自是被问澄方丈请了去。富贵便随着七盲于寺内游览,大寺之大果非寻常,足走了一个时辰才算走遍。武僧院里硕大的练武场上早已是棍棒声起,齐眉棍每一下敲在地上,富贵都能觉出脚下一震,大寺功夫甲天下,果非虚言。
“师父,你会武吗?”富贵想了一大上午,终是问出了口。
“学过。”七盲看着练武场上满身大汗、肌肉刚劲的一时,想了想道。
“那你教我啊。”富贵揉了揉酸疼的肩膀。
“不行,我的功夫不适合教你,你去找你一时师叔学吧。”七盲又想了想,摇头道。
“为什么啊师父?是什么功夫啊?”富贵追问。
“醉拳。”七盲扔下两个字,也扔下富贵,顾自走了。
5
午后,高阳,秋风,红叶。
富贵随着七盲端坐在大殿之上,昏昏欲睡。
富贵强自支撑,七盲却是诵念连连,满目虔诚。
下午各院僧众皆在为三日后的水陆法会做筹备,寺中一时热闹起来。道场选在大殿前的空场上,几十人聚在一起又是摆灯又是布台。
富贵登时满心激动,七盲倒不甚在意,听着院中人声,反倒靠在蒲垫上睡了过去。
日落,霞艳,晚课时分,殿中六七十人诵经如吟,好不壮观,晚课毕,众人刹时便没了声音。
木鱼轻敲,佛香袅袅,大殿静谧,一比丘突然开了口:“净土在何方?”
此问一起,应声连连。
“在慈悲之处。”
“在莲座之下。”
“在人心之中。”
众比丘依次作答。
富贵心下惊喜,他盼着参加中原大寺的辩经会已许久,早前佛前许愿,不想菩萨果真显灵。虽说这不过是日常禅辩,却也难得,登时心下立愿,回去他要蒸油豆腐白菜馅儿的包子供奉菩萨。如此想着,只觉心中一念,不由兴起,便朗声道:“在这儿。”
众人侧目,殿中重归寂静。
引灯大师恍若未曾听见,手捻念珠,垂首默然,却是嘴角含笑。
七盲当真不甚在意,兀自打坐,似已入定。
此后富贵便得了众人推崇,只道是青年一辈罕见的佛缘之人,便是诸位大比丘也是连连赞许,一时间到让富贵满心得意起来。
夜深时分,众人散去,七盲立于院中,仰望天空,今日月圆。
“师兄,寺中不得饮酒。”一时不知何时立于身后。
“嗯,不饮。”七盲点头。
“师兄,不饮酒亦可?不会失了乐趣?”一时奇道,人常说心瘾难戒,七盲竟然答得这般轻巧。
“不会,水酒无差,皆可醉人心。”七盲再点头。
一时蓦然未语。
“师弟归来许久,可否失了乐趣?”七盲扭头看去,鹰眼含笑。
“一如从前,不如从前。”一时微微叹气,答的话与那日山下一同。
“此前可是彼前?”七盲问得也是一样。
“非也,非也。”一时再叹气。
七盲大笑,“哈哈哈,你莫打机锋,两个‘从前’各有意思,你不说我也猜得到。一个是你入八苦寺前,一个是你离八苦寺前,对也不对?”
一时转瞬红了脸,不再言语,哪想往日机锋打得出神入化的七盲,今日竟然白话做解了呢,一语中的,揭人心腑。
“佛修自在。”七盲正色。
一时怔愣,脸色愈红,是的,他归来日久,愈发不自在,对八苦寺反倒甚是怀念。
6
临近法会,各寺的僧人逐渐到来,以至僧舍拥挤,不得不添加被褥,四人同居。
搬来七盲与富贵房中的,是河东广济寺来的法师见净和徒儿语知。
“早先小徒曾往八苦寺中暂修,多蒙二位照顾,今下小徒虽已往登极乐,这份恩情,见净还是要代为谢过才是。”见净法师说着便是一礼。
七盲眨了眨眼,忙回礼道:“见净师的徒儿心下空明,很是难得。”
“七盲师谬赞,若当真空明何至如此?本以为他佛缘颇深,放其远游修行,却落得此等结局,深陷迷局,难以自拔,实非我所料啊……”见净法师身材消瘦,脖颈处青筋隆起,痛心之情可见。
“见净师焉知红尘便是迷局?那孩子此等归处,也未见不好。”七盲却是摇头。
“七盲师不必安慰我,修佛之人,四大皆空,让他往四处的庙宇修行便是要他习空,哪想倒是让他习了个儿女情长……哎……是我这个师父做得不到……”见净法师恨不能攥紧双拳,语知在一旁垂头不语,满面悲思。
“是你这个师父做得不到!”七盲此话一出,惊得富贵慌忙向门口靠了靠,师父第一次见面便这等说话,等会儿若是打了起来,靠着门总还是能跑得快些的吧。
听得此话,见净法师也是一愣,抬眼看向七盲,却见七盲道:“即是要他习空,又何苦四下往庙子里去?那偌大的一间庙子,哪里就成了空?他若真把这些看做了空,那不叫空,该叫做心死才是。”
见净法师静默良久,长吁一声,微微点头,“七盲师说得是,我若不让他下山兴许他已然窥得佛意了吧……那孩子实在是个机灵人儿,哪想却是被红尘误了去。”
富贵见得无事,一颗心始放了下来,正想着二人说得到底是谁,不想七盲却是言辞严厉地又开了口:“那孩子的确是个机灵人儿,只可惜,错拜了师父。”
富贵人坐得周正,心底却是惊得恨不能跳起来就走,语知一双大眼睛看了看七盲,又看向自家师父,也是无措。
“七盲师这是何意?”见净法师果真拧了眉头。
“出红尘是清福,入红尘也未见是罪恶,那孩子即有如此缘分,得来如此结局,便是他之命运。见净师修佛多年,如何还不肯参透,只一味悔其当初,否其行事?
“既是自家弟子,便更该知晓其心性,那孩子心思剔透,热爱生活,与人为善,若不是入我佛门,恐此下红尘里正幸福美满,焉知就不是我佛误了他?”
“七盲师你……怎么说是我佛误人?你这……”见净法师被气得一时语竭,起身便要走,却在到得门口时又气哄哄地回身行了个礼,这才甩着袖子离去。
语知也只得跟着行礼远去了,那孩子不过十六七岁,很是小心翼翼。
“师父,你们说的是……”富贵听得这番话,心里也已有了计较。
“语虚。”七盲吐出两个字。
富贵眼前已是现出了那几年前曾在八苦寺挂单修行,眉眼弯弯的干净少年,喜花草,善耕种,就是得知七盲爱酒之后也未曾多有惊讶,反倒学着用番薯酿起了酒。
这样的人儿最后殁在了红尘里,可有时候,富贵真的觉得,这样的人儿,就该殁在红尘里,师父说得不错。
7
月明,星稀,檀香沁人。
见净法师带着语知回房已是深夜。
“七盲师。”见净法师入门便是一喝,惊得富贵手里的木鱼都险些掉落下去。
“见净师。”七盲合十行礼,声色如常。
“承蒙指点,感激不尽,吾徒能往八苦寺暂修,当真造化也。”见净法师长施一礼,盘腿坐在了七盲眼前,满眼兴奋,他在佛前想了三四个时辰,七盲的话句句敲在耳中,如有鸣钟。
“见净师客气。”七盲提壶斟茶,递了过去,二人热聊一夜,富贵和语知却是抱着被子瞌睡了半宿。
“师父,见净师叔真是健谈啊,性格也很是爽朗。”富贵晃着脑袋,跟在七盲身后,这一夜,也不知二人说了些什么,一阵一阵的笑声把富贵的觉搅了个稀碎。
“是啊,人不错,不入红尘可惜了。”七盲点头。
“师父,入红尘比修佛好吗?”富贵歪头疑问,隐隐想起了那个雨后佛塔前求愿的女子。
“都一样,其实,都一样,吃米饭吃馒头都一样。”七盲又点头。
“师父,你是说入红尘也是修行吗?”富贵似懂似不懂。
“我是说,再不快走几步,你米饭馒头就都吃不上了。”七盲指了指饭堂处进进出出的人,加快了脚步。
法会在即,诸僧众皆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以至于晚上都破例加了餐,这会儿的早餐更是抢手。
非本寺僧众皆正常行早晚课,然本寺僧众却是寅时便要起床为法会奔忙,一连七日的法会,光是施舍出去的饭食就不知要多少。饭堂里的番薯和白菜堆得小山一样,左一盆右一盆的面摆在桌上,足有十几盆。
三日接触下来,那见净法师果真是个直性子的爽朗人,而且礼数周全,无论进出总要行礼,不免让富贵想起那清远镇里的私塾先生,果真是越看越像红尘里的人。
“富贵师兄?”语知趁着诵经完毕的工夫靠了过来,他一直不大爱说话。
“此前曾收到我师兄的信,说他学会了酿酒……”语知抬眼看了看富贵,声音愈发的轻,“说是在你们那学会的……寺里学酿酒做什么?”
“啊?”富贵咬唇无语,语知一双大眼睛还是一睁一眨地看着自己,问得认真。
“酿酒自然是为了喝!”七盲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
“喝……酒?谁?”语知满眼的疑问看向七盲。
“酒还不是谁都能喝,人佛神鬼,猫猫狗狗的,只是你方才说谁酿酒了?”七盲微微笑着挑了挑眉毛。
“啊!没……没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七盲师叔,语知诵经去了。”语知年幼,被七盲这一笑,笑得心上发毛,若是被人知道归去的师兄还会酿酒,这误入红尘的话里只怕就又要加上一项了。
8
水陆慈济,四圣六道,人间悲悯,布施洒净。
法会当天,好不盛大。
内外坛皆是高僧主持,乃是各寺的方丈住持,无不身披金襕袈裟,头戴毗卢帽五佛冠,手持二股六环紫铜法杖。唯大寺方丈问澄法师持二股十二环镀金法杖,持经诵咒,净水结界,法相庄严。
一百二十幅“水陆画”挂满各殿,宝幡高悬,“启建十方法界四圣六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道场功德”二十二字迎风抖动。每日分三时,宣读文疏,昭告十方法界,回向功德,度一切苦厄。
如是七天。
殿前桌几数十张,皆是布施饭食所用,每至此时,寺中便要人山人海,虽是佛门慈悲地,可那为着饭食争抢之事却也常有。
“日渐艰难啊。”引灯大师每每见此情景,总是难忍感叹。
“师父,红尘总是这样吗?”富贵问七盲。
“红尘总是这样吗?”七盲罕见未答。
这一日入夜的诵经,七盲也未往殿上来,待得富贵寻到他时,他正在后山的塔林里饮茶。
“师父,你在哀叹红尘不似往日吗?”富贵扶助七盲,七盲腿脚摇晃,竟似醉了。富贵忙举起茶壶闻了闻,是茶,新下的茉莉花茶。
“你怎知往日便好?”七盲抬眼看向富贵。
“不知。”富贵摇头。
“可师父你说过,红尘是一方死海,即可托浮众生,又可溺死万千,想来它也未见都是恶的。”富贵想起早前的话,彼时刚传来语虚圆寂的消息,他曾问过七盲,什么是红尘。
“是吗?忘了,我这一生说过太多的话,不知还会再说多少的话,你也忘了吧,记不过来。”七盲也摇头。
“师父,你怎么了?”七盲说的醉话,富贵听不懂,可茶也会醉人吗?
“这一生太长,我忘了……”七盲还是摇头,似已是醉了过去。
他这一生太长,他忘了太多的东西,忘了红尘究竟是何模样,也忘了红尘早已改变,更忘了该如何逃脱红尘,独独记得他为何流连红尘不肯自度,却也是时过境迁,变了模样。
今夜有风,今夜亦有月。
然此风非彼风,此月却也已非彼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