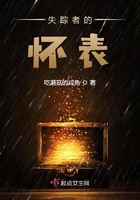她的指尖带出一丝杀气时,已被人握住了她的手腕,轻轻一扯便跌进了那人怀中。
愤怒和惊慌袭上心头,这男子有着迷惑人的圣洁外貌,品行却如此下流!为什么眼前一阵一阵发黑?想要骂出口的话也卡在喉咙里,突然全身一麻,她似乎被人点了穴,身体便软软地倒了下来,她瞪着面前的男人,看他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来!
可是他却给装蒜来着。
只睁开眼睛呢喃了一句话:“娘子,相公还要休息呢。不要闹。你不是一直叫我给你一个名分吗?我今日便是给了。如若是这样,我还是没有理由留在这吗?”
听到这里,她的脸黑了一半,怎么这个男人不记得别的,就光记住这个了,真是强词夺理。
正要再说什么,却看到面前这个男人还躺在床上,翻个身继续睡,一声满足的叹息从凉薄的唇内溢出。那人如墨一般,发出琉璃般光泽的长发铺在床上,长得一直拖到了床边,和她的发纠缠在一起,一只胳膊压在她的腿上。
看到这里,雨烟突然想到同缠连理之丝的说法,再摇摇头,面前这个卑劣的男人怎么能和那么温情的东西缠在一起吗?难道三年前的伤害还不够,难道让他再带一个女子站到自己面前,她才会后悔?
她坐起了起来,抱着双膝,坐在凉风喷薄的窗前静默地思考。
眼睛的余光中,仿佛一双清澄中带着微微邪恶的桃花目半眯半醒,然后睁大了忽闪忽闪地看她。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张大脸向她扑上来,男子的脸在她面前不断放大:“烟儿,若是你着恼我为你作的事情,也无需坐在晨风,若是伤了身子,你叫你相公如何想啊?”
这个男人怎么把相公二字说得如此溜顺?
羞怒的红晕像两片红云爬上两颊,忽然一根手指拂过她的穴道,她感觉身子顿时一抖,骂出一句:“混……混蛋,你怎么可以如此对我!”便轰然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漆黑之中。
上官云看着她淡淡地说:“唉!你当我很乐意这样对你吗?你要是现在不休息一下,明天怎么与我一起去见你父亲呢,他三年前认为你失踪了,曾经让皇上都动员整个京畿的兵力,在风云国大找你的影踪,动员了这么大的人力,自然很快便知道你在我府上。皇上并没有说别的,只是派人把一个小七的丫鬟送到府上,而她手里带一张帖子,是皇上的手谕,当时命令我与你一起前往红滦,你父亲当时知道后,气倒在床躺了三天才好,之后也只得忍着,好在我当时趁着自己兴致很高,和你一起去红滦,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彻底了解你,又怎么知道你是如此合适我的娘子呢?”
一只手揽住她的身体,放回床上。
上官云抬手挽起两边垂下的青色流苏帐,昏黄如豆的烛光淡淡映出他柔和又不失刚毅的脸,起身披了件罩衫。高贵的金色与绯色的丝质纱衣映着他的黑发,白晳的皮肤,尖削的下巴,墨黑得近乎发紫的眸和雪山般的鼻梁。
他转过身看了看陷入昏睡中的女子,她比原来的性格更加活泼了呢。
她原来离开自己是如此自由和幸福吗?
可惜啊,可惜啊,日益增进的感情及他倾心的眷恋,敌不过他最初犯下的错误。
原来当初对她的排斥诋毁,都是出于原本内心里的对她的在意,直到那一夜她温暖了自己,连争执及口角都来不及发生。
她为了他放弃了即将得到的红滦国的公主身份,放弃了美好的生活。
却从来就没有对自己表示过,只为了让流言不再影响他,当着他的面,投身夜色之中消失了……
在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她。
而后遍寻整个京城却是怎么也找不到她。
三年后的此刻,他目不转睛的望着她,不但无法移开视线,就连眨眼都不敢,生怕她会在这一瞬间消失不见……
上官云微微闭起的眼又睁开,下定决心一样,瘦长的指尖探向肩头掀开了她的衣服,目光在那张绝色的脸上梭巡,他靠近了她,用手指在她的肌肤上打磨。
他知道不应该在此刻欺负她,只是若不是如此,她身上三年前中的红滦冰水之毒就不会散去,这风云国只有他练了融水成冰的功夫,他能把她身上那些毒水全部冻成冰从身体里出来,而不伤害发肤,他知道只有自己能帮她,所以他不得不作。
他抱住这具又香又软的身体,右手一指灌注了内力,抵住她额头上的血线。他的手上,头上,身上不停地冒出蒸腾的白汽,不多时两人便被运功所逼出来的白汽所包围。
热。
好热。
如同置身火山般炎热。
过了一会儿又很冷,置身冰窖一般,冻得林雨烟全身发抖。她只有不断地向那热源靠拢。身体仿佛仰面飘在半空之中,一股气从她的额头涌入,上至顶门,下至足心,如岩浆洪流汹涌遍行于血脉中。
她努力想让痛楚使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一些,但是在四肢横冲直撞,要撕开她的那股蛮力忽然消失不见了,就好像全身功力突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虚弱无力的清凉,两片冰凉湿润的东西覆了上来,她吃了一惊,只觉带着薄荷香气向她袭来,她要挣扎,却无力……一股浓重的药味与血的腥味顺势滑入口中,带着又苦又涩又腥甜的芳香从喉咙一直漫延到四肢百骸,渐渐的,肢体变得有知觉,有痛觉,她告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