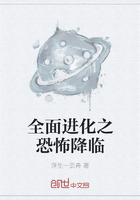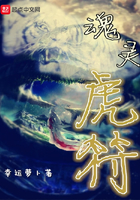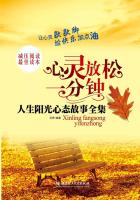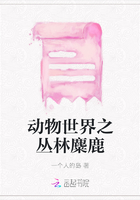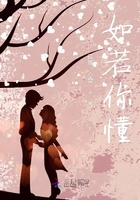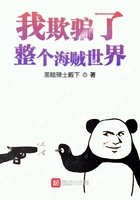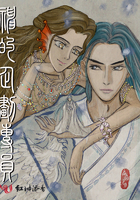很想以此书与众位红迷朋友们交流,有些朋友在读过我的文章之后,
对诗词隐喻十二钗及宝玉的结论仍然存有疑义。认为我仅从一两个字就
判断曹雪芹所写的诗是隐喻《红楼梦》的主人公,令他们无法接受。我要对朋友们的负责态度表示尊重,然后也想就此问题再谈谈我的看法。
我们知道,初本(富察明义所见八十回本)的书名是《红楼梦》,也就是说《红楼梦》的确是作者最原始的创作意图。它的全部故事从大观园
的盛况开始,到贾家事败结束,描写的是宝、黛、钗的婚姻悲剧和贾府的兴衰。但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作者逐渐脱离了“自我以及情感”的纠缠,而把更多的内容放在了人物命运的流变上。他已经意识到,十二钗命运的沉浮,才应当是创作的重心,以她们的薄命来折射人生的悲欢离合,才是更为严肃、更为深刻的文学命题。这一点在第三十六回“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一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回回末有这样的文字:“宝玉一进来,就和袭人长叹,说道:‘我昨晚上的话竟说错了,怪道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袭人昨夜不过是些顽话,已经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疯了。’宝玉默默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此皆宝玉心中所怀,也不可十分妄拟。”在这里,“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表明了作者对全书中心如何掌控的犹豫和其他复杂的心态变化。正是这些原因,在一百一十回的改本中,作者把《风月宝鉴》与初本的内容融合到了一起,确定了以十二钗为中心的总体创作思路。我们可以从《红楼梦》十二曲中感受到这一创作思路的变迁。在此书中,我们分析出了贾宝玉是《终身误》的影寓对象,因而《红楼梦》十二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陵十二钗》曲,这就充分说明,“红楼梦”这一书名与全书“金陵十二钗”的主题并不吻合。试想,假如曹雪芹要写一本名为“红楼梦”的书,会以“红楼梦”来命名这一曲名吗?以他的才能,应该会极力避免这样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加入《风月宝鉴》内容的一百一十回本,书名再也无法称为“红楼梦”。所以,就没有沿用初本的书名(富察明义所见八十回本),而在“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艰辛创作基本结束后,最终确定了全书的题目:所以才“题曰‘金陵十二钗’”。
因此,作者自己确定的书名应当是“金陵十二钗”。后来,由于曹雪芹非常珍视他与脂砚斋的感情,才言听计从地改为“石头记”。现在看来,“石头记”的名字尚不如“红楼梦”,更不用说与“金陵十二钗”相比了。但是,《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极其复杂。由于后三十回佚稿的遗失,以及前八十回的不完整(许多部分是他人补写),从某种意义上讲,脂砚斋和其他修订、补写者也是此书的创作者。这样,就难以避免小说中心思想的偏移。所有认为《红楼梦》是贾宝玉的情感日记,或认为是描写宝黛恋爱悲剧的人,都是受到了后三十回高鹗的续作或者他人改补内容的影响。在高鹗的续作中,无论是掉包计还是黛玉焚稿、宝玉哭灵,等等后四十回的情节,其中心早已与曹雪芹的本意相悖。当然,我们并非说高鹗的续作一无是处,它的文学价值和对《红楼梦》的推广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假如要为包括高鹗续作在内的程高本定一个书名的话,那“红楼梦”显然最佳,“金陵十二钗”反而不符合书中后四十回的故事情节。
其实,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前八十回中,作者不止一次地向我
们暗示了十二钗的最后结局,他已经遗失的后三十回,一定还是要把“闺
阁中”的“历历”之人(第一回),作为主要人物来刻画,脂砚斋所透漏的书末情榜就说明了一切。在读《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过程中,要时时注意对十二钗的隐喻。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我分析出来的那些影射关系,绝非简单的巧合,而是作者十年辛苦、殚精竭虑的精妙构思。说到这里,有人也许要问:神瑛侍者呢?你把贾宝玉置于何地?我的意见是:毫无疑问,贾宝玉的生活原型就是作者自己。在书中反复被称为蠢物、浊物的他,正是第一回作者所言“风流冤孽”的其中一员,是《金陵十二钗》故事的影响和旁观者。他在书中作为甄宝玉的影子出现,甄宝玉音射“真宝玉”——“石头”,而这个“石头”就是编写全书故事之人——曹雪芹。
从第一篇《红楼梦》探索文章开始,每一次探索都是顺着这一思路展
开。因此,全部结论都由一气贯通的线索连接在一起。之所以仅以少数文
字就能够判断出某些影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之上。这样,
各个结论之间可以存在足够的互证关系,保证了结论的准确度,也保持了
研究方向的正确。因此,我认为我的探索分析还是有足够根据的,所有的
研究过程也都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刻意的揣摩和轻易的定论。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的文笔是何等的玄妙与细腻。如
果不作耐心、深入的分析,很难发现他文字后面所隐藏的秘密,细读文本才是探索的关键。
最后需要说明,本书所引用的文字资料一部分来源于作者的原著,但
大部分来源于网络,鉴于条件所限,难免有所疏漏。许多相关网络文字的引用,实在不能得知原作者的姓名和出处,不到之处敬请原作者及读者谅察。
特别感谢郑文莉大姐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帮助我实现了多年夙愿。祝
福所有关心和支持这本书的朋友,以及你们的家人!
2015年11月11日于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