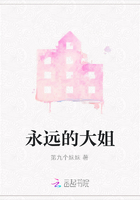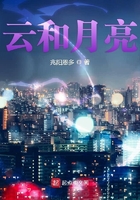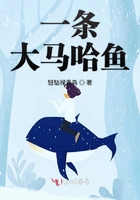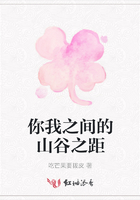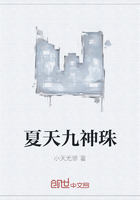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是《红楼梦》
全书的重点。因为不仅宝钗念的《寄生草》:“漫漫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暗示了宝玉出家、乞讨的结果。而且,众人写的灯谜诗也被认为是暗示了他们各自的命运和结局。例如,元妃写的炮竹灯谜、探春写的风筝灯谜,一直都被认为是她们最终命运的写照。就连脂砚斋恐怕也被作者给瞒过了,因为她在两首诗后都有批语,元春诗的批语是:“此元春之迷,才得侥幸,奈寿不长,可悲哉!”
探春诗的批语是:“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可见她也认为这两首诗是暗指元春与探春二人的。但是,经过我的研究,发现事实竟非如此!这就充分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曹雪芹一人,脂砚斋只是很重要的参与者,有些脂砚斋所称的“狡狯之笔”,恐怕连脂砚斋自己都会产生误解。关于书名的确定,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何“石头记”被脂砚斋确定,被曹雪芹“屈从”,却最后被“红楼梦”取代了呢?说明“石头记”并非最贴切的或最好的书名。其实,真正的书名应当是“金陵十二钗”,这才是作者的真正意愿。
这些灯谜诗在脂本中共有八首,分别为贾环、贾母、贾政、元妃、迎春、探春、惜春、宝钗所作,而且在惜春诗的第一句后面有一条庚辰眉批:“此后破失,系再补。”脂本中缺少通行本(一百二十回本)里宝玉的镜子诗以及最后一首宝钗的诗,还把黛玉的更香诗写成是宝钗所作,又多出了惜春的一首海灯诗。由于脂本在此节缺失较多,当然应当以更为完整的通行本为准,惜春一首诗有人疑为脂砚斋所后补。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行本中这些灯谜诗的含义。通行本第二十二回的灯谜诗共有九首,分别为九人所作:贾环、贾母、贾政、元妃、迎
春、探春、黛玉、宝玉、宝钗。如果姑且认为脂砚斋的批语判断正确,那么这些诗与作者就应当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如果仔细一读,就会觉得除元春与探春的诗意尚稍有些关联的可能,其他的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有人会说,其他的就乱来,我想这样就大大地低估了曹雪芹的神来之笔。而且,当你看到最后一首时,就会发现,这首诗怎么像是说了好几个人呢?宝钗的灯谜诗是“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山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虽浓不到冬”。“有眼无珠腹内空”能用来形容宝钗吗?我们知道,十二钗中宝钗的博学是最为突出的。即使用于宝玉,这句话也显得极其过分,令人无法接受。接着,“荷花山水喜相逢”则毫无连贯的意味。是说她与宝玉相逢吗?但她是牡丹而不是荷花呀,这句子用在黛玉、惜春,甚至其他任何人或者可以稍有余地,用于宝钗则解释不通。可以断定,前两句绝不是说她自己,或者是与宝玉的婚姻。“梧桐叶落分离别”我们暂且不表,我认为“恩爱虽浓不到冬”才是她的判词。我们姑且先假设这四句诗是意指四个人物,那么,前八首加上这四句就又是十二个独立的意义。怎么又是十二个呢?又会是巧合吗?有这么巧合的事吗?结合贾政的“悲谶语”,显然这些灯谜诗隐藏着关键人物的最后结局。我认为,这些灯谜诗又是十二钗的判词。
这样一来我们才能理解迎春为什么会写出“纷纷乱”的算盘诗,十二
钗里面,谁都知道只有王熙凤才会“机关算尽太聪明”而且是“有功无运”的人,这首诗显然是指她;也会理解黛玉和宝钗(脂本这首为宝钗所作)怎么会有“琴边衾里两无缘”,因为黛玉、宝钗和琴没什么关系呀,琴应该是元春的代表嘛。我们知道,元、迎、探、惜是分别以琴棋书画见长的,就连她们的丫鬟都起了相关的名字: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朝罢谁携两袖烟”这句说得更加明白,这首诗是暗指朝廷内的人物,这定是元春无疑。诗的后面几句,描述了她在宫中的幽微生活,非常的悲切。那迎春是哪一首呢?我觉得应当是贾环写的灯谜诗。这首诗的意义绝非仅仅是表现贾环的搞笑,以曹雪芹的文笔,它还会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只在床上坐”,显然是在暗说贾琏的好色淫乱;“爱在房上蹲”,是说宝玉的情高。仔细想来也只有迎春、探春才符合大哥、二哥的条件限制,而后来的枕头和兽头又暗指了迎春的与兽共枕,嫁给了中山狼的最后结局。
既然元春的判词是黛玉(或宝钗)作的灯谜诗,那她的炮竹诗就只能是说秦可卿的了。诗中不仅描述出了她的“欲知命短问前生”的短暂生
命,还体现出了“能使妖魔胆尽摧”的警幻之妹的仙界身份,和“身如束帛气如雷”的高贵出身,以及她死后造成的“人方恐”和最后贾府的“化灰”结局。探春的诗是指黛玉。第七十回,众人放风筝,第一个放飞的就是黛玉的风筝。“阶下儿童”道出了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妆点”,正合了潇湘妃子的“风露清愁”(第六十三回)。“游丝一断浑无力”,是说她体弱多病,而“莫向东风怨别离”,也正是第六十三回的“莫怨东风当自嗟”一句的翻版。到现在,我们该叹服作者的“烟云模糊”之笔了吧?贾母的“猴子身轻站树梢”一定是说湘云。第四十九回黛玉说“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第三十一回,也提到了她穿着又大又长的大红猩猩毡斗篷栽到沟跟前,弄了一身泥水。既然“立(意合站字)枝”就是荔枝,那“吏”(音同立)字去掉一是不是就是个史字呢?当然,这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了。
总之,不管怎样,十二钗中又只剩下了六位:妙玉、巧姐、李纨、惜春、探春、宝钗。而其中,描写分离的只有“梧桐叶落分离别”一句,这一定是说探春了。在书中第四十回,贾母在探春房内言道:“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细些。”是关于探春的暗语,暗指她将来的命运。有人会说,探春是在清明节坐船走的呀,梧桐叶如何会落呢?我想,既然贾府已经马上就要“大厦将倾”了,作者就保不准要来一个“天时”的暗示,就像第七十七回宝玉说:“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知就有异事,果然应在她身上。”或风或雪,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探春走时,竟然“梧桐叶落”了也未可知。“有眼无珠腹内空”,就一定是指李纨,“有眼”是指贾兰日后的中举(可能是榜眼);“无珠”当然是说贾珠的早死;腹内空即是说她只以“女红”为要,未“十分读书”,丧偶后更如“槁木死灰”一般。“荷花山水喜相逢”是说惜春,惜春于藕香榭居住,自与荷花有关;而“荷花山
水喜相逢”,又暗指她的绘画才能,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就只剩下了三位:妙玉、巧姐、宝钗。那么“恩爱虽浓不到冬”就只能是说宝钗了,看来她与宝玉也曾一度恩爱过短短的时间,但不久就结束了,而且结束的时间“大约在冬季”。关键是砚台和镜子的归属问题,由于“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来形容巧姐,所以巧姐便是宝玉诗所称“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的镜子,特点是自省、易碎、亦真亦幻。这时我们就会对第四十一回刘姥姥在宝玉房内照镜子的情节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不仅“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后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暗示了巧姐判词中“巧得遇恩人”与“济刘氏”的特殊因果关系,而且“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也隐含了板儿与巧姐的姻缘。那么妙玉与砚台如何解释呢?我认为其中隐藏了《红楼梦》全书之中最大的秘密,我将另写文章详细说明。
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认为脂本中惜春作的海灯诗应该也是曹
翁所作,原因在于虽然脂砚斋也曾对《红楼梦》全书进行修订,但是对作者的原文却非常尊重。如第七十五回所缺的中秋诗,脂砚斋虽多次重评,却未轻易补上。这首诗的含义指向了宝玉:“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其诗文用来形容惜春明显牵强。“色相”在这里是佛教名词,指一切事物的形状外貌。《华严经》有“无边色相”,《楞严经》有“离诸色相”。“前身色相总无成”,是宝玉一身的结语,言他一事无成,而惜春作为古代女子并无重要事业可言。“不听菱歌”是造成误解的另外原因,但惜春住在蓼风轩、藕香榭,“菱”字若有所指,那也只能是指住在缀锦楼、紫菱洲的迎春,与惜春没有任何关系。根据脂批,“不听菱歌听佛经”明显是暗合了后三十回中,宝玉到紫菱洲一带悼念颦儿并悟道的情节。“沉黑海”就是第五回末被警幻形容为“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的迷津。最末一句是指他最后的大彻大悟和皈依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