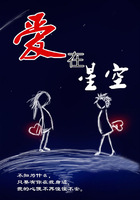身体猛地一震,坐起来,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她还是能感觉到,这儿不是宿舍,像是医院,四周冷冰冰的,病房是独立一间,她拧破脑袋也想不出,自己怎么在这儿,又是谁送她来的。即使此时她头脑是清醒的,可还是略微有点胀痛,身体也有些酸软。
她费力的从那床上坐起来,从渐渐有点光亮的外景,摸索床边的鞋,当然她不是找不到房间的灯,她只是不想去打破这份静谧,她想一个人带着疑问,带着心事走走。
刚才的梦,还在脑海里隐隐浮现,难不成自己其实已经命悬一线,到了过奈何桥的关键一步,挺了回来?
她穿着的病服好像大了一号,长长的衣袖耷拉着,不见她的五指。她隔着衣袖将门推开,抬起那双没有重量的拖鞋,其中一只依着她的脚,弹出门外一步,触到走廊暖光的一角,另一只慢慢跟了上来。
然后站在自己刚刚走出的门外,四周仅有拉上房门的一点点声响,这条长长的走道没有一人的声音,只有静谧无人端坐的一把椅子,在那廊道尽头的窗台上,安然放置的一盆盆栽,还有从那儿再望去的一轮明月,这一切简直寂静的令人窒息。
“你怎么走出来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音,从后面传来。
“这深更半夜的容易着凉,你又没披件衣服出来,到时候要跟严重了!”她转过身去,只听那男人继续说道,他一身大白褂,佩戴听诊器,这样就明显了,是这儿的医生,见他朝着自己走来,她正好有些问题问他。
“那个,医生,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在这儿多久了?”
“你男朋友送你来的啊,前天下午送过来的。”
“前天?我男朋友?”聂木思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跳到了另一个梦里,有些诧异的问道。
“是啊,他现在就在你隔壁房里呢?”
“在我隔壁?”心里的疑问一下问不完,这医生问一句答一句,还越扯越远,把她弄得更糊涂了,既然他说她男朋友就在隔壁,何不过去一探见分晓。于是,提腿就往隔壁迈。前脚刚迈出去,后脚就被人拉了回来。
“你要去,也先披件衣服过去。你们年轻人也真是爱的不知死活,感冒了还唾液传播。”
那医生一边无奈的摇头,从房里拿出大衣给她披上,虽然室内有暖气,但是这个医生还这么细心关照,真是让聂木思看着他潇洒离去的背影感激的鼻涕直流,全然没有理会这医生说起话来,也是有那么三分不正经的。
她蹑手蹑脚的推门而入,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像做贼似的,只是这毕竟是传说中的男朋友,不好好一睹芳容,如何是好。
走了几步,刚好停在电视机与病床的中间,月光投影在那个人的睡颜上,让他多了几分妩媚,她不敢再上前去看,只是远远的呆在那儿,扶着床尾的杆子,右手按住跳动的心,她在心里责怪它,怎么那么不安分。
一边眼睛一刻都不曾离开,从偏分的刘海,到隐隐露出的饱满额头,神气的粗眉,还有平时根本没这么清楚的看到的,又长又浓密的睫毛,以及很远都能让她感受到,他深深浅浅的呼吸,从高挺的鼻梁收入,又放出,再延伸到那个有些干涩的嘴唇。
“他是为什么在这儿?”刚刚问那个医生也没问出来,她有些无奈的陷入到自己的回忆里面,然后眉头有些波动,小声的自说自问道:“是上次在哪儿着凉的吗?”
那天她心情不好,哭了很久,虽然天气很冷,又入夜转凉,也无法转走她的悲伤,任性的在哪儿低落了很久,但她没想到,他会一直等在哪儿。当时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外套,想必是在那时着凉了。
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意,也不管是不是自作多情,现下四周寂静无声,如果没人再来打断她,她的思想真的要沦陷了,要沦陷了,就沦陷了,她看着那双闭着眼的长睫毛,一步一步,从松开床尾的杆子开始,一步一步,向他接近,紧接着挡住了他被月光的投影,让她的影子照在他的身上,伸过头去,就像走火入魔一般,她的唇盖上他的,当深深留下一个印记后,她才如梦初醒一般,定定地直起身,那个从不脸红的她,此时此刻就像炭烧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