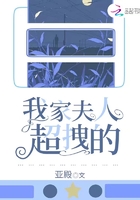我加快脚步冲进了人类的队伍,他们如惊弓之鸟四下里散开,对我举起刀剑。
我立马抬手道:“我是女巫,瞧,我可不怕阳光,天呐,我只是肤色白了点,总有人把我认成吸血鬼!”
我抬高嗓音,让自己显得更有女巫的权威与气势,同时,玩笑似的解释了我惨白的皮肤,尽管他们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笑意。
他们的眼睛如咸鱼般木讷地瞪着我。
我尴尬地立定,心想是不是哪里出错了,难道巫师不是他们的盟友吗?
还是说不包括女巫?
我心下越来越忐忑,一个将领模样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正朝我走来,面色不善,我大感不妙,这时想回头却也晚了。
不料他狰狞的脸一到面前就劈头盖脸吼道:“为什么不进王宫去?早知道你们这些摆弄草药和咒术的喜欢磨磨蹭蹭......”
后面的我没听清,因为他边说话边把我往前推,我只好顺从地往前跑,又被路上的尸体绊了几脚,只听那将领在背后开怀大笑道:“跑快点儿,短腿猫,你要是不做女巫也不必在这儿遭罪......”
之后又是一阵笑。
我相信若他不是歼灭运动的士兵,一定是能逗乐大伙儿的存在,可他现在成了魔鬼。
很多人类,在这场运动中,都成了魔鬼。
这里并没有硝烟弥漫,除了那栋图书馆楼烧得只剩框架,其余建筑物完好无损,如果一个不知情的人意外闯进这里,绝看不出这座城市战斗过的痕迹,倒会以为这是一处地上有尸体的鬼城。
那支人类队伍被我远远甩在后边了,我停下这没命的奔跑,开始往近在咫尺的墓园走。
我想不到他们好应付得很,但愿他们过来的时候,斯图尔特亲王能为自己找到个藏身之处。
我仿佛在一座空城前行,墓园的大门被利器砸开,有半扇已歪倒一旁,前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恍若置身大漠的寂静,孤独包围着我,我简直怀疑——
他们是不是都死了?!
不过我很快赶走了这个念头,转而回想起那种阻挡紫外线的黑袍子。
它并没有流向帝国市面,几次看见它们都穿在萨曼塔手下或亚伯家族身上,连告诉我它的作用的人也是杰克。
现在看来,我们之前对这种黑袍子只流动于血族上层社会的猜想是错误的。
或许只有魔党和亚伯家的亲信拥有这样的袍子,而卡玛利拉有可能连这种袍子的存在都不知道。
长老会被眼皮子底下的叛党作弄,很是悲哀,可这样的教训也实在解恨。
大概忙于为歼灭运动绷紧神经,怎么也想不到一切竟是同族所为。
他们明白真相时的惊讶,不会亚于我。
我走向王宫时就如同走在光秃秃的平原上,非常显眼,如果有人从王宫朝墓地方向看,他们一定能见着我这个靶子似的目标,方圆百里仿佛只剩我一个活物。
但愿我没那么倒霉,被认识我的人——尤其是亚伯家族撞见。
好不容易熬完了全程,那心情活像一个从斗兽场侥幸生存下来的人,还没休息半会儿,下一场角斗又出现在眼前,似乎永无宁日,欣喜与苦楚交织。
但我还是走上了台阶,我原本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去,可是周遭的气氛显然不太对劲。
太安静了。
难道已经结束了?
那我刚才遇见的士兵是幻觉吗?
我一级一级向上走,心底越发不安起来,直到走尽台阶,上到正殿门口,四周仍旧静谧。
人都去哪儿了?
我看到许久之前那场庆祝血宿的舞会残留下来的东西,血液在地上凝固成黑色,不知是酒瓶里的食物还是战士为自身党派所作的牺牲。
但这样的血迹大片大片盛开在碎瓷,碎玻璃,雕花木块和不再新鲜的花束之间,而这一切,在花饰手工地毯上零落各处,一片狼藉。
心里满满的全是疑问,却不敢贸然前行,木头一样钉在原地。
现在怎么办?
拿上一把冲锋枪冲上战场却发现连个鬼影都没有,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我觉得也许会突然听见一阵声响,至少是一点为我指引方向的骚动,但我等了很久,空荡荡的殿内什么也没有改变。
凭着记忆,我从正殿侧门出去,朝阿丽莎的宅邸走近,远远看去,宅子上方圆柱形的结构,也就是上次囚禁我的环形监狱,现在已经修葺完毕,看不出损坏。
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这些囚室,而是那间蛊室。
我不知道蛊室的确切位置,进门以后只能挨间去找,那应该是个潮湿阴暗的地方,这个猜想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没找到地下室之类的痕迹。
我毫无目的地搜寻,像是在人迹罕至的老屋里游荡,实话说,我现在宁肯遇到魔党士兵,也不想孤零零在这儿晃悠。
既然什么人也没有,杀希拉尔也杀不了了,现在看来我该回去了,顺道遇上斯图尔特亲王就把他捎上,指不定一回去发现大团圆了,哈德斯的病也好了,腰不酸腿不痛脑袋不抽筋脸色也不五颜六色了,真是个美满的结局。
毕竟这里什么也没有。
可是,强烈的直觉告诉我,一定不对劲!
我想上楼去,楼梯是石砌的,未经打磨的岩石,不易摧毁,可石阶表面却有几道裂纹,崭新的裂纹,每一道都有一个巴掌大小。
也就是说,这附近,短期内一定发生过剧烈的震动,不然,就只有巨人可以踩出这种裂纹了。
我沿着裂纹向上走,三四级台阶以后就没有了,可我接着上了楼,打算去二楼找一圈。
我低着头,不放过台阶上的蛛丝马迹,到最后也没什么意外发现,踏到二楼的区域,我觉得心里毛毛的,很是奇怪。
刚才我走过的楼梯很奇怪,不过我说不出来,这是一种直觉,就像当一双眼睛盯住你时你所有的感受。
我讷讷地背过身去,眼睛一晃,蓦然发现扶手上有血红色的掌印,掌纹指纹依晰呈现,从扶手下端那头,像行走一样,有力胜似无力地搭上来,一只一只急疾的逼向我。
它停在了二楼。
掌印的主人当时大概就站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因失血而变得虚弱,为此他不得不摸着扶手上来,举步维艰,所以掌印渗得深,血手影看上去就像鬼片里的场景,可怖极了。
我下意识地环顾一下四周,生怕从哪儿蹦出个鬼一样的东西来。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注意到一块不显眼的血迹,它在离我最近的门的门框上,门是半掩的,那块血迹真是值得推敲,倘若刚才我稍不留神,就可能把它忽视掉。
我走到近处,立刻发现这血迹是被故意抹擦了的,可以想象,进门的人不想让后来的人知道他进去了,用袖子匆忙涂抹了一阵儿,所以痕迹不深,而且凌乱。
这个人可能还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