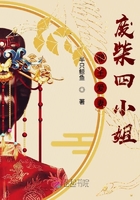我恍惚地走到沙发边,靠在背垫上,思及良久我问他,“你说过他会毫发无损回来的,现在呢?”
他像是早知道我会这么问了,他迫不及待地回答:“我没想到蛊术的皮毛之式能与圣器相匹敌。”
他忧虑地摸索着下巴,仿佛那儿有把胡子,“这是谁也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们用这种东方巫术对付我们,我们几乎没有胜算。蛊术多种多样,在食物里,饮料里,甚至空气里,可怕的是,还有一种用眼神蛊惑人心的蛊术。”
“夏谷子的传承人在哪里?”我不想听他的埋怨,立即问道。
“苗疆,苗族人聚居的寨子里,他们分为内寨外寨,熟蛊术的人家都在内寨,尚未被现代文明同化,她就在那儿。”
“传承人是个女人?”
“传内不传外,传女不传男。”他提醒道。
“你那么肯定她会教我?既然是传内不传外……”
“一切都是未知数。”丹尼尔扶着我的肩意味深长地说,“缪斯,我相信你可以把未知变成已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别忘了,你本是传承人。”
我从他灰色的眼中看见了希望,有如朝霞终于照耀了沉寂的一池死水,他这神秘的深不可测的双眼,让我的意识快闪出一些画面,我曾见过这双眼眸。
我为这记忆的复苏而兴奋,但我没把情绪表现出来,如我初见他时一样,这种关系太过陌生,我难以敞开心怀。
“你也看到了,如果没人解蛊,他就会死。”丹尼尔再次言明后果,似乎是要时时提醒我,否则我就会立马改变主意一般。
他害怕我反悔吗?他真的担心哈德斯吗?
我对他有了猜忌,并且恐惧。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一声不吭,他也一样,我们坐到沙发上,怀着各自的心思,一直待到天亮。
离开北美大陆使我感觉非常良好,飞机在太平洋上飞驰时我拆封了一本现代读物,旁边的非洲年轻人怪异的瞟了我一眼。
怎么了?难道读小说已经过时了?我有些顾虑,唯恐自己正在做的事与现代人类社会格格不入,于是把这本安妮.赖斯的《梅瑞克》轻轻放在膝盖上,开始看窗外的云景。
越是靠近东方那片秘密的土地,越是向往恍若前世的苗疆风情,我无所顾忌地相信,这是目前留给我的羁绊,长存在我灵魂深处的牵念。
夜间到达北京,父亲安排的接机者交给我一些中国货币,以备不时之需,在某些城市,银行卡式不适用的。
随即登上去往华中的飞机。到了那边,如我这般的外籍面孔就少见了,接机者是那座城市所剩无几的吸血鬼之一,区域亲王的助理,他为我安排了住宿,并告知次日亲王接见的时间——外域的吸血鬼来到新的区域长久留驻需要得到区域亲王的召见与认可,方能在该辖区活动。
在这座城市游荡一个白天,被不少人用夹生的英文搭讪,甚是汗颜。
傍晚回到酒店,亲王已然至此,竟是个中国人——这血统来之不易,不禁使我想起马尔斯,与这位亲王一样,血统纯正的亚洲人被初拥,要承受的血液变异的痛苦比欧美人深重数倍,存活几率小,因而他们都是凭顽强的意志撑过初拥过程的。
他们的长相更偏于混血儿,因为样貌随血液转变,有了欧美人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微之甚微,不细看也难以觉察。
他摘下帽子,给了我一个惊诧——他的头顶,居然一毛不拔。
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受初拥那天剃了个头,之后就再也没长头发了。”
“你的尊长没告诉你吸血鬼的头发是无法改变的吗?”我感受到这位亲王的和蔼了,所以我在他面前哈哈大笑,他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嘲讽,诚然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
“我的尊长告诉我,光头永远不会过时。”
他不苟言笑,我们之间的气氛立刻轻松了下来,但愿他在面对卡玛利拉老谋深算的长老时没有这样亲切。
见一面,相谈甚欢,没有惹他生气,这就算通过了召见。
我谢绝了他要派助理陪同我的好意,对我而言那意味着白昼里行动的限制,他不再坚持,只说必要时可以给予我帮助。
天亮后,终于坐上了开往苗疆聚居地的车,离骨子里的牵念,越来越近。
到达苗疆所谓的外寨,发现不过是假模假样的竹楼里有些许穿戏服的人,连掉缺银饰部件都可以拿胶水粘回去,他们在旅行者面前重复一段又一段的演说,然后手舞足蹈,献上山歌——但不是苗语。
丹尼尔远程定位的谷歌地图把我带离旅游区,进入一片深山老林里迷了路。指南针开始还有用,后来无休止地胡乱旋转,也许是被附近某种未知的磁场干扰了。
一个迷路的吸血鬼,实在太逊了,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决意自行碰碰运气。
一个以血的欲望为主食的生物,在这狂野的自然里多么合适,尽管我尚存人性。
自然的神明分辨得了好与恶,不该困住无害于它的生物,好比如我。
我这样自信的再林子里转悠一阵儿,没走出去,但好歹见到了个人影。
我担心那是不出深寨的只说苗语的人,别说是苗语,就连中文我都说不顺溜,原本在城市里,人人都能说几句英文,对外来长相的人格外亲切,外寨里也少有人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如今进内寨去,怕是连中文都不管用了。
不多时,那人影靠近我,这时我才发现雾有多重,因为他离我两米左右时我才看清他的模样,一个白发老人,左手攥紧一只黑色的布袋,右手一根竹竿撑在地上,竿上用草绳绑了类似铁钩的东西,像是捕捉器。
他是个真正的传统苗人,从精编细织的服饰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与外寨那些形似戏服的化纤劣质装束大有不同。
上装为棉麻制成的对襟短衣,深色的,肩披是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头缠青色包头,小腿上缠裹绑腿,有少许泥泞,他大概在林子里待上了一段时间。
“猛唔。”他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说道,语气很是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