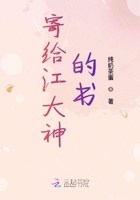不久后我们便抱了各自的笔记本来。事实证明,纯良的教诲确实是真理。自从四台笔记本进入514,上网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大约混混沌沌没日没夜地上了几天网,忽然发现学期已经过了一半。我做了些什么呢。参加了几个古里古怪的社团,看了几部没头没尾的电影,认识了几个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了几块不明不白的冤钱。没头没脑地忙了些日子,文学社,辩论队,学生会,还有一个缩写SICA(我管它叫西瓜的啥啥)的学生交流协会。没过多久,系里又开始组织一个啥啥“一二九”合唱。一帮中文系新生黑压压地站在五院二楼会议室里,哇哇哇地练声。那位组织合唱的学姐嫌我们声音不够响,没放开来,要求我们全都弯腰九十度,对着地板练嗓子,据说这样可以扩大声腔,加大声道共鸣,从而增加音强,以达到宏亮的声音效果。练声时要求发舌面前低圆唇元音以及舌面前高不圆唇元音。我一听语音学术语就犯迷糊,没发声倒先被自己的口水呛着了。
“一二九”合唱排练的后遗症是,514不时传出美妙的乐声。有一次丁子吊着嗓子在唱,片子说,我很喜欢你唱京剧呀!丁子狠狠地白了片子一眼,用冷得能结冰的声音说:我在唱歌。我在一边笑得快瘫了。
上BBS灌水,聊天聊得手疼,开无聊的会,跑无聊的差,我实在有些腻了。我跟纯良说,想找点有意义的事做。纯良就问我想不想当志愿者。我说行,你觉得什么有意思我就跟着你干什么吧。
然后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P大国际文化节的展台志愿者。国际文化节是P大自我标榜的国际学生交流盛会,把所有能召集的外国留学生都拉扯进来。文化节那天,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展台,由各自留学生布置主持,展台志愿者按他们的要求提供帮助,说白了就是不要钱的帮佣。大多数报名当展台志愿者的人最初都有这样美好的愿望:希望被分配到北美或者西欧的展台去,最差也得是新加坡。但事实上来自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少得可怜。留学生最多的是韩国,走在路上都会见到两个韩国人打招呼说声“阿纳塞哟”。据说是因为韩国人都要服兵役,他们跑到中国来留学可以逃掉兵役。我当然也做过能接手韩国或者日本展台的美梦。我收到分配国家的邮件的时候愣了一下。我被分到孟加拉。当时大脑的第一反应是,呃,非洲。
然后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脖子上缠着蟒蛇的黑人形象。我打了个哆嗦。纯良敲着我的脑袋说,亏你读文科的呢,给我看地图去。
负责孟加拉展台的小组就两个人:极不负责的组长纯良和我。当我终于在喜马拉雅山的南边找到孟加拉国的时候收到纯良的一条短信,说孟加拉的留学生想在周日下午与我们见面。我收起地图,一边在脑海中勾勒了一个完美的黑马王子形象。孟加拉毗邻印度,而印度人是白种人,所以孟加拉人应该也具备白人的特征。
我一面遥想一面下意识地抬起头仰望,眼前登时出现了一个年轻英俊的打虎英雄。
黝黑的皮肤,闪光的眼睛,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梁,骑在威猛的孟加拉虎的背上,迎面向我走来……片子听完我的描述,一脸鄙夷:“当心你的黑马王子大得可以给你当爹!”
下午我如愿见到了传说中的孟加拉留学生。黝黑的皮肤,反光的眼镜,高高的额头,高高的——嗯,嘴唇,骑在——嗯,广泛使用的自行车上,迎面向我驶来……不幸全被片子言中了。看他的年纪,几乎可以肯定是个有家室的,就算没家室也应该有主儿的人。我英俊的黑马王子就这么被现实无情地击垮了。当然我不能把我的失望之情表现出来。志愿者培训的时候我们就被反复告诫,绝对不能与留学生发生冲突,必须尊重对方,这是涉及到中孟两国关系的大事情。本着深刻的国际主义觉悟,我面带微笑地与那个孟加拉人打招呼。
我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低头开始费力地读上面的英文字母。MohammadMainul Islam.从貌似他名字的那几个单词里我勉强认出了类似穆罕默德、伊斯兰之类的单词。他笑了:“哦,我信伊斯兰教。我叫马伊努,不过更多人叫我‘小马哥’。”然后他开始了一大段折磨我听力的自我介绍,抑扬顿挫的汉语中不时夹几句英语。凡是我以为他在讲英语的时候,他都在讲汉语;等我用汉语的语法去理解他的话时,他又切换成英语了。在亲爱的组长的帮助下,我大概听明白了,原来马伊努是孟加拉达卡大学的副教授,在P大攻读人口学的博士学位,已经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真要命,原来一直被我YY的是个教授,真是不要命了我。之后马伊努掏出一本纪念册,给我们看他去年参加国际文化节的照片。照片中的马伊努穿着民族服装,笑容飞扬,简直就是个友谊大使。交谈的时候不断有路过的黑头发或者黄头发女孩冲马伊努打招呼。马伊努笑说:“那是我妹妹……我在中国可有很多妹妹哦!”然后看我,看得我满身疙瘩。
我们离开之前马伊努提出来,周五他要去孟加拉大使馆,问我们能不能去。
我那个超级不负责的组长挠挠头说,他有课。然后就用半命令半抱歉的眼神看我。
一出马伊努的视线,我就开始跟纯良理论。进京之前我妈就告诫我,千万不能一个人出校门,何况去的是一个大使馆。
“你不是一个人去……(不是一个人才糟啊……)放心吧没事儿。北京的治安好着呢。去吧去吧。我保管你活着回来!”
活着回来……我要少一根毛我就死给你看……得,要死也得拉上个伴儿。于是我找上片子。
“开什么玩笑!如果真是个年轻英俊的孟加拉帅哥我当然还可以考虑考虑,我怎么能把我的美好青春浪费在一个老头身上!”
我对片子的重色轻友表示强烈不满给予严厉谴责,然后我从道义上良心上法律上国际主义精神上对她进行轮番轰炸。最后一招是,我请客。片子同意去了。
周五下午阳光明媚。安全起见,我把学校报警电话设了快捷键。我跟片子在约定的地方等马伊努。但是不久一个皮肤黝黑的青年朝我们走来问:“请问是刘小姐吗?”
我吓了一大跳。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叫小姐。我傻了似地望着他。咦,几天不见,马伊怒怎么进化得那么帅了?黑的皮肤,没错。个子也不高,没错。但是,怎么说呢,我不是故意用褒义词,可是感觉……很舒服。
“喂!”片子咬我耳朵,“好像跟你描述的风格不太一样呀。”
“嗯,是这样。马伊努下午有事来不了,所以让我去使馆拿展品。我也是孟加拉的留学生,叫我柯修就行。”他说,很好听的声音。
之后柯修就领着我们出校门打的去大使馆。路上几乎没什么话。他似乎并不爱说话,不像马伊努。马伊努在的时候,他会一直掌握着话题,学术,人口,P大,文化节。他很能说,听的人便听着,不会觉得不自在。可是跟柯修在一起,一直沉默地走着,觉得很尴尬,觉得该说些什么。我忽然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去查查有关孟加拉的资料,起码不至于无话可说啊。
出租车驶入使馆区的时候,会有出乎意料又理所当然的感觉。我对北京使馆区的印象,还停留在战争年代。戒备森严,没有路人,拒人千里之外的黑色建筑,敞开却不怀好意的大门。但是这条街上,整洁,平和,干净。各式各样的小别墅安静地坐落在树影后面,屋檐用温和的角度反射着阳光。要不是那些按一定角度摆头的警卫,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区。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它们安静地栖居在各自等大的领地,国旗一样地在风中飘扬。柔阳从树叶尖跌落进每个路人的手心。
出租车在一幢蓝白相间的建筑前停了下来。我们跟着柯修进去,门卫甚至没拦住我们要求登记。通过一条窄窄的走道就是不大的会客厅,富丽而典雅,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孟加拉女子的肖像,桌上摆着各式各样古怪而精致的饰品。电视似乎在放孟加拉的节目。几个孟加拉人坐在会客室里,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谈笑着。柯修走开了。我们有些忐忑地坐在角落里等着,傻傻地假装看电视。
并不很久,柯修进来找我们。“一秘想与你们见见。”他说。然后领着我们出去。片子一看到那个一秘就在我耳朵里喊帅。发现对方正在走近,忙闪到我后面。我又急又怒,支吾了两句英语,说我们是志愿者,希望他能来参加国际文化节。一秘先生(后来知道他叫菲亚兹·卡兹)很温和地微笑着与我握手,并且说你的英语很好。我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天,这种差事应该让纯良来做。幸好会面很短,我不用想下一句说什么,就可以用上“谢谢”和“再见”了。
我们帮柯修把展品从使馆搬进出租车,便算大功告成。要命的是归程上让人难堪的沉默。
“我希望你们不太介意,我不太会说话……不太会中国话。”像是刻意要打破沉默,柯修有些支吾地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卷招贴画。”
我和片子有些笨手笨脚地把招贴画展开。第一幅是孟加拉地图。Bangladesh.
我轻声念了出来。
柯修笑了一下,然后指着地图上密布的河流:“河……孟加拉有太多的河。
每到雨季,上游所有洪水都涌向孟加拉……你知道的,洪灾,没完没了……还有风暴……”
第二幅是孟加拉的简介。
“人口……孟加拉有近1.4亿的人口。孟加拉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柯修自顾自地说,眉头紧锁。
柯修终于不只是沉默了,可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翻到一张孟加拉虎的海报。
“有名的孟加拉虎!”我说。
“这儿还有一只更大的。”柯修笑,拿过一张黄麻织的有孟加拉虎形象的挂毯,“总是这样,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两种象征性的动物。不只是动物,还有人,物,景。当哪里又举行什么国际性的会展了,他们便把那些象征性的东西挂出去,好看的,光艳的,堂皇的。”
那天回程,柯修一直轻柔地断断续续地说着,填补着难堪的沉默。可也许,与其说柯修在向我们介绍孟加拉,不如说是在自语。
跟片子一起告别柯修,我们回头看他。看到一个瘦瘦的背影驼着一大堆东西消失在拐角。低着头,弯着腰,看着路。
文化节当天,纯良极其不负责任地一直到九点才出现。片子说她对柯修印象不错,便屁颠屁颠地跟着我来了,一来就后悔。马伊努果然真把我们当成免费不收钱的帮佣,让我们去给他们搬张桌子。妈呀。展台可是设在百年讲堂广场,要搬一张桌子得跑小半个学校!无奈,我跟片子两个弱女子本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跑了半个学校到艺园搬桌子。二楼不行,三楼没有,一直到四楼才找到一张合适的。
我跟片子嗬哟嗬哟地把桌子从艺园搬到讲堂门口,小命去了半条。脸皮犹如地壳的纯良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