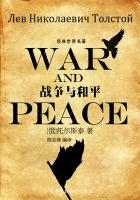热血男女在一起,就像汽油跟火的关系,它们很可能各自操守自己的使命,没有任何联系。又很可能有最紧密的联系。它们可以互为独立,也可以互为同谋、互为利益伙伴。
敢去么?贾界问。
去就去!去了又能怎样?房美月说。
虽然有柳明名捣乱,虽然有太多男同学积极参与并企图“策反“、拆台、篡位,两个人毕竟恋爱那么久了,连吃饭都共用一个汤匙、一双筷子,总之,贾界得手后总结道:我是占了得天独厚的便宜。
都熟成这样了,到底有没有家信,房美月也不再问了。
在公园僻静处的草地上,贾界一只手抱紧房美月,另一只手隔着衬衫轻抚房美月的乳房。房美月一抬手,啪,打开了侵略者。贾界嘿嘿嘿笑几声,冒火的眼睛直盯盯看着她的高高凸兀的双乳,说,我、我受不了啦!
房美月敏感地一下子挣脱他:老实点!
热血沸腾的贾界什么都不顾了,一下子扑倒房美月,猛地压住她,双手掀起衣襟,掀翻乳罩,两个大而尖挺的乳房豁然裸现!
当它们分别成了一只手、一个唇的俘虏,它的主人突然忘了恪守和反抗,猛然间合拢了开关,浑身电流腾跃,酥痒得要死!刚才还恐惧的包装一下子被撕开,只剩下听之任之……哦,惊悸和颤栗怎么换成了旷世享受?清醒也没用了。电闸合拢后,清醒握着优犹寡断——怕触碰又希望触碰,怕着火又希望着火,怕开始更怕结束……
过后,贾界说,美月,你这两个尤物是世界上最美的乳房!那时,贾界还说不出“波霸”的流行词呢。
贾界又说,美月,什么都不用,你这对东西,就能拴住我一辈子……
如今,话犹在耳,现在他们即使同床而眠,也常常如远隔千山万水!
房美月出了楼洞口,白条鸡已走到楼侧的“坏肾”处。白条鸡的头上,正是翻色的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追上白条鸡后,房美月笑了笑,说我有事请教你呢。
请教我?白条鸡瞪大惊骇的眼睛,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以为听错了。
房美月亲切地点了点头,又轻轻摸一下白条鸡的手,说,等我一下,我向单位请个假。其实,房美月是躲在另一个楼拐角,看见贾界钻出楼洞口,目送他向另一个方向拐去,身影消失了,才赶紧走出来,和白条鸡招招手。
你――,在躲他?白条鸡问。
房美月眼窝一潮,连忙咬紧下唇。白条鸡一下子拉紧房美月的手腕:小妹,不要怕。有什么事,姐给你撑腰!
房美月真想一下扑进这个女人的怀抱,放声大哭。至于她是谁,她能帮她什么,都无所谓。现在,她只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怀抱,一个给她撑腰的人……
在一家小饭馆,房美月向白条鸡请教了类似的问题: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男人为什么忽冷忽热?难道每个男人都一样,在得到了女人的身体后,就不再喜欢这个女人了?
白条鸡毫不保守,有问必答。可是,个个跑题。说来说去,白条鸡只说她接触的嫖客。各种类型的嫖客。她说的最多的,是她的乳房。例举了好多的实例,都是从她的乳房说起。最后归结出:大部分男人,都喜欢大乳房的女人……
说这话的时候,白条鸡不时还晃晃上身。她的大乳房随之跳上跳下,像两张蒙着盖头的脸。
房美月仔细看了看,大。真大。可是,那两个被无数身体蹂躏过的东西,早就如同解开衣襟敞开怀的女人,没收没管……
半天就这样耗过去了,白条鸡的话流水一样滔滔不绝。可是,这滔流被一道看不见堤坝挡住了……
离开白条鸡后,房美月的脑袋里只增加了一条信息:白条鸡开始干“旧物回收”了,收益还不错。
“旧物回收?”
哦,就是捡破烂呀!哎呀妹子,这个来钱好快哟!
房美月说,谢谢你,陪了我半天。
哎哟,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面对房美月惊讶的眼神,白条鸡说,要不是你听呀,这些话都快把我憋炸啦!
哦,两个不同的身体,一样苦闷的心!
在这个浮躁的城市,除了钱和性都不在话下的城市,苦闷像在空气中飞行的流行感冒病菌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柳明名想在我们杂志社“掏一把”吃了我的软钉子后,又奔婚介所去了。好在沈阳城市大,婚介所有的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东方不亮西方亮。现在,柳明名由初级的迷恋女人的身体,经过约分、化简合并同类项后,只迷恋女人的钱。但,他最苦闷的是,像样的“拿不下”,“拿下的”都不像样。在一次酒后,他团着舌头跟我说,有朝一日,我要是能靠上个“女大款”,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吃软饭?我问。
我操,别说得那么难听,钱才是硬道理呢!柳明名的眼睛通红通红,融着玻璃窗不断扫射匆匆路过的女人,一个不漏,仿佛他要猎获的“女大款”就在其中……
看我不认识那样看着他,柳明名说,别挂个“执行主编”的头衔就乐出鼻涕泡了,你跟我一样也是磨道上的驴,离开钱,你就玩不转啦!
柳明名尽管说得对,我也不愿意承认。我口是心非地说,我们可是主流媒体呀,哪像你,除了……
柳明名十分不屑地向我摆摆手,说得得得,阻止我再说下去。然后,他咕嘟嘟灌下去一杯啤酒,哈哈哈大笑一气,说,你可真能攀高枝呀,一个自负盈亏的杂志,也敢称什么“主流”?别拿大奶头吓唬小孩子了!如果国家财政不掏腰包,地方财政也分文不拿,还算主流么?自己打食吃,饥一顿饱一顿的,见了钱能迈动步?一心向钱看的媒体是什么?就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躲在钱的裤裆里把握方向盘……
少说这些没用的,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合作?
你们杂志是打着公家旗号干自己的事,我呢,是打着自己的旗号干自己的事,这不一样。你们的旗号好唬呀!
柳明名最后一句话永远留在我的耳边:老同学,挑干的捞,我的忙,能帮不?
贾界一直陷在苦闷里。
那些日子,总跟房美月叨叨佟大志。
讲排场的贾界以为自己两万块就“搞定了”佟大志,不料却让佟大志抢先买了单。掉过来说,是被贾界搞定了。让小民工买单,还让人家搭上三千块。这么大的老板请客,张罗了大半天最后弄成这样,贾界觉得很没面子。贾界轰走了秘书后,直接叫来房美月,问她怎么回事。房美月知道这是贾界发疯的前兆,立刻把头摇成了货郎鼓。此后,任凭贾界调着方地问,房美月都以不变应万变,摇头。
那时,房美月知道贾界的心早就飞了,真诚不再。哪怕在一块儿的时间很短很短,也常常走神儿。就连做爱都三心二意的,不是应付了事,就是做广播操一样平淡,走走过场。就这,还常常弄成“半截子工程”。尽管睡一个被窝儿,可他醒来后那空洞的眼色,已预示这个最近的男人很可能渐行渐远。
但,房美月仍然没有二心。
“他是他,我是我。”这句自我安慰的话,可能扯出一串子眼泪。但,这仍然是挽留、留恋和期待回心转意的眼泪……
不过,房美月清楚——不,是女人都清楚,当自己的身体产权专属于一个男人时,千万不要说另一个男人的好,尤其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男人。
关于佟大志的事,他们间一直是清白的。当年上大学前,房美月曾经有过打算,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佟大志。但,佟大志拒绝了。以后,再也没有必然历史的机会了。后来,如果说房美月此时的确向贾界隐瞒了实情,也是善意的。不然,她怎么应对贾界的话:我要是叫不来佟大志,“我是你养的?”
“到我这儿抢什么风头?”这是贾界那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此后,贾界无论用什么招子,也兑现不了“救救这个民工”、给他月薪一万的承诺。最后,当着房美月的面摔完一只杯子后,说佟大志这个家伙,瘦驴拉硬屎,嘴叼狗屎给麻花都不换!见房美月不为所动,贾界步步紧逼,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起初房美月一直沉默。没有退路了,房美月才告饶:贾界,你就别熊我啦!
苦闷也是恋旧的家伙,一旦被它看好了,就会生根发芽。
贾界公司开张后,房美月就想辞了幼儿园的工作。“压寨妇人兼掌包的”的话虽然太江湖了,可毕竟跟实力和亲昵结伴。可园长冯中强说,我的事业刚火起来,你一走,不是撂我台吗?
房美月说“我也不爱走,可老公摧得紧哟!”
园长听说过绿野公司,也在电视上看过贾界。但,她从来没跟房美月对上号。现在房美月没直说,她仍然对不上号。最后,园长说,你是我们园的顶梁柱,你一走,园里肯定要受影响的。我知道留不住你,但你能不能看在姐妹情份上,晚走几天?
房美月答应了。
“尽快找人”,别撂了孩子们。这话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个短暂的承诺,却把她拖住了。
那些天,贾界一回来就敲敲打打:行呀,个头矮了,层次却高了。不再跟妓女打成一片,一心培养革命后代啦!
站好最后一班岗。房美月一直这样想。
宁可跑好远的路,也决不迟到。哪怕下了大雨,她也会准时到达。房美月恨不能立刻离开这里,省得贾界抓话把。但,她又怕离开。她喜欢那些可爱的孩子。孩子们天真的样子,水儿一样,能洗去污浊,洗去烦恼,洗去忧虑。时日,就常常在这样的犹豫中穿梭而过。犹豫分散了心思,也分散了目光。出事了。
这天下午,她正领着两个孩子看马路对过的电子招牌时,因忽视了闪亮的红灯横穿马路,被突然拐过来的一个摩托车剐倒……
自己的腿和胳膊少了两片皮倒没什么,曾经成功出演过《小白兔》男一号的孩子右肘骨折……
那个瘦医生说,这个地方叫“鹰嘴”,一旦落下病根,胳膊就伸不直了。瘦医生还举了个例子,说知道周恩来的胳膊为什么直不了吗?毛病就在这儿,“鹰嘴”坏了。
园长一听,立刻犯了心脏病,要不是及时塞嘴里一大把救心丹,她就告别这个世界了!
闯下这个祸还怎么走?
在贾界面前,房美月只好以“新老师来了我就走”为由,捱着日子。房美月再三跟家长说,药钱她拿。男孩子恋房美女,家长也爱屋及乌,一口咬死“跟房老师没关,我只跟你你园长算账。”
园长病卧在床,怕上火,怕气,怕急,气都喘不匀,还怎么算?
多亏园长老公及时出手,一个海底捞月,一下把问题托出水面:一切都由园里承担,好说好说的。园长老公笑了笑,又补充道: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在场的房美月和男孩子家长一听,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园长老公姓胡,名长海。个头不高,小头挤脸的,眼睛似有似无。总之,哪都小。但,说话办事真痛快,就一个字:爽!
胡长海说,我把好好的生意放下,就是要整明白这事。什么是大事?明天才是大事。什么是明天,孩子才是明天。这了这个,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
胡长海还以“代园长”自居,要“生龙活虎”地接手幼儿园工作。胡长海甩给男孩子妈一万块钱后,还甩给房美月一万块。房美月虽然没要,但也深深地感动。自己闯了祸,人家根本没当回事。啥也别说了,知恩图报吧!每每胡长海布置的事,房美月非常配合。那天下班后,当房美月被叫到胡长海办公室,胡长海突然关了门,笑嘻嘻地迎上来。房美月觉得不好,还没来及叫一声,胡长海就猴子一样窜上来,一下把她扑倒在长条沙发上。房美月一声“你等等”,趁胡长海愣神的工夫,翻身站了起来,掉头就跑。哪里跑得了?在男人中,胡长海只算个瘦小的“微型”,可在女人中,他可是大力士了。胡长海一把搂住房美月后,一只手已经按住饱满的乳房。房美月大声喊着“不!不!”,却抵挡不住进攻。胡长海的腿伸进房美月两腿间一别,顶得房美月大腿里子生疼,稍一松懈,她的衣襟被解开,两只大大的乳房脱兔般跳了出来……
“不!不!”无论房美月怎么叫,都抵挡不住胡长海预期的计划,很快,房美月的裤带被解开了……
就在胡长海激动得呼呼喘,就要撕开内裤时,房美月绝望地一声大叫:贾界,你在哪里呀,哦哦哦哦……
房美月不再挣扎了。
碰上这样的男人,女人的挣扎无疑是徒劳的。
除了绝望和哭泣,房美月还能干什么呢?
可是,胡长海也停止了动作。
胡长海的脸立刻白了:贾界是你什么人?
房美月见形势有所转机,也急中生智道:我男人!他,他会杀了你的!
胡长海哆哆嗦嗦地说,就是那个、那个绿野公司……
对呀!
房美月在慌乱中站起来时,胡长海却矮了下去。
啪啪啪啪,胡长海跪在地上,接二连三地打自己的嘴巴,央求房美月,看在他老婆心脏病很重的份上,饶了他吧……
那是一个风黑月高的晚上。
眼见要毕业了,我们几个要好的捉个通宵。在那个低档小饭馆猜火柴棍,划拳,嚎歌,跳舞,喝酒。说“嚎歌”,除了因发泄过猛而不着调外,还因为那时的小饭店没有卡拉OK,干唱。那时,还没有现在满街满街的专业歌厅。为了尽兴,我们连手指头弹脑壳、鼻子上贴纸条、钻桌子那些老掉牙的游戏都用上了。
上酒店之前,带不带柳明名的问题,我们曾犹豫过。怕“马户单刀”不高兴。毕竟,这小子没少捅漏子。没想到,贾界竟然十分大度,怎么能少了柳明名呢,带上他带上他!不管怎么说,我们可是一个车道沟来的啊!抚顺的胡力韦也来了。说实在的,胡力韦根本不搭界,即不是老乡,跟我们也不是太近,怕他感情“抽条”。但,胡力韦是班里着名的“和事佬”,亲和。都快散伙啦,上赶子跟我们“辽北帮”套近乎,这一点就够了。我说,来吧老胡,我们欢迎你!平时我们都吊儿啷当,严格遵守“60分万岁,61分浪费,59岁犯罪”的基本原则。让酒精给泡得肿眼咣当、天旋地转之时,胡力韦砰地一声咬开一瓶啤酒,瓶嘴朝下对准自己的脑瓜盖,眼见他头顶冒白沫,酒液飞炸,脸上水淋淋,才晃晃头说,“我提议,十年后我们还在这里相聚,现在,我提议,大家预测一下十年后我们各自的情况吧!”
“十年不错。那首《二十年后再相会》不好,二十年太长啦!”房美月说。
现在才知道,十年都太长。同学会只坚持了五六年,再也没人提起。偶尔有人张罗一下,曲高和寡,响应者寥寥无几。毕业十年后,没人提起我们当年的话。十年后,我掐着指头算了算,没一个人预测准的,个个都脱了靶!贾界早已安息在天福乐园,那个在绿茵场上驰骋的马户单刀还在当“前锋”,在赴天国的路上;胡力韦到深圳闯天下,干得还真冲,当上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策划,月薪三万,吃喝嫖赌全报销。可惜,同时被三把尖刀扎成“蜂窝”,误伤。他的后半生,将在轮椅上度过;房美月回西丰老家,跟那个老鳏夫“第十一”打发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岁月;柳明名在开原精神病院,有时往脸上抹大便,有时捡树叶做书签;我也不比他们好多少,在文人“百无一用”的时候,我还在爬格子混粥喝——更可悲的是,有时为了顺应单位头头,我或避重就轻、或说违心之话,拿自己的灵魂当敲门砖……
十年前,贾界以“眼白”为桥,踏上了通往富比王候的路;胡力韦常常唾沫星子喷飞地在深圳的大学里演讲,唬得小师妹们直往上贴;柳明名在婚介所跟女人玩打游击,把婚介女老板都给划拉了;房美月作着“贾大款”压寨夫人的美梦,看见右下巴有痦子的女人就想叫声妈;我不时为得个什么奖项乐得跟雷蕾扭在一起,跳舞、喝酒、做爱……
十年前,我们已经毕业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