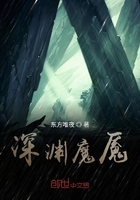“我当时要是回那儿去,也就在那儿留下了。这是实话。我坚持了那么久,打了一仗又一仗,从没有躲在人家后面,从没有投机取巧,现在竟干出这种事来。干出这种要命的事来。干了这种事人家不会白白放过我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经干了,要想挽回也来不及了。”
他闭上眼睛躺着——这样说起话来可以好过一些——他心里怀着按捺不住的怨恨,却无处可以泄愤。
“可是你怎么,怎么这样胆大包天?”纳斯焦娜忍不住问。“这可不是小事。你打哪儿来的胆量?”
“不知道,”他迟疑了一会才回答,纳斯焦娜觉得他并非瞎说。“我忍受不了啦。太想见到你们了,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要是在前线,我当然不会开小差。可是到了医院里,我觉得家乡似乎就在附近。可是哪在附近呀?我搭车走啊,走啊……回部队还没有这么远呢。我并不是存心要开小差的。过后我意识到,怎么能回部队去呢?回去送死。那还不如死在这儿的好。现在还有什么好说呢!自作自受嘛。”
“等仗打完了,他们也许会饶恕你的,”纳斯焦娜没有把握地说。
“不,这种事他们不会饶恕的。为了这种事,如果一个人给枪毙以后没有送命的话,就要枪毙他三次,好让别人不敢再犯。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现在用不着再为它操心。我一路往回走,一路在想:我回到家乡,见一见纳斯焦娜,请她原谅我毁了她的一生。本来可以活下去,好好过日子,我却无缘无故折磨她,自己也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说真的,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咱俩都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应当快快活活地活下去嘛。可我却不这样,偏偏要使性子,自作主张。真蠢。我自己也明白这样做真蠢,我到底还不是个十足的笨蛋,还有一点脑筋,可就是欲罢不能。我本来以为咱俩是有奔头的,尽可以活下去,尽可以相亲相爱个够——日子长着呢。这下子叫你有奔头去吧。我本来想,我回到家乡,会一会纳斯焦娜,向她认罪,叫她不要把我看成坏人,再打暗处偷偷地望父亲、母亲一眼,然后就一头埋进雪堆里去。让那些野兽来把我收拾掉,不留下一丝痕迹。至于像这样跟你在一起——我可没有指望过,连想都不敢想。我怎么会有这份福气?就凭这一点,要不是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的话,我真该把你当宝贝似的捧在手里。”
“瞧你说的,”纳斯焦娜插嘴说。但是他打断了她的话:
“等一等。我既然讲了,就应该把话讲完,以后也许没有机会啦。我现在没有必要瞒这瞒那了,用不着。有什么心事,通通说出来。你听着。我本来只想回到家乡过几天,请求原谅以后就告别,现在我却很想多活些日子,活到夏天。最后一次看看夏天是什么样子的。总而言之,很想——哪怕毙了我。今天你给了我温暖——正好让我高高兴兴地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他呛了一下,咽下堵住喉咙的口水,沉默了片刻。“我不需要你为我做更多的事情,纳斯焦娜。即使这样,你也已经为我做了不知多少事情啦。你再忍耐几个月,替我保守保守秘密,时候一到,我就会消失的。不过,暂时你只好忍耐一下。你已经为我忍受了不少痛苦,就再忍受一下吧。”
纳斯焦娜觉得该抱怨他几句,数落他几句才是,可是不知怎的,一点也不想开口,两人共同承受的痛苦压抑着她,她默不作声。他迟疑了一下,见她不作声,便又继续说下去:
“咱俩以后不能在人前一起过日子了。一天也不行。什么时候你想我,心疼我了,你就来吧。我是巴不得你来的。我不能在人前露面,哪怕要咽气了也不能。别的事我都无所谓,可这件事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不愿意将来让人家对你,对父亲、母亲指指点点。我不愿意让人家猜测我怎么藏起来的,来搜寻我的踪迹。让人家添枝加叶、说长道短地议论我,我可不愿意。”他欠起身子,在铺板上坐了起来,他的脸变得尖削了,脸色发白。“你听好,纳斯焦娜,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不要对任何人说出我曾经回来过。对谁也不要说。不然的话,我就是死了,也要来找你算账。”
“你怎么啦,安德烈?!你怎么啦?!”纳斯焦娜吓坏了,也坐起来,现在他俩并排坐着,臂肘挨着臂肘,她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好像是在胸腔里边嗡嗡响着。
“我不是吓唬你。我怎么会吓唬你呢,纳斯焦娜?!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幸福和安慰。不过,你要记住,永远记住:不管我是死是活,别忘了我这一生的不幸和苦难。将来,等到这一切全都结束了,你就可以重新安排你的生活。一定要重新安排,你的日子还长着呢。说不定,有朝一日,你日子过得非常好,为了报答人家给你带来的幸福,你会忍不住把你的身世通通讲出来。但是我这件事你可别提起。只能让你一个人知道我的真情,其他的人,让他们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吧。你可别告诉他们。”
“安德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气得你要这样跟我讲话?”纳斯焦娜问。她惊慌失措,不知说什么才好。她脱口而出的这句诘问的话,纯属女人家的口头禅,与其说是抱怨,不如说是哀求,而且语气又是那么悲戚。但是安德烈听了却挺高兴,这句问话说明她是顺从他的,这使他完全放心了。
“你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也没有做。别生气,用不着。我知道你会明白我的心思,会正确地理解这一切。我下次大概不会再讲这些话了。可是现在不得不讲清楚。现在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干吗这样做。好像活着的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他钻进了我的躯壳,随心所欲地支配着我。我要向右拐,他偏偏不许,硬逼着我向左拐!唉,算了,反正日子已经剩下不多了。”
“你怎么老说些吓人的话……”
“别怕。我不是吓唬你,我是在吓唬自己。不过也没必要吓唬自己,不会再有更可怕的事情了。我这是在你面前泄了气。不过,该说的我全都说了,该提醒你的全都提醒了。人也觉得好过一些。现在你说吧。”
“说什么好呢……”
“母亲怎么样——能下床走动吗?”
“这一年来,几乎一直躺在炉炕上。只有烧饭的时候才起来。她不放心我发面,非要亲自动手不可。也许,我一辈子也学不会烘面包了。”
“父亲还在马棚干活吗?”
“是的,要是没有他,他们早就把所有的马全整死了。只有他一个人照看马。他身体也差劲了,老是气喘。他劳累得够呛。再加上我前天还给了他当头一棒。”
“怎么回事?”
“认购公债呗。我一时糊涂说走了嘴:一下子认购了两千卢布。我这个人脑子简单,心想:钱还不知在哪儿,有啥好心疼的。可是他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认这么多。他可高兴啦,不消说,还夸了我两句,”纳斯焦娜歉疚地笑了笑,瞥了安德烈一眼。
“你暂时别扔下两位老人家不管,”他说着,脸色又阴沉下来,沉思了一会儿。“母亲大概拖不了多久了。得想办法偷偷地去看他们一眼。”
“安德烈,往后怎么办呢?”纳斯焦娜怯生生地问,这个问题把她自己也吓呆了。“他们可在等着你,盼着你,以为你马上就要写信来告诉他们你在哪儿。可是等战争一结束,他们又该怎么想呢?他们的盼头全在你身上啊。”
“盼头,盼头……”他一下子跳起来,在屋里来回踱着。“他们什么盼头也没有。完了。没有了。关于这个,我刚才已经讲清楚了。至于我人在哪儿,你听我给你讲件事。我们医院里住过一个大尉。人家给他治好了伤,就把证件交到他手里——也是要他回部队去。第二天,发现那些证件全撂在邮筒里,大尉失踪了。他上哪儿去了?连老天爷也不知道。也许有人看中了他的军服、钱财和口粮,把他给杀害了;也许是他自己销声匿迹,躲起来了。反正有过这么个人,现在却不知去向了。你问谁去?一个大尉算得了啥,眼下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没法找到。有人在天上,有人在地下,有人在人世间受煎熬,有人躲了起来,有人连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谁——全都搅得一团糟,上哪儿找线索去。我也是这样:好像还在世上,又好像不在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那两位老人家用不着等待我多久,就可以跟我在阴间团聚了,到那时候我再同他们好好地谈吧。也许那儿没有战争。而在这儿,不管是弱者还是强者,都只有一个盼头,那就是盼你自己,再也没有别的人好盼了。”
纳斯焦娜想反驳几句,却拿不定主意。安德烈沉默了一会儿,稍微平静一些,又说下去:
“还不知道是哪种情况好些:是确切知道儿子或者丈夫给打死了好,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好?做妻子的,大概是巴望让她知道的——她好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这也难怪她:你自己没法活下去,就该让她好好地活下去。不要耽误了她。做母亲的呢?有多少母亲宁可不知道,蒙在鼓里糊里糊涂过日子。做母亲的,即使收到阵亡通知书,也不愿意相信。即使指给她看儿子埋在哪儿,即使掩埋他的同志写信告诉她,她还是不相信。既然我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去看望我那两位老人,那还是让他们对我存一线希望吧,哪怕是十分渺茫,但总是一线希望。”他朝纳斯焦娜转过身去,把手一甩,说:“算了,这件事就谈到这里。你下地来,咱们喝茶吧。你很快就该上路了。你走吗?也许还是留下吧?”
“我怎么能留下呢?”
“你还来吗?”
“来的,安德烈,我要来的。要是没有车,我跑也要跑来的。现在我已经认识路了。”
“要是不想来,就别来。这种事不能勉强。我受得了,今儿这一天就够我回味很长一阵子了。”
纳斯焦娜忽然想了起来:
“哎哟,我给你带来了弹药。差一点儿没把它再带回去。”
她轻巧地跳下铺板,在门角那堆东西里翻出两个粗布小口袋,里面装的是火药和霰弹。“你倒一半去,另外一半我要带给父亲,是他叫我买的。”
“我一半就足够了,”安德烈喜出望外,忙着摆弄两个口袋。“这下我可以活下去了。现在哪怕是魔鬼我也不怕了。瞧你给了我多好的东西。你把一切都给我了。嗳,纳斯焦娜,你真是我的好妻子!”他一把抱住她,微微地举了起来,她挣扎着,尖声叫着,他立刻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下来,苦着脸自言自语地说:“有这么个妻子该堂堂皇皇地在人面前过日子,而不该偷偷摸摸地躲在地洞里。”
“瞧你!”纳斯焦娜没有听到他在嘀咕什么,管自激动地说。“把我吓的,简直连灵魂都出窍啦!我已经不习惯被人这么抱了。”
“你常常来,我会叫你习惯的。”
“我倒是愿意每天都来。”
“那干吗不来呢?”
这次长达一整天、但仍然觉得很仓促的会面该结束了。天已经擦黑,屋角里散发出的霉气越来越浓,翘棱的天花板仿佛下垂得更加低,更加摇摇欲坠。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诡秘,那么难以捉摸,使人心惊肉跳。谈话渐渐地停了下来。
他俩匆忙地喝了点茶,安德烈一定要纳斯焦娜吃点东西,纳斯焦娜食不甘味地嚼着脂油和面包。当她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安德烈默默地递给她一只圆滚滚、亮晶晶的东西,上面有些像小眼睛似的闪闪发光的小点子。纳斯焦娜轻轻地惊叫起来:
“哎哟,这是什么怪物?”
“拿着吧,纳斯焦娜。这是表。是我亲手从一个德国军官手上摘下来的。是从活人,不是从死人手上摘下的。我再也用不着它了,它对你可是有用处的。你要是把它卖掉,可别卖得太便宜:这是只好表,瑞士货。不出到两千卢布你别卖掉。”
“天哪,连拿着它都叫人提心吊胆。”
“拿着吧。别的没有什么好给你了。”
他一直把她送到安加拉河边的路口,在雪橇里拥抱着她,一动不动地过了一会儿,然后朝卡里卡抽了一鞭子,便跳到雪地上去了。他久久地目送着逐渐远去的小黑点,呆呆地站立着,他的脸也是呆呆的,思绪中断了,停滞在一点上:唉,这算什么……
……纳斯焦娜一边赶路,一边哭泣——她的心碎了,可一时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难受。心头的每一阵痛楚都使她不知如何对付才好,——整个人都被一种隐隐约约而又贯穿全身的惊慌紧紧地缠绕着。这好比是在茶水里放了对半的糖和盐,一股脑儿喝下去,五脏六腑一下子就收紧,憋住了:顿时甜酸苦辣,各种滋味混杂在一起。刚刚尝到一点甜味,立刻就叫咸味驱走了;一阵悲痛传遍全身,一直渗透到骨髓。
多少年来,纳斯焦娜一直被拴在村子里、家庭里和劳动上,她是个守本分的人,从不越雷池一步,因为她知道,有些东西多亏有了她,才牢牢地结成一个整体的,可是现在,绳索忽然松开了——虽没有完全解开,但是已经松动了。只要有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干你想干的事,去你要去的地方。可是,到哪儿去呢?去干什么呢?她早已习惯于对她的羁绊,早已适应,再说,即使下决心出去走走也走不到哪儿去,何况又无处可去。所以,怎么能不叫她张皇失措呢?不,看来绳索是不能去掉的,应该把它收紧一些,瞧瞧以后会怎样。她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的。现在她还是只好在原来的圈子里打转,虽然如此,她却又好像成了圈外人,冷眼旁观着别人怎样生活,而自己过的生活却是与众不同的,不可告人的。因此得睁大眼睛多多提防,话到嘴边要掂掂分量。干活要加倍努力,睡觉可要减少一半。而且还必须玩弄花招,支吾搪塞,说谎骗人,尽管她事先就知道这会落得什么下场。
一切都是为了让丈夫得以苟且偷生。
凡是人,都有罪过,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人。可是,能犯这样的罪吗?这罪,安德烈是经受不住的,显然,是经受不住的。他这心灵的创伤是愈合不了的,永远愈合不了,这样的罪他是担当不起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和他一刀两断?不管他的死活?他回到家乡来,也许她也有罪责的吧?——没有罪,但是有罪责。他之所以牵肠挂肚地想回家来,不主要是为了她吗?他担心永远见不到的,担心不能与之诀别的人,不就是她吗?他连父母都不让他们知道他的下落,却让她知道。也许,他正是为了要跟她团聚几天,才将死期推迟的吧?既然如此,怎能拒绝他呢?要拒绝他,除非是完全没有心肝的人,把心肝换成了天平秤,才对什么事都要称一称:对自己有利可图还是无利可图。现在这种情况,即便他是个陌生人,而且道德败坏透顶,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撒手不管,何况安德烈是自己的亲人。把他俩结合在一起的,是老天爷,或者是生活本身,为的是让他俩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遇到什么灾难,都要风雨同舟,相依为命。
人们都生活在那边,而他却在这边。主啊,教教我怎么办吧!
纳斯焦娜心情沉重、不安,同时又空虚、落寞——就像一间给搬空了东西的房子,可以随便怎样处置它。这种空虚既寒气逼人,又具有诱惑力,每一个念头都会在光溜溜的四壁上面引起很响的疑问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