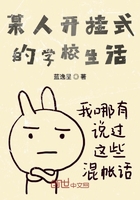长干一曲
妹妹和我说阿正近日里就要结婚了,我不禁咋舌,一面也为他高兴。“那我也要去吃他的喜酒。”妹妹看我一眼,正色地说:“你最好不要去,免给人难堪了,他看了你去,不是要伤心吗?”我好讶异妹妹怎么这样说,“你说哪里去了,我好为他高兴,待会儿我还要上街买礼物呢。”妹妹看我仍说呆话,更正色地说:“你这人真是的,别太幼稚过头了,大前年他不是一度写许多信给你,你竟也看不出人家的意思,还说了些令他丧气的话。后来他写了一封信骂你,我还记得他口气有多恶意,你反而不记得了,还要去送礼,你是存心栽人还是健忘大王?”我这才记起他曾经写了一封信骂我,骂我骄傲自大,骂我不识大体等等,我只是不回信,他后来倒也同妹妹说了,是他不对,才一时写了那些气话,但妹妹还是不饶他,我是很快就把这事忘了,也不对他生气,妹妹反为我抱不平,誓死都不与他和好。我好像很赖皮,不善记仇,就像小孩子狠狠地打了一架,隔不了半天,又同在一淘玩耍。我性子比妹妹不坚定,她是勾践型的,我却散漫不成型,人家对我好,我记得,对我坏,我常记不住,大概是那种柔弱无能的软性子。而这回阿正的婚事,我打从心底为他觉得幸福,妹妹可也不能知我心意,只当我是不辨正邪,但是他的的确确是阿“正”呀!
阿正长得很白很好看。记得小学四年级时,一天傍晚放学回家,发现一位长辈带着他儿子来我家玩,那男孩很害羞很端正地坐在一边听大人说话,是那种白面书生型的男孩,我们笑他可以扮关帝庙里的“掌笔太子”,一张白皙皙的圆脸蛋,不久他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他和二哥同年纪,我退了一阶给他排,他很得意,便爱喊我“阿五”。因为他生得好看,原来就不好看的“阿五妹妹”相形之下便格外显得丑。我很自卑,但我当他是自家人便安心些,因为自家人只能如此,奈我无何,于是十多年下来都这么以为,不敢视他为外人,倒也落得自在无事。
有一年大年初一,大清早阿正就跑来报到,穿着笔挺的黑夹克,藏青色毛质长裤,新皮鞋,方方的褐色眼镜框,真个潇洒好看,我再看看自己穿的黑长裤、米黄套头毛线衣、学生头、学生鞋,还穿一双白条纹袜子,一副土样子很不如人。正在踌躇时,阿正从皮夹里抽出一张亮新的五块钱,说:“阿五,三哥哥给你压岁钱。”我好感动,接了来红了一脸,妹妹也在一旁,阿正却没给她,难怪妹妹一直对他有微词。其实妹妹比我生得好看,阿正却偏只给我压岁钱,我也一直不懂,但是为此我始终感激他待我的不薄。
日记里我常会写起他来,但也只有天知地知,因为他是“太子”型的,是注定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小生,而我是花旦,一辈子要奔波劳碌的,是两个世界的人,这辈子是无缘定了,只为偶然的际会,一旦长大还是会面临完全的未知的。但在那段长长的日子里,我还是最在意他。有一回家事课做熊娃娃,我选了刺目的大红绒布,缝做了一只短腿短手大耳朵的小熊,分数打完了抱回家,我就把它送给阿正了。他笑我做成了个丑狗熊,我知道做得不很细致好看,但执意请他带回家做伴,阿正看我给得快哭了,果也抱在左臂上特地骑单车带回去。如今狗熊如何了?我想大概还在阿正的阁楼上,也许塞在衣柜顶上吃灰尘,仍在那儿的,只是今天阿正已有了另一个家,他不会再住那阁楼的,我那丑狗熊便也要落得身份不明,甚至下落不明呢!
《礼运大同篇》里的“男有分,女有归”,我一直很相信中国所以“厚生”便是从这一句衍生而来的,这六个字好像定了两个位、两个点,可以连接起来成一直线,时下婚姻制度的繁复,我想也许是出在那两个位、两个点的不完全连接。旧式的媒妁婚姻便是先肯定那两个定点,然后一定可以连成最短的直线。
再说阿正的婚礼我到底决定不去了,也不是因为妹妹的一番话,而是阿正始终没有送帖子来家里,我纵使要送礼去也成了私意的。也许阿正还是认为我仍记得那封信,因为妹妹不饶他,如果送帖子来会惹火妹妹的牛脾气,又我如果送礼去更要令他不解了,彼此为难,反为不好。但是我实在为他雀跃了好几天,恨不得快些认识他的新娘子,既然阿正是小生型的,他的新娘一定要是青衣的柔媚倩美,我这个花旦只配在青衣前面领路。可惜没有人邀我去参加,我也不怨谁,只在家里大声朗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男有分,女有归,货恶……”最后添上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