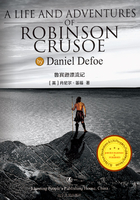人才是人群中的智者,人类中的精华。才并非博学,而是他们的天分高于常人。他们的能力超凡,他们是社会各个领域的标杆,他们以自己的影响成为社会的核心。他们遵从的只是天的规则,大自然的规则,道的规则,而不是人的规则,人的规则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许多原本弱势的集团因为得到了人才,从无创造了有,从有创造了大,从大创造了强。也有许多原本强势的集团因为失去了人才,举措失当,危机重重,优势不断流失,强势中渐显败象,最后导致消亡。关键就是这个思想的核心:人才。
人才既然是决定成与败、盛与衰的先决条件,人才也成为对垒双方争夺激烈的焦点。对人才的发现、招揽、使用,也成了生死存亡、强衰进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古来如此,于今尤甚。我在百度输入“人才”二字,迅即搜出网页上一亿个结果,可见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才争夺战的白热化程度。
那么,社会既然如此急切地需要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无数集团又是给人才开出了极为优惠的价码,又是万人翘首以盼的焦急期待,如同旱天翘首以望云霓,人才到底都窝在哪里呢?为什么藏着掖着不肯面世呢?
人才真的是稀缺物质,藏匿在千山万壑、重重山水中踪迹难寻吗?非也。人才虽属于稀缺一族,却并非罕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之所以奇缺,只是缺少发现的慧眼,这双慧眼具有X光的透视功能,能从平常中看见不平常,能从正中看见奇,能从茫茫人海中发现那藏匿在寻常市井间的不凡,能够透过人才身上层层包裹着的障目的俗尘,捕捉到核里面蕴含着的灿烂光华。
人才为什么不自己走出来展露才华,而非要等待别人去发现呢?
因为人才所需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与一般人相比相对苛刻。一般人能够轻松适应的,偏就人才适应不了。一个平庸的上司,越平庸就越狭隘。他需要用虚张声势来遮掩他的平庸,他需要手下人对他毕恭毕敬、随声附和,他需要在虚妄的喝彩中,忘记自己的平庸。人才对平庸和肤浅的忍耐度十分有限,熔点很低,他在平庸面前,只能选择沉默和孤独,一旦无可忍耐时,他也只能选择逃脱。平庸的上司虽然也做出爱才的姿态,但他内心对人才是防范的、排斥的、抵触的。他对人才敬而远之,或者束之高阁,或者装进金丝笼,只希望两不相犯。内心深处却像是防贼一样防着人才,寻着他的短处,搔着他的伤口,一旦发现有些许越轨的言论,他会立即让自己养的蚊蝇蝇集蚁附,无中生有地诽谤、迫害、攻击、造谣生事,直到把一个人才扭曲成神经病或者疯子。
如果是皇帝老儿呢?干脆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一切都是老子的,一切都要为我所用。能够为我所用,豺狗即是才;不能为我所用,人才即是祸苗。在他们眼里,人才应该是对自己更乖巧,对敌人更凶狠的咬人狗,用得着时,放狗出去撕咬一通,一旦无用了,干脆杀了狗吃它的肉。
因为这样平庸的上司和凶残的皇上比比皆是,人才也望而生畏,与其出世去做帮腔或者帮凶,还不如把一腔才情挥洒在天地间。放浪形骸、自生自灭,回归于大自然。于是,他们开始逃避,拒不合作,哪怕衣衫褴褛,任凭饥寒,放歌于山林,也不愿出来做官。有几个出来做了官的,如果不放弃自己多年苦修而成的良知和正义感,学会官场一贯畅行的逢迎和圆滑,如果不昧了良心洇没自己残存的一点善良,学会谀、学会谄、学会糊涂、学会逢场作戏,不但官做不到头,还要招来杀身之祸,并且殃及宗族。这一切,智者们看得很明白,也想得透彻,他们避官如同避祸,坚辞不从。如果用轿子强把他们抬到官场,他们也会装聋作傻,迹同庸人,借以保全。
可是,人才毕竟不等同于凡物,他是有尖刺的。尖刺长期的蜷伏使他难受,他总要把尖刺露出来,即使把他装进麻袋里,尖刺迟早也会露出来。人才最耐不得的是寂寞,瓦釜雷鸣、黄钟无声,会使他们欲哭无泪,英雄无用武之地,才是人才最大的悲哀。于是,悖论出现了:一方面,社会缺乏人才,到处都在呼唤人才,寻访人才,猎取人才;另一方面,许多人才被埋没、被闲置、被浪费、被扼杀、被空耗。许多人才在郁郁不得志中恨恨而终,像一碟豆芽因缺水而枯萎,这可真是暴殄天物。
如同太行山上那匹拉着沉重盐车的疲惫不堪的马,“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
“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如同卞和手上捧着的那块和普通石头并无二致的顽石。“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
人才渴望被赏识,被发现,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渴望与燧石相撞击,任凭粉身碎骨也要迸发出绚丽的火花。伯乐遇到太行山上疲惫的马,“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被昏庸的两任楚王砍了双脚的卞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文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千里马遇到知音的嘶鸣和卞和泣尽而继之以血的悲愤都是对“大才无人识”、“大才不得出”的血和泪的控诉!
古往今来,有多少大才因为得不到发现或者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而悲愤呼号,泣尽而继之以血!
可是,世上的伯乐和楚文王又是那样的少。人才们为什么非要等待他们慧眼发现呢?与其在无望的期待中发霉,何如亮出剑锋?难道就不能从盐车的重轭下逃出,潇洒地跑一趟,让人们知道自己的价值?难道非得在楚山苦苦地等待楚文王的出现,不会自己剖开美玉的璞,让那绝世真容出现在世间?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避官如避祸,乱世如此,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盛世,人才该不藏着掖着了吧,该像冯谖一样弹剑而歌,该像毛遂一样自荐,争相出世,蔚然成林,该不会再有压抑的悲愤,该不会有人才被埋没的悲剧了吧。
但是,人才被浪费被空耗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追究到人才本身的坏脾气了,所谓“凡人才者必有怪癖”。如果圆通光滑、八面玲珑、贤淑如处女,那就是聪明人而非人才。所谓人才,横溢的才华总是和令人生厌的怪癖相伴相生,就像那块绝世美玉偏偏就裹了一层璞,形似顽石,就像那匹日行千里的马偏就才美不外现,食量惊人却连盐车都拉不动,形似个不中用的货。其实他们的高贵和才华都藏在内里,需要激发和发现,需要适合他们生长的独特土壤。表面上,他们落落寡合,不招人喜欢,并且有很多怪癖。人才的桀骜不驯,人才的自恃清高,人才的冷傲与孤独,人才的大智若愚……这些怪癖使他与众不同,又使他不能相容于世俗的社会,使他才高和寡,阳春白雪,成了另类,与世俗的生活本身格格不入,人才枉自嗟叹,埋怨找不到一块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世人也在感叹,人才要是能磨掉自己身上的怪癖该有多好啊。
我也忍不住叹息一声。
既然人才被埋没对人才是极大的浪费,那就设法让自己不被埋没。
既然人才不被发现是人才极大的悲愤,那就要设法推销自己让人们发现。
要做到这样,人才也要打磨掉自己的怪脾气,也要打磨自己的毛刺。一味桀骜不驯吓得人退避三舍,不妨外圆内方一些,一味的大巧若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也不妨圆通豁达一些。
如能这样,则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