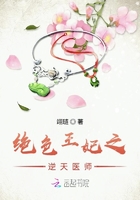似乎有点苍白啊。
杜尽忠又补了一句:“我一走,她就哭……”
段如月还是没动,只是看着他们。
然后她抬手把那孩子捞走了。
“段将军……”
杜尽忠愣在原地,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他看见段如月抱起那孩子,让她倚在肩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营帐,只丢下一句:“赶紧过去集合,再有下次,军棍伺候。”
或许是因为段如月已经是全军营里唯一的女子了,又或许是刚刚哭累了,那小丫头一伏在她肩头,便停止了哭闹,老老实实地趴着,眼角余红未消,像只可怜巴巴的小兔子。
因为战乱,一个尚不记事的幼女流离失所,或许再也见不到亲人。
再想想那岑玉太子,锦衣玉食地供着,把百姓的命不当命。段如月不禁目透寒光。
那天,将士们看到了一件很稀奇的事,向来杀伐果断、干脆利落的段将军居然很细心地在给一个小丫头喂面糊糊,并且透露着圣光般的母爱。
确实,那天段如月似乎有用不完的耐心。
她活到二十岁,一直活得很快,习武便要通,习阵便要精,及笄便嫁人,嫁人便生子。
很难得像现在这样,细细地去做一个母亲该做的事。
她想起了她还在宫中等她归去的小女儿,应该和这丫头差不多大小。况且现在已近京城,也不会因为一个孤女再回岑玉了,便将她带回了京城。
思绪飘飞,又飞回朝堂的大殿上。
有臣子一惊,小心翼翼地道:“这孤女,莫不就是……”
那大臣没说完,但满朝堂的人已经知道他猜的是什么了。
“小王早就说过,段将军瞒是瞒不住的。”岑玉使节露出一抹邪笑,乜了旁边的段如月一眼,得意道:“段将军当年既已将我岑玉公主带回京城,如今,可否还给我岑玉了?”
段如月怔怔地看着面前的地毯,似乎正要开口。
“使节大人且慢,本皇子以为,此事疑点颇多,还请大人毋要妄下论断。”
不等段如月说些什么,四皇子先向前一步,替黎殷说了话。
“清鸿,你且说来听听,也好不叫使节大人寻错了人,回去岑玉难以交差。”老皇帝在座上授意。
四皇子又施一礼,这回再开口,是朝着满殿文武:“诸位可想一想,当年无论是对于段将军,还是杜大人,这孩子都是捡来的,举目无亲,谁能弃置不顾?明显与使节大人所说以城池胁迫不符。
况且,若真是一名岑玉孤女,想来也不会在京城有过高的地位,那孩子现在该有十三四了,一国公主,与寄人篱下,谁不会做出判断,若真在此处,为何不与本国使节前来相认?”
仔细一想,当年段如月所捡到的幼女与岑玉使节所说的公主,除了恰巧当年都是孩提外,确实有很多细微之处让人难以联想到一起去。
尤其再被大臣们心中的储君四皇子这样一分析,便再次生疑,更有心直口快的大臣直言:“莫不是岑玉知道了段将军好心收留岑玉孤女一事,特来冒认,好从我黎殷获些好处吧?”
一时间,再无人言语,但众人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样一番话,引起了很多共鸣。
想来那岑玉使节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氛围,不耐烦地开口道:“军营中那么多人见过我岑玉公主,段将军自然只能说出事实,可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捡来的,恐怕,还是有说谎的余地吧?”
“我母妃既已说出大部分事实,恐怕没必要在那细枝末节上说谎。”云清霜白了他一眼,满是傲气地道。
“七公主无需再辩。”岑玉使节理理衣袖,正视段如月:“只要段将军将当年带回京城的小姑娘带出来,与我皇滴血认亲,一切便都清楚了。”
一旁立即有的大臣手执笏板站出来道:“陛下,事关我黎殷颜面,万万不可随意将我黎殷女子送去岑玉啊!”
老皇帝一摆手:“朕不会……”
“陛下多虑。”岑玉使节又低下头,似乎在袖子里摸着什么。
不一会儿,之见他手中多出了一个红色木塞封口的白色瓷瓶。
“这是我岑玉皇帝的血液。我岑玉爱惜子嗣,陛下不惜自伤龙体,也要寻回公主。”
朝堂上,那岑玉使节举着那一小瓶血液,像是举着一块无价的玉玺,叫人心头一颤,望而难进。
云清霜额上冒出了几点汗珠,事关她母妃,就算她全然相信庄贵妃,也不由得捏了把汗。
“段将军?”岑玉使节提高了声音,“请将那姑娘带上来,可好?”
无人应答。
朝堂上在一瞬间静如止水,几十人齐齐看向段如月,不知她该如何回应这岑玉使节。
四皇子似乎还想帮着黎殷说句话,可岑玉做到这个份上,众臣恐怕都认为岑玉是有备而来、证据确凿了,终于张张口,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众人都在盯着段如月。
就连一向疼爱这位庄贵妃的老皇帝,也只能端坐着,等待她回应。此刻,他只是君,她只是臣。
“使节大人。”
终于,段如月沉沉开口。
众人或多或少地都替她捏了把汗,可她依旧处变不惊。
“并非我不愿将她带来,而是现在——”她顿了顿,“她根本不在京城。”
众人听后均是一惊,随后又是略带侥幸地暂时松了一口气。
只有那岑玉使节像是从来不曾想过那小姑娘不在京城似的,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额上青筋甚至有些微微突出。
但毕竟,他面相有几分像狐狸,心也如狐狸般玲珑狡猾,很快意识到自己失态,赶紧调整好姿态,咬牙道:“那她究竟在何处?小王何时才能回去同宰相交差?”
纵然没有刚刚的冷静与轻蔑,他忍耐力不错,还算是问的得体。
不过,只刚刚小小的失态,便让白笙儿捕捉到了他的一时口不择言。
宰相!
久闻岑玉现在的皇帝疏于朝政,确是宰相管理不少事务。可一个自称“小王”的人,竟要回去向宰相交差,不免太过奇怪,似乎这宰相已经代皇称帝了一样。
云清霜也没有放过这一处纰漏,但终究不是议此事的时候。她白笙儿交换了个眼神,立刻心领神会,按兵不动,只默默记下。
这是,段如月叹了口气,然后自入朝堂来一直平静无波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显得那么无奈而又真诚:
“使节大人急也没用,并不是臣不愿将那孩子带来见您,而是臣自己也不知道,那孩子究竟在何处。”
“你亲手带回京城的,怎会不知?”岑玉使节终于露出了急切的神情。
“是谁告诉使节大人,臣带那孩子回京了的?”
段如月面向龙椅,叩首而拜:“陛下明鉴,当年臣胜仗归来,身边并无幼女。
那是因为,发现那孩子的时候,臣等并未到京城,点兵之后,途径一村庄,臣当时认为那孩子既是寻常百姓家的姑娘,便不该进京为奴为婢,而使村中一对好心的新婚夫妇收养了她。”
“所以,”段如月声音愈发真切地萦绕在每个人耳边:“那孩子现在究竟身处何方,臣,实在不知。”
满座皆惊。
谁能想到,十年前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因好心收留的一位幼女,竟会在十年后的朝堂上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那村庄呢?你把我岑玉公主留在哪个村庄了?现在去找总能找到的吧!”
藏不住了,那岑玉使节满脸的急切与惊慌已经藏不住了。仿佛一旦找不到,他面前的,就将是深渊地狱一样。
“八年前那村落遇旱灾,村民大批外迁,动向……早就查不到了。”
岑玉使节循声猛地转头,竟发觉是一直以来不曾讲话的杜尽忠。
杜尽忠幽幽道:“我杜家近些日子……有些不太光彩的事情,想必诸位同僚都听说了。其实,后来我也曾怀疑那姑娘的身份,这才让犬子与岑玉贵族联系,却不想询查无果,反而使犬子遭我连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