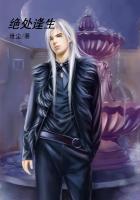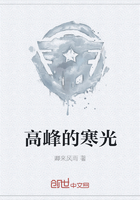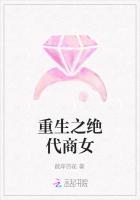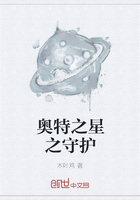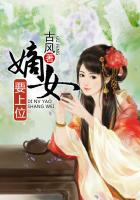玄武门是太极宫的北门,在玄武门南侧还有一汪湖水,名叫太掖池。众人看见李世民正在太掖池边徘徊,时而仰首望天,时而俯首叹息。徘徊良久,众内侍都是远远地看着,不敢上前。
李靖估计李世民肯定是为长孙皇后的重病而担忧,心中甚是同情,有心去安慰安慰他。他便对薛仁贵等侍卫说道:“你们在此好好地值班,老夫前去看看。”
李世民这段时间真是愁肠百结。
太上皇去世不久,刚刚安葬妥当,诸事消停。不想长孙皇后的生身母亲赵国太夫人又接连薨逝。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长孙皇后一病不起,日渐沉重。所以他这段时间心乱如麻,国事也无心打理。今日早上药王孙思邈禀报,委婉地劝他多陪陪皇后,多让她开开心。李世民马上意识到皇后的病已入膏肓,已经无药石可治了。这便令他的情绪低落,伤心悲痛。
可他一肚子心事又无人可诉,所以便一个人在这太掖池边感伤、徘徊。
李靖悄悄地来到李世民的身边,李世民却正在伤心时,并未发现。侍卫见卫国公李靖来了,想要禀报,李靖挥挥手制止了他。
“陛下。”
“陛下!”
“噢,是李爱卿。”
李靖连着轻轻地叫了两声,李世民才回过神来。他抬起头来,见是李靖到来,心中稍感欣慰。
李靖见李世民眼窝深陷,面容憔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知道现在李世民的内心肯定是非常伤心忧虑。
李世民对李靖点点头说道:“李卿来的正好。朕现在正有一肚子的话不知和谁说呢。卿来得正好,正好陪朕说说话。”
李靖连忙拱手躬身道:“陛下,最近一段时间,伤心事接二连三,对陛下打击较大。人生无常,总是命运多舛,这又岂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臣请陛下一定要节哀顺变,多多保重自己的龙体要紧。”
李世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伤心地说道:“朕是想注意身体,可这段时间朕又哪能静得下心啊。太上皇和赵国太夫人接连薨逝,已经令朕伤心不已。而长孙皇后又接连病倒,更使朕六神无主。朕即使贵为天子又有何用,有些事还不是只能听天由命!唉,有些事皇后又一直与朕犟着来,让朕好生为难。正好李卿来了,快给朕出出主意,说一说朕该怎么做?”
李靖连忙躬身道:“长孙皇后向来贤惠豁达,通情达理,又会有何事让陛下如此操心呢?”
“唉!”
李世民长叹了一口气道:“皇后病重,卧床不起。太医和孙思邈轮番救治,但药石已不见效。孙思邈也告诉朕说只能是但凭天意了。”
李世民说到此,仰头望了望天,眼中有大颗的泪水滚落。纵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千古一帝,英雄豪杰,此时也难免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李世民顿了顿,又接着说道:“皇太子李承乾见他母亲大病不起,向朕请求大赦天下,并准备着度人入道,想以此恳求上天垂怜。朕也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或许上天垂怜,皇后的病能有所好转。可皇后坚决反对此事,朕再三劝说也不行,太子跪在床榻前恳求也不管用。她说自己此病是多年的病根和操劳伤心过度所致,哪是什么天意所能左右的?不能因自己的生病之事而干扰国事,损伤国体。朕岂不知道皇后之病乃是体弱,又加上近一段时间的接连打击,伤心过度所致?但如此贤后良妻叫我如何割情?朕若失去长孙皇后这样的贤妻良佐,朕又如何能不痛苦悲伤啊!”
李世民说话间,竟不顾李靖在身边,掩面啜泣不已。
李靖也是伤心不已。长孙皇后不仅是他和红拂女一家人的知己至交,更是一代贤后。她辅佐丈夫,教育皇子,抑制外戚,奖进忠良。她每一件事无不做得非常完美,人人感服。
李靖上前一步说道:“陛下在心痛之时,仍要注意保重龙体。臣觉得皇后在病重之时,仍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国家为念,犹让人敬佩。臣觉得皇后说的话也没错,很有理性,于国于己都对。既不让一己之事干扰国政,也不让世人因自己的事情而妄议陛下因私废公。臣请陛下能听从皇后的劝告,以全皇后贤惠忠良之名。”
李世民已是泪流满面,他哽咽道:“朕知道你说的有道理,也知道皇后说的有道理。可她总是想着朕和朕的江山,什么时候想过她自己?没有了朕的爱妻,朕即使纵有这万里江山又与谁共呢!让朕眼睁睁地看着皇后日益病重,而朕却枉为天子,竟什么也做不了,你说朕这心里面怎么能不痛心呢!”
李世民说完,痛苦地摇摇头。他扶着柳枝,呆呆地望着太掖池中的一池碧水。池中数只鸳鸯成双成对,它们正在池水中相拥着快乐地理毛戏水,这更勾起了李世民的伤心事。
“唉,朕贵为天子,现在竟还不如那对鸳鸯过的快活惬意啊!”
李世民指着池中的鸟儿,伤心地说道。他一边叹息,一边自言自语,喃喃地咏道:“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春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皇后啊,你看如今桃花、嫩柳都还在,却哪还有人陪朕一起观看蝶舞,倾听莺啼啊!”
李世民说罢,痛哭不已,竟忘了李靖还站在那里,便独自踽踽离去。
李靖知道李世民咏唱的是长孙皇后早年所作的《春游曲》。当年的长孙皇后是何等的容光焕发,青春靓丽,又是何等的知性可人,夫妇偕和。可如今,他看到李世民茕茕孑立,踽踽独行的样子也非常伤心。
但除了安慰之外,李靖又能做什么呢?
贞观十年六月(636年),长孙皇后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之死,朝野震惊,举国哀恸。
李世民更是悲伤不已,他遵从皇后遗愿,葬事从简,营山为陵,是为昭陵。
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伤心至极,多日不愿理朝视事。众人都很着急,怎么劝谏也没有用。
魏征也上书劝谏,说道:“皇后崩逝,陛下思念乃是人之常情。皇后逝世举国同悲,国人都痛心失去一位贤后。可皇后已逝,大唐江山还要继续啊。陛下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而是一国之君,不能一日而废朝政。况陛下对皇后已经极尽哀荣,累赠谥号‘文德顺圣皇后’。如此尊荣亘古未有,皇后若地下有知,也一定心安矣。望陛下以国事为重,节哀顺变,这才不负长孙皇后的临终期望啊。”
众臣们越是规劝,李世民越是难过,对爱妻的思念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朝堂之上,都情不自禁地向大臣们倾诉自己在丧偶之后,心思恍惚,食不甘味,彻夜废寝的悲苦情境。
众人无奈,都来找李靖。
他们知道李靖与李世民的特殊关系,让他去劝劝陛下。李靖心中也是难受,但知道李世民确实不能再沉迷于伤妻之痛中,要早日醒来。但他又不知从何劝起,一直无法劝说。
一日,李世民邀他进宫,二人同上层观。层观是李世民在宫中特意修建的一个高台。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李世民久久无法释怀,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在这里可以远远地眺望亡妻的陵墓。
李世民指着昭陵的方向对李靖说道:“李卿,你看到了吗?前方那就是长孙皇后的昭陵啊?”
李靖茫然四顾,失望地说道:“臣老眼昏花,实在是看不见啊。”
李靖实际上是装作没看见。
李世民急了:“怎么会看不见呢!你看,就在前面,你朝前望啊,那就是昭陵啊!”
李靖闻言,有些惶恐地说道:“什么?原来陛下说的是昭陵啊,臣还以为陛下天天望的是献陵呢!”
在中国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李世民此举确实有违礼制。
李靖双眼流泪道:“陛下,普天之下,大唐所有子民之所以那么爱戴长孙皇后,是因为长孙皇后一直以国事为重。她从来不因己、因亲而废公。长孙皇后崩逝时还遗言要求薄葬,希望不起坟茔,依山为陵。她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都为大唐着想,都为陛下您着想,难道陛下还不懂皇后的良苦用心吗?”
李世民明白李靖的用意,让他不要因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而了大唐的江山。他此时一下子难以抑制情绪,痛哭不止。
李世民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慢慢调整情绪,重新复朝理政。
不久,李世民改封李靖为卫国公,授濮州刺史。考虑到李靖足疾严重,行动不便,许他不用上朝,有事奉诏即可。李靖的两个孩子也都在朝中为官,李德謇官至从四品下将作少监,李德奖也另有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