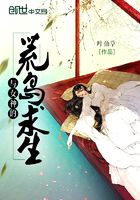她把钱装回他的内衣口袋,然后用额头与他的额头轻轻相碰。望着洛桑的背影消失在转经的人群中,她的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其时,她身无分文。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像个真正的天使,真正的达摩,挽救了她绝望的心情。她满脑幻念,来到更庆寺。武士和他们的马匹焦躁不安。一匹种马不停地嗅着它身旁母马的屁股,突然扬起前蹄,把粗壮的生殖器插进母马的产门。武士们乱作一团,咒骂着,分开这两匹交配的马。她看见酒鬼丹珠躺在寺院的墙根下,已经烂醉如泥。一群孩子站在他面前说:“酒鬼丹珠,你到鱼肚子里把手枪取出来给我们瞧瞧嘛。”酒鬼丹珠乜斜着眼睛打量着那帮孩子,突然翻一下身,嘴里嘟哝着说:“我的手枪藏在鱼肚子里,小心我取出来一枪子儿崩掉你的尕鸡巴。”
孩子们哈哈大笑着一哄而散。
晌午,有人吹响了牛角号。迎接灵童的队伍出发了。大街上的人们摩肩接踵。汽车和摩托车的喇叭声,马的嘶鸣,人的呼喊,响成一片。向西,车队和马队绝尘而去。人们开始静静地等待。艳阳如火,炙烤着大街上的人群。
下午,迎接灵童的车队行将到来的消息传来,人们慌忙挤向大街,排起狭长的人墙,个个手捧哈达。一匹匹骏马走过,一辆辆摩托车走过,一辆辆汽车走过,载着灵童的越野车缓缓行驶。人们争先恐后,把哈达抛向汽车,用额头触碰汽车,脸上露出热烈迷狂并因此而扭曲变形的脸。一张张这样扭曲的面孔成了虚妄的海洋,看着让她感到恐惧。任何非理性的迷狂,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其必然的结果都将导致愚昧、迷信和暴力。值得警惕的永远是非理性的迷狂。她因看到这种迷狂的情绪而感到悲哀。
她在日暮的黄色雾霭中漫步山坡,一再想到的,不是迎接灵童的仪式上那种艳俗的场景,而是少年洛桑,他的慷慨和仁慈,让那样一个灰暗的日子光彩四溢。
黄昏,巨大的雷霆推动着金沙江,在四川和西藏之间,在秋天和冬天之间。夜半,却见今年的初雪,推动着雷霆,仿如鹰群尖锐的飞行撕破了空气。风雪经过屋顶,你干燥的梦境有了湿润的呼吸,初雪、忍冬草和常青树的呼吸。草原风雪,令百兽匍匐在地。这高原之上的雪夜,亡灵从山顶披挂着枝柯,踢踏而来。一百头雄性牦牛鼓呼着肺叶驱驰在山谷。茶马古道上,经卷和驿铎的锈迹,被一束年轻的唱诵擦亮。你夜半的歌声光芒万丈。你歌者的血液里,酒和思念被远方的一朵爱情照
修行
亮。爱情照亮,你幽暗的心脏和半个脸庞,而一具灿烂涅槃的肉体,蹀躞在禅中光明的路上。需要屏住呼吸:倾听,冥想。夜半走过的,是玛瑙和牛粪共同裹砌的时光。
九月之末的一个夜晚,大雪飘临草原。戈麦高地上的冬天来得总是这样突然。她手脚冰凉,从被窝里爬起,打开窗户,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那是十万个小天使在舞蹈。小木屋冷若冰室,但她毫不介意。她裹着那件军大衣,伏在窗户上久久地望雪。藏狗桑丹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梅花状的爪印。她敲开水缸上的冰,舀水洗脸,然后走出小木屋,伸出双手,扶住落雪,像扶着她思想的羽毛,或者,像扶着她一腔献祭的热血。戈麦高地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对面西藏那银色的山峦下,碧绿的金沙江蜿蜒如玉。山坡下的牧人,正在屋顶上扫雪,他们黑色的身影仿佛稿纸上的感叹号。央金玛从牛栏里赶出牦牛,向山坡下的草原走去。她咯咯咯咯地笑着,不知道什么事让她那么开心。牛蹄子踩着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很远都能听见。
她像匹马儿,静静地伫立在大雪中,啜饮着这个冬天粗糙的表面。
九月的初雪,已在念冬神山的额头堆积。乌鸦麇集,在牧民的屋顶。你出门时撞见花草枯萎,牛羊走遍山坡也还感到饥饿。季节变了。孤单的行脚僧,持诵的咒言还鲜嫩如初。年轻的喇嘛仁青巴灯捧读的一卷经,还停留在思考的第一页。天气变了。西部以远,一个草原浪人的国度,拥抱着风雪和思念,以及一份远方的爱情。当天空布满石头和苍鹰,仰望的岁月更加漫长,持续。仰望,在初雪的九月。草原上的冬天,没有人会比你更加形单影只,也没有人会比你更加幸福和平淡。只
需要一朵云彩,就可以把伤感的城市推远。只需要把眺望的习惯稍稍改变,兽一样,蹲在石头上,眼睛里装满热情和爱戴,日日眷念着远方的朋友,和一朵唤作拉萨的爱情。雪一样,躲在天空中,沉思默想,或给视线以外的世界,写一封信,湿润而又漫长。朋友,当你捧读信笺,你将看到九月的牛羊归圈,九月的念冬神山,山高水长,恩情浩荡。你日日目击着祈愿成真,神祇飞翔。你阅读着经卷,写作着诗歌,教育着三十个草原上的苦孩子。
哦,九月,山高水长,一颗伟大的心灵被草原滋养。啜饮着大地的光芒,你一个人,在这蹄角遍布的地方,没有忧伤。在土地的土中,在祖国的国中,在你流浪的这高山牧场,狼群出没,但羊如智者,在圈中观望。你以手为犁,开拓内心的爱和阳光。夜半的粮仓,如饱满的乐器正迎风歌唱。
多年以前,她和他一样,曾经向往过这片高原,这片被神秘主义者在修辞中完美过的高原。没想到,许多年以后,她和他一样,骑马走进冬天,康巴藏区的冬天,进入戈麦高地上的这一片苦寒。这苦寒注定要在远行之后历尽艰难,然后再进入一张日渐沧桑的脸。
戈麦高地上,一场雪聚拢了言词、感念之歌和一个草原浪人的青春。一场雪聚拢了马匹、羊子、牦牛、马靴和宰牲季节的刀子。
你在高处,目睹了这个冬天的到来。
直接迎向冬天的三郎瑙乳,就像义无反顾的刀子迎向一场淋漓的鲜血。大雪飞扬,阴风怒号。三郎瑙乳赶着两头牦牛,走出村庄。大雪覆盖了陡峭的山路和倾斜的冰川。路边悬崖下,一片风雪的迷蒙,致使那些寻觅寒食的鹰和乌鸦一次次迷失了飞行的路径。这是一次显而易见的觳觫之行,但他必须赶着牦牛到达县城。这个时候正是肉价高昂的季节,宰牲的匠人说好了今天在县城等待他的到来。三郎瑙乳需要穿过风雪,到达县城,请宰牲的匠人杀掉牦牛,然后在德格县城的桥头市场上,守着一堆牛肉,卖掉,换回来年的开销用度。
从戈麦到县城,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骑马或徒步要走七八个小时,而在这样的雪天,不知道三郎瑙乳走了多长的时间。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一路上经历着危险。他的脚会在雪地和冰川上打滑。他必须紧紧抓住牦牛的尾巴,才不至于一不小心就掉落在悬崖下。
你仍在高处,目睹着这场大雪。金色的牧场消失了,变成白茫茫的一片雪原。西风吹雪,一再埋没兽迹和鸟羽,一再埋没雪原行旅者仓皇的脚印。雪原行旅,其实是远人之流放。命运的风雪中,是谁把你流放在这荒凉的人世上?举首向上或者俯身向下,向上和向下是同一条路,但上下都不平坦。上下都不平坦,可你还要走上好多好多年。好多好多年以后,青春的山和海逐渐拉平,生命中爱与恨的情感逐渐平淡,那时候,或许你才会发现,只有死亡的过程上下都很平坦。就如此刻,你在高处,连粗重的呼吸也不平坦。
你只是关注着,大雪的日子,草原上一个康巴人居住的村庄,到底有什么发生或者到底有什么最终不会发生。你看,大雪中,牦牛和羊群挤在一起,用相互的体温取暖;老人们躲入寺院,昼夜诵经;女人们在厨房里打着酥油;儿童们趴在羊毛毡上写着作业;一座建设中的房子停止了施工。
在这深入的草原,如果你孤独,你将永远孤独。如果你没有房子,
你也不必建造,一顶黑色的帐篷,就足以携带着你以及你的家人,从东到西,从春天到冬天,仿若迁徙的鸟打开或收拢翅膀,就足以翻越南极和北极,雪原和大洋,在海拔和纬度的地理学中,成就自由的飞翔。
鱼,依源而行,因而鱼自由;鸟,执命向西,因而鸟自由;那名叫察绒的草原老猎人,依靠粗糙的生活,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因而察绒自由。
许多年过去了,猎人察绒追逐着四季的风和野兽的足迹,走遍了草原的角角落落。他是草原的褶皱里一粒沉默的种子,荣了又枯,枯了又荣。
某个兽皮一样缤纷的夏日黄昏,照亮了猎人察绒的眼睛,他决定在戈麦高地上定居下来,因为格桑喇嘛捎话给他说:“明年五月格桑梅朵盛开的时候,就是察绒大喜的日子。”
猎人察绒要修建一所能够举行盛大婚礼的小木楼。他要把扎西青措将要居住的新房装饰成小小的宫殿。他要把多年积攒的豹皮和鹿头挂上墙壁,以便情人的眼睛感到愉悦。水,抱椽而流,有了建筑、手艺、居留和繁衍。人,依源而行,有了爱情。一所房子将要在草原上落成。用于建筑的木材来自金沙江上游,那里有一片茂密的森林。猎人察绒去那片森林里伐木。针叶林在那个迷人的秋天散发着一阵阵酒样的清香,树林里吃草的马儿被这酒样的清香醉得东倒西歪。在那个秋天行将结束的时候,木材被扎成排子,猎人察绒和众亲戚中赶来帮忙的男人,驾驭着木排,在金沙江汹涌的浪花上,顺流而下,仿佛驭马狂奔的刀锋战士,冲入乱阵。不断有人落入激流,不断有人的皮肤或骨头被水中的石头击中,不断有人死去。水葬的仪式在逆风呼啸的江面上举行,惨烈,而且血洒一样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