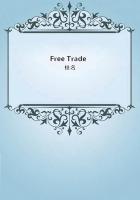在戈麦高地,生物钟调节着人们的休养生息,所有的生命全都遵从自然的节律。她投身其中的大草原,荣也寂寂,枯也寂寂。即使站在金沙江边,她也不会如那古代的哲人一般,喟然长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她的大脑中,时间无始亦无终。沙漏无漏。日晷无影。这样的日子,与其说是那些云和羊子,不如说是那些山和源泉,在动;与其说是她在观察和思考,不如说是一缕隐居者的思想,被推远,成为那些云和羊子,那些山与源泉,凝固的背景。哦,在这忧伤的马头下……书籍和清新迷离的风,在她的额头堆积,形成一道若隐若现的智慧。她的额头下,那灯盏般的眼睛被智慧擦亮,仿如这忧伤的马头下,一双鹰翅被飞翔擦亮。哦,在这星辰的苍穹下……她素食,禁欲,观照时间止息于星海;她参禅,晨操,深入平民的朴素。隐居的日子,词语归于内心和缄默,树叶归于地层和孕育,星象归于苍穹和启示。哦,在这羽毛的天空下……看惯了云和羊子的奔跑,马和母亲的哭泣,看惯了石头开花儿女长大,羽毛和神祇的飞行,她更加缄默了。因其缄默,她偶尔吐露的言词,才更像一粒真理,播种在心造的国土中。而她那一具凡俗的肉体,逐渐归于更加阔大的捐赐和牺牲。哦,在这自然的节律下……
她和戈麦高地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马都日渐熟稔,似乎她从来就是这辽阔草原上的一名小学老师,日复一日地活在平淡的节奏里。
每天清晨,她在校园外的草地上漫步,聆听着从教室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有人在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有人背她自编的西藏历史四字经。天地之初,海水一片。日月星辰,慢慢出现。青藏高原,长出水面。罗刹女神,来到人间……有人在背昌耀的诗歌《月亮与少女》。月亮月亮幽幽空谷少女少女挽马徐行长路长路丹枫白露……
从遥远牧场上骑马而来的牧民,趴在窗台上和门边上,看她上课。姑娘们羞涩地卖弄风情。课间休息的时候,那些鲜艳的姑娘和英俊的小伙子在校园里打情骂俏,追逐嬉戏,放荡而美丽。洛桑在课堂上神气活现,洋洋得意。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因了这大草原的滋养,提早成熟了。洛桑打扮得花里胡哨。毡帽,花衬衫,牛仔裤,白球鞋,手腕上套着棉织护腕。他多么想成为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洛桑扭动腰臀跳着舞蹈,挑逗着姑娘们。这个小牧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仁波切加持祝福的佛教徒,如果没有被昆明的那所基督教教会学校开除的话,他会成为一名牧师,会是一个宣讲天国福音和上帝之爱的青年。他会被派到戈麦高地来,在他的祖先们信仰佛教的草原上,给人们宣讲另外一个世界,把人们从佛陀的世界引向基督的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宗,依靠的总是剑和血。那时候,洛桑会不会成为亲人的仇人,会不会在背叛之名下灵魂分裂?有一天,洛桑对她剖白他在基督教教会学校时的迷惑。他说:
“我不明白基督和佛陀是什么关系。外国人的神跟我们藏族人的神完全不同。那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基督和佛陀在打架。我想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疯掉的。”
她也相信,如果长此以往,洛桑会有疯掉的一天。所幸,他被开除了。他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故乡,心满意足地按照一个藏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活着。
看着校园里活蹦乱跳的洛桑,她觉得,只有单纯的知识和信仰才能给人幸福。她对洛桑说:“好吧,就这样吧,就这样桀骜不驯,追逐姑娘,健康成长。”
一个阴霾垂天的中午,你吃过午饭,在校园外散步。似乎是要下雪的样子。阴沉沉的天空有了重量,仿佛那些缓缓移动的阴云载着煤炭,压在人的头顶,让人喘不过气来。你在这样的天空下感到胸闷气短,加之孤独感时时侵扰,所以心绪烦乱。你蹲在一块石头上,把目光投向山下的那片草原,渴望着有个熟悉的身影出现。没有朋友从远方来,世界似乎已经将你遗忘,你像一个被抛弃的人居住在流放地。
戈麦高地,这是你的流放地,执行官是高高在上的神灵,秘密地掌握着你的命运。你是孤独的犯人,没人跟你交流思想,没人对你体贴关怀,没有建立在崇高心灵之上的友谊,也没有爱情。蹲在石头上,你又开始唱歌。那些忧伤的歌子令你落泪。
一条小路,通向村东头成堆的巨石。鹌鹑在巨石堆里安营扎寨。你走过。受到骚扰的鹌鹑不满地叫骂着,扑棱着翅膀向山坡上的荆棘丛中跑去。巨石堆后面,是一块平整的青稞地,裸露出荒芜的黑土,一群麻雀在地里搜寻着稞粒,几只牦牛懒洋洋地站着,眼神空茫地望向阴暗的天空,像哲学家一样沉思着。被青稞地包围着的,是洛桑的家。一条大黑狗看见你走来,就狂吠起来。它一次次从狗窝的位置跃起,又一次次被脖子上的铁链拉回去。铁链因而哗哗作响。另一只小黑狗也不甘示弱,从石头堆里扬起小脑袋,冲你汪汪直叫。洛桑的阿妈卓嘎为你打开木门。她一身破烂的皮袄,脸也好久没洗了,脏兮兮的,像一块破旧的抹布挂在烟熏火燎的灶台上。你低头进入低矮的门,屋子里一片黑暗。洛桑偎在墙角的凳子上,见你进来,急忙站起来向你问好。
你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屋子里的黑暗,但土灶台里冒出的股股浓烟却让你难以忍受。你的眼泪被熏出来了。央金玛守着灶洞里的火苗。她长着一双海子一样深沉而忧郁的眼睛,每当你看到那双眼睛,你都想脱光衣服跳入其中,永远也不出来,即使死了,你也渴望着埋入那双眼睛。你相信,在那海子一样的眼睛里,你会游到她的心灵深处。你刚刚接过央金玛端给你的一碗酥油茶,就听见出门去赶牛的洛桑在门外喊你的名字。他的人跟他的声音一起冲进了房间。“亚嘎老师……你的朋友来了。”
由于刚才的奔跑,孩子说起话来气喘吁吁。“在哪儿?”你急切地问道。“在草原上,正往学校走呢。”
你赶快起身,冲出门去,没有顾及门外的大黑狗。你在小路上狂奔而去。校园外的山坡上,一个僧人正领着一个狗熊一样健壮的汉子向校园走来。你冲下山坡,在青稞地边的小路上直奔而下。
啊,神啊,你根本无法想像,那人竟然是边巴茨仁!他简直像个狂热的复仇者,嗅着你的踪迹追到了戈麦高地。他从兰州出发,搭乘班车,穿过甘南草原和若尔盖草原,来到了戈麦高地。
汗水浸湿了他那浓密的长发。边巴茨仁冲你哦哦叫唤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好啊兄弟,你把我的女人拐跑了,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也一起拐跑呢?”边巴茨仁擂着你的胸脯,一本正经地质问道。
“嗳,我是为你做好事。”你强词夺理地说,“我把卓玛拐跑了不就成全了你和拉姆措的美事吗?你就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去两兄弟旅店了嘛。”“神啊,你听听这个男人在说什么?”边巴茨仁露出懊丧的表情说,“啊,我真是个倒霉鬼。老婆被最好的朋友拐跑了,情人嘛,又让拜把子的兄弟拐跑了。哎呀,觉仁波,我上辈子是造了啥孽了!”“嗳嗳嗳,你说谁把拉姆措拐跑了?”你从边巴茨仁手里夺过酒瓶,猛灌了一口,然后问道。“扎巴多吉呗……”边巴茨仁从你手里气呼呼地夺过酒瓶,喝了一大口,又喘了一会儿气才说,“扎巴多吉在拉萨生意做大了,就回玛曲来,还他以前欠下的债。啊,我一看他还活着,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就陪他连喝了三天三夜的酒。啊,没想到,那家伙这几年在外面做生意,见了大世面,酒量好得很呐。啊,喝了三天酒,我就足足睡了五天。
等我醒来一看,枕头边放着拉姆措的银镯子。过了两三天我才醒过神儿来。她把我送给她的银镯子褪下来,戴上扎巴多吉给的金镯子跑掉了。觉仁波,这些女人!”
“卓玛也被他用一个银手环给骗走了。”
“我听说了。”他咂着紫色嘴唇上的一滴酒说,“他把卓玛带到美国开了一家藏餐厅,结果嘛,卓玛一学会英语就把他给甩了,跟了个美国佬跑了。”
“然后他又跑回玛曲把你的拉姆措拐走了?”“喏。他把拉姆措带到北京,还给拉姆措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结果,人家拉姆措跟一个美国大使嘛啥人结婚了。觉仁波,这些女人!”“扎巴多吉现在在哪里?咱俩把这家伙好好修理一下。”
“啊,你想找扎巴多吉?找不着了,再也找不着了。”
“为什么?”
“他生意做砸了,欠了别人一屁股债。啊,好家伙,他这次啊,在香港一艘超级豪华的游轮上赌博,赌着赌着,说是海底下有个金矿,就直接从甲板上跳到海里去了。啊,你想想,太平洋那么大,这次是死定了。觉仁波,这个男人!”
“也许他还活着。也许几年后我们会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头条新闻就是他制造的哩。”“觉仁波,你真是电影看多了。你以为他会成为纽约的黑帮教父或者是加勒比海盗头目?”“谁知道呢?我相信一切可能性。好啦,让我们为他祈祷吧,他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啊,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你。”边巴茨仁说,“上周一,我收到一个特快专递,里面有一张银联卡和一个纸条。我就在取款机上试着输入我的名字和我的生日。啊,兄弟,动动你那聪明的脑子,你猜,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发生了啥?”“我想先知道那纸条上写着什么。”“不,先猜发生了啥。”“取款机爆炸啦?”“啊,你蠢得像一头阉过的叫驴。”“银联卡被取款机给吃了。”“啊,你太缺乏想像力了,兄弟,太缺乏想像力了。嗐,就你这智商还当啥诗人哩唦!”“操,到底发生什么啦?”
“钱哎,兄弟,取款机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标着,三十万。”
“我对钱没兴趣。”你摆摆手说,“告诉我,纸条上写着什么?”
“这笔钱给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你们想出版多少本诗集,就出版多少,我想三十万元够你们两人出一辈子诗集了。最后的落款是:你们永远的朋友扎巴多吉。”
边巴茨仁一口气说完话,眼泪早已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了。
修行135星星布满了夜空。不知什么时候,阴云散尽,一钩弯月像阿拉伯战士手中锋利的弯刀,挂在山岭上,似乎要将那苍莽山岭一刀砍断,似乎要取走你们的头颅。你真想把头颅交给黑夜,夜的孤独的女儿将用你的头颅制作酒杯饮下芬芳的四季。四季的花朵湿漉漉沾染了毒药。四季的花朵是你爱过的女人。西藏如船。美女如监。她们占有你。她们戕害你。她们,囚你于爱情,囚你于情欲,囚你于秀发红唇与黏糊糊的舌苔。世界枯涩。囚你于歌。惟时间之豹,突围而出。两个男人挽着手臂在蓝色星光下向校园走去。做晚饭的时候,没有烟筒的炉子冒出阵阵浓烟。边巴茨仁从县城带来了土豆、西红柿和黄瓜。这是绝对的美味。可是浓烟滚滚,熏得你俩泪水涟涟。
匆匆炒了个土豆丝,下了一锅挂面,你俩就弄熄了炉火逃出小木屋,端着碗站在凌厉的寒风中草草吃完,然后在校园里一边漫步一边聊天。乌云遮住了星光,漆黑的夜晚像一团墨汁。你俩瑟缩着脖子,在黑夜中谈话,显得极其诡异。你俩看不清彼此的面孔,有时候感觉自己说出的话像是自言自语,而对方的话语像是从一堵墙上弹过来的回音。你们谈到了玛曲往事和那躁动不安的青春岁月。你们谈论着文学和音乐、宗教和信仰,兴奋地大吼大叫。你俩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扎巴多吉。“他是个音乐天才。”边巴茨仁说,“如果他不去做生意的话,他也许会和鲍伯·迪伦①一样著名。”“说起扎巴多吉的死,我突然想起那个东北的行为艺术家来了。他在①鲍伯·迪伦(Bob Dylan,1941—),美国摇滚乐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歌手和歌曲创作者。
格尔木①下了我们的车,会不会死掉啊?”“啊,那个人嘛,倔强得跟个叫驴子一样嘛。我让他别下车,他非
要在格尔木搞啥死亡行为艺术。唉,我估计是死掉了。”你和边巴茨仁在暗夜里唱起了歌,借以怀念扎巴多吉。
草原上的格桑梅朵,你静静地开放静静地摇晃。草原上流浪的人儿,你爬上山冈然后独自歌唱。那在春天到来的姑娘,她给你带来一罐马奶子很香。那在秋天开走的班车,它把你心爱的人儿带去远方。没有人告诉你,你的姑娘她是否幸福。没有人告诉你,你的姑娘她是否靠在别人的肩膀。阿妈说,女人是牛栏那边的河流,她走了就不再回头。阿妈说,男人是一匹善跑的骏马,他流浪是因为受伤。趁着天黑,阿妈还没醒来,你就走了。你走的时候,草原上的格桑梅朵正在开放。你爬上山冈,帐篷前的阿妈她向山冈张望。趁着天黑,看不清阿妈的眼泪,你就走了。
两个男人粗糙的歌声在夜空中回荡。这么黑的夜,天堂应该很低,居住在天堂里的扎巴多吉应该听得见你们的歌声。或许此刻他正抱着一把吉他,看着你们,唱着这同一首歌。扎巴多吉,你居住在天堂里冷吗?你居住在天堂里孤单吗?这样的夜晚,我们一起在草原,一起回
①格尔木市是青海省西部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格尔木为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