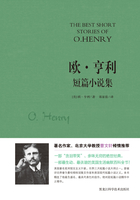却说凌贵兴自从打发丈人何达安去后,便代他妻子开丧挂孝起来,把一座裕耕堂重新收拾,延僧礼道,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众强徒借着帮忙为名,益发无昼无夜,都啸聚在凌家。贵兴没了老婆、妹子在耳边聒絮,反觉得爽利。到了第三天,爵兴便叫贵兴到往来的钱铺子里,打了票子,整的散的,共是二十六张。爵兴拿了一张一千的去交了何达安,其余散的二十五张,共是一千七百两,对不住,他自己拿去用了,还落得两边都感激他。他还要到凌家来吃白饭。这个一声“贤侄”,那个一声“侄老爹”,那一边又是一片声的“大爷”,贵兴倒也觉得十分热闹,反把死人的事忘了,天天那僧道礼忏之声,与那欢呼畅饮之声相唱和。过了三七,便把两口棺材,抬到祖坟去安葬了。贵兴便纳了两个侍妾:一个杨氏,一个潘氏。丧事之中,又带着吃喜酒,真是笑啼皆作,吉凶并行。
这一天,宗孔偶然想起一件事道:“我记得八月十六那一天,看见梁翰昭在千总衙门里出来,莫非他们此刻要交结官场,来同我们作对么?”爵兴道:“不见得。他们这般村老儿,见了个官就吓得话也说不出来了,那里想得到结交他呢?”贵兴道:“话虽如此,也不可不防,并且我们商量要抢割他的稻谷,迟两天就要动手了。这件事,千总管得着的。我这里一动手,他那边一报官,就是报到文衙门里,也要请他武官追捕的。这便如何是好?”爵兴道:“不要紧。这黄千总是最贪的,只要送上他几两银子,他便叫你做老子都肯的了。”贵兴道:“只是那个认得他,方好过付?”爵兴道:“只我就同他极相好,无话不谈的,何必求人?”贵兴大喜,就兑了五十两银子,请爵兴送去。爵兴道:“不必,不必!这些武狗,看见了一个铜钱,就笑得眼睛都没缝了,何必这许多?只要二十两就够了。这是当省的,我不能不叫你省,不比陈家、何家的事,是万万省不来的呀!”贵兴就改兑了二十两。爵兴接了,就去斡旋去了。好爵兴,果然只化了二十两银子,却买了一个黄千总了,回报贵兴,自然欢喜。
这一夜,外面铙钹喧天,他里面却是洞房花烛。这风声传到了梁家,凌氏等知道桂仙姑嫂双双自尽,不免叹息一番。只因彼此成了仇敌,也不便去吊唁。凌氏念着一脉至亲,哭了一场,方才想起,十五那夜,桂仙私行到来,临去那番话,竟是句临终叮嘱之言,难得他小孩子家,有这个远虑。后来天来回家,谈起桂仙的话,凌氏便把桂仙叮嘱,恐怕贵兴闹了大乱子,托付照应他的话说了,天来也是叹息不止。表过不提。
且说凌氏这一天,正在没事,看着儿媳们赶做冬衣。忽然哄了一班佃户进来道:“老太太,不好了!今天来了许多强盗,把我们的田禾都抢割了!”凌氏一看,正是北沙一带的佃户,不觉叹了一口气道:“既然遇了强盗,今年的租,且免了罢。”众佃户道:“老太太呀!多蒙你的慈悲,田租便免了,只是我们靠着过冬天、度新年的本钱,都没了呀!”说罢都哭了。凌氏道:“你们且歇歇去罢,我再商量周济你们点便了。”众佃户谢了出来。凌氏便叫请了翰昭过来,告之此事。翰昭飞也似的,去报了千总。那黄千总皱眉道:“可巧我今天泻肚子,还没有吃饭。这是地方公事,说不得也要去走一遭,只是我要吃点饭才走得动呢。”翰昭道:“吃过饭,恐怕强盗去远了,追不着呢。”黄千总怒道:“朝廷也不使饿兵,你们倒要使起饿官来了!”吓得翰昭不敢再说,只得退出来等候。直等了两个多时辰,方才听见传呼备马,又等了好一会,黄千总方才出来,跨上马,带了几十个兵。翰昭跟着走。翰昭起先还恐怕跟不上,谁知他倒是按辔徐行,莫说翰昭只有五十多岁的人,就是八十岁老头子,只怕也跟着他绰绰有余呢!等到到了北沙时,那里还有个强盗的影子?只剩了一片蹂躏之迹,两面毗连的田禾,却依然是黄云满地。黄千总问道:“这两面毗连的田,也是你的么?”翰昭道:“两面都是别人家的。”黄千总道:“这又奇了!既是强盗抢割,他又何分彼此?何以你家的便抢得一颗不留,人家的却一颗不动呢?”两句话问得翰昭无言可答。黄千总道:“只怕你欠了人家钱债,人家来取去抵债的罢。”翰昭道:“我并没有欠人家的债,或者仇家是说不定的。”黄千总大喝道:“既然是仇家,你怎么报的是强盗?好不知轻重的村夫!你可知地方上出了盗案,地方官要担处分的呢?这种话好胡说乱道的么?你这是遇了我,要到文衙门里这么一说,先赏你这厮一顿嘴巴!”说罢,拨转马头去了。翰昭目定口呆地怔了一会,只得回去告知凌氏。凌氏听了,也是无法可施。翰昭道:“不如通个信给天来侄儿,叫他回来计较。”凌氏道:“这可不必了。此刻将近年下,糖行里生意正忙,不要又叫他分了心,并且叫他回来,也不过是叹上两口气。他的怕事,比你我还厉害呢。”翰昭只得罢了。这里凌氏又张罗周济了各佃户,方才拜谢而去。幸而年来他们糖行生意还好,又是向来宽裕人家,虽然吃了这个亏,还不至于亏累。要是差不多的人家,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
闲话少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是腊尽春回,交到雍正六年戊申了。天来在行中料理生意,直到年三十夜,方才同了君来、养福回家度岁。广东风气,大行店家,新年里总要到正月二十几才开张,所以天来兄弟父子,就得在家多盘桓几日,以叙天伦之乐。
贵兴那边,景象又自不同。一班酒肉兄弟,狐群狗党,终日不是赌钱,便是吃酒,偶然取过锣鼓来,乱打一阵,这就算他们最清雅的顽意儿了。
一天早起,天井里两盆兰花开了几朵。贵兴便大高兴起来,要置酒赏兰,在去年打不尽的裕耕堂上,大排筵席,真是群凶毕至,众丑咸集。饮酒中间,贵兴忽然停下酒杯,叹了一口气。宗孔又忽然扭扭捏捏、摇摇摆摆地问道:“吾问侄老爹者,为何忽然而叹气之乎?”贵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道:“叔父怎么掉起文来了?”宗孔呵呵大笑道:“我近来亲近了区老表台,听见他常常的‘之乎者也’,我染了他点书卷气,也来学学。这句话,文便掉了,只是那个‘也’字还没有安上去。”说得众人一齐大笑。爵兴道:“笑话慢说,端的贤侄为何叹气?”贵兴道:“我只恨天来那所石室,坏了我的风水,不然,前年我就中了。中举之后,一定是连捷的,连捷起来,我还是个状元。你想去年丁未科的状元,怎么还会让给一个‘彭启丰’呢!”(雍正五年丁未状元彭启丰)爵兴道:“这个何必心焦!他那所石室,总不能死守着的。好在今年不是乡试年期,我们各尽能力,尽今年弄了过来,纵使弄他不过来,硬拆也要拆了他的。包管明年己酉,贤侄高中一名解元,后年庚戌连捷大状。我这里预贺一杯!”说罢,吃干了一杯酒。众强徒一时又欢呼起来。贵兴道:“我想我的运气,真不如人。你看今日赏花,那花盆都是粗货,往日南雄广源店,本有二十四个玉石花盆,还有一堂花梨木桌椅,却又被天来拿去了。若在这里,岂不光辉!”宗孔大叫道:“既是广源店的东西,就是两家都可以用的了。他是甚么人,敢拿了去!来,来,众兄弟们帮个忙,同我去拿了来!”说着就要走。爵兴道:“且慢。贤侄既有此事,你可写个字条儿,只说同他借来用。他要是肯呢,我们这个就是刘备借荆州;他不肯时,我们就去抢了来。这是先礼后兵,他却怪不得我了。”贵兴大喜,就写了个字条,叫喜来去借。喜来去了许久,回来说道:“不肯,不肯,他说东西都在省城,被人家借去了。”宗孔跳起来就要去抢。爵兴道:“你们且慢,等我分派这件事。要贤侄带了头,先叫开了门,只说一来拜年,二来当面求借东西。有你带了头,以后就没有事了。若是教别人去,他明天到衙门里报一个盗案,那可怎么得了!虽然谅他也不敢,然而总不能不防到这一着。”贵兴道:“我亲去了,怎么就没事了呢?”爵兴道:“贤侄自己去了,他那里还好告?就是告到官司,只说我们中表至亲,闹着玩的,谁稀奇他的东西?这就变了个谈笑官司了。”宗孔又跳起来道:“妙计,妙计!我侄老爹几时做了皇帝,封你做个军师。”爵兴道:“不要胡说!”宗孔道:“状元升宰相,宰相升皇帝,这有什么稀奇!不要多说了,侄老爹,走罢。”拉着就走。众强徒一拥而去,只剩下爵兴看家。众人一拥,到了梁家门首,贵兴道:“他看见我们人多了,一定不肯开门。你们且悄悄地站在两旁,等我打开了门,你们就一拥而入。”众人点头应允。贵兴便去敲门,祈富便问是谁。贵兴道:“是我。”祈富听得是贵兴声音,吃惊不少,不敢开门,飞跑到里面报信。凌氏等也吃了一惊。未知开门与他否,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