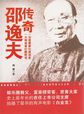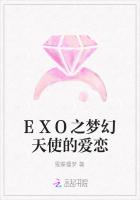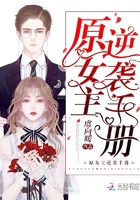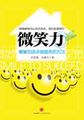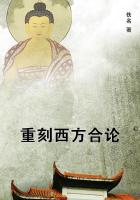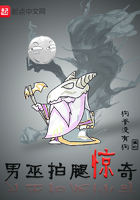梅蕊犯寒开
梅花,小时候就是我的最爱。虽然不曾亲眼见到过,更不懂其骨、韵、神等诸多梅的神韵,但这般傲寒的花枝,在画页里常常看到,也就远远地爱了。我没有生在那样的风雅之地,于冬天也少有这样那样风雪中的枝叶,更不要说梅般的花朵,但喜欢得却丝毫不虚浮,竟然朝朝暮暮地都在心里。
那时候喜欢画画,尤爱画花,最爱的自然是梅,也就抹黑为枝干,点红为花朵。涂涂点点,彼为得意,常常忘情于这红黑之间。如今再看儿时的涂鸦,自是笑得风高浪急,但对梅,却是更加地喜欢了。
青葱年华,也和一个叫梅的姑娘一见成缘,牵牵依依不觉已经是半生云尘。这般幸福花开,果然不枉了我少小对梅的痴爱。
看来是,缘生缘起缘在心啊,不是吗?
对于欧阳修,只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那自然是《醉翁亭记》。知了他的文,也就爱了他的人。仰望之中才觉得他是我心中的梅花一树。无论他身处何样苦寒的境地,依然锦绣在心,傲骨在身,毫无悲怯之声。即使权居峰岭之巅,还是大有品节和虚怀。特别是繁华过后,归于自然,更见青青心境。最是落叶萧萧的时候,不失风骨铮铮笑对云舒云卷。
宋朝,是历史中艺梅的兴盛时代,欧阳修当正是应了这岁月的机缘。我与他在书卷中相遇,再不愿是擦肩而过的匆忙,从此翻捡着北宋的文字细细品咂。
文字,是当下人与他相牵的缘。
一切,从四川绵州的一所半旧的院子说起。墙是青砖,方方正正地围起几间房子,虽然大小不一,倒也很规整。漫墙有几株青藤,依门是几棵绿植。西墙下,一丛翠竹;东墙边,似是一篱蔷薇。院中间,有一株小小的枝叶,细了看,却是新栽的梅树小苗。求风骨,更求朝气,当是主家的心境。这般院落,朴素之中倒也有几分品味,自不是一般的民间宅院。上房临窗的桌椅间,一个中年男人正手持书卷,但似又无心文字,面有忧郁之色。这就是欧阳观。
欧阳观,一个四十九岁才考中进士的老男人,实在用不上大器晚成之说,更何况他一直碌碌于底层官吏之中,没有风云作为。但故事无法让你绕开他,一绕就是我的错。
景德年间,对于欧阳观来说,不是欣喜的岁月,年纪堪堪半百有余,仕途灰暗,更让他心生凉意的是,膝下无儿女承欢。至于前妻,虽然育有一子,他却一纸休书,将母子二人散于老家的荒野之中,也就一并忘却了。后来孩子长大,千里迢迢来相认,欧阳观虽然勉强认下,却一直冷冷相待,竟然不如下人能得到他的一点儿温言热语。这般倒也惹了邻人亲朋不少的怨责,但欧阳观却从无悔意,难说不是遗憾。
是谁负了谁?
爱恨纠葛,有时不说也对,有时不说也错。更何况这般早已迷漫于历史之中的情感烟雨,对错本来就无处说。
再娶的郑氏,也曾是望族之后,只是到了她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不见繁茂之姿,但毕竟是有诗书的濡染,厅堂之上,房厨之中,很是得体。更在欧阳观夜理公务的时候,秉烛持扇,理难解愁,这让他大得宽慰,很是欣喜。转年郑氏孕满,生下一个孩子,可很快夭折了,这让欧阳观心中的喜悦瞬间水泼冰镇了一般。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如树木在秋,落叶渐疏,不见前程,也就视儿女为春天了,对孩子的渴望想来是迫切的,再遭遇这样的打击,实在是有点儿承受不起。那些日子,也真的就是冬天的景致,寒意阵阵,悲情瑟瑟。
少妻懂他,植一株幼梅,续欧阳家的根脉,传他的风神。
错过的,也许就是无缘,不论怎样的情感。孩子也是。父母儿女,缘聚一家,是几生几世的好缘分?
这般的说道,不过是劝人的辞令。身在其中,又有几人能自解心结?
好在郑氏年华正蓬勃,很快又怀孕了,这让欧阳观又打起了精神。处理完官衙的事务,也就急急忙忙回到家中。看着妻子日渐丰盈的腹部,他是欢喜又担忧,生怕再出什么差错。作为一个小小的军事推官,虽然没有多少俸银,但欧阳观尽量想方设法侍奉好妻子的饮食,扶持好她的起居,除非是官事推脱不开,很少让下人们动手,多是他亲力亲为。
说来欧阳观此人,比郑氏大了三十岁,本有老夫少妻之怨幽。但时日渐深,欧阳观正直仁善,清廉勤勉。特别是审理案卷,尤其认真,一一细查,绝不潦草行事,冤屈一位好人。诸般的好,让郑氏感念在心,再怀身孕,也就格外小心,以期能顺利产下一个健壮的儿子,好为欧阳家绵延烟火,更憧憬孩子长大成才,光耀门庭。每每丈夫伏案夜读,她轻抚男人的脊背,都充满不尽美好。
窗外,那株小树苗,正沐浴在甜甜的月光里。风,浅浅地吹着。
景德四年(1007)六月二十一日,正值盛夏,当为荷香盈门,蛙鼓敲窗的日子。深夜,欧阳观无心这些,他在外屋地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时不时地搓几下手,稍显焦虑。灯光将他的影子忽高忽低、忽东忽西地映在墙上。里间,郑氏的呻吟声不时传来,让他心神难定。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对他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日子。
一丝风也没有,好闷,欧阳观解开了几粒小衣的扣子,却依然烦乱。
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欧阳观走到了院子里,他长长舒出了一口气,望向夜空。那里,繁星点点,璀璨美丽,这让欧阳观的心稍稍放松了下来,朦胧中想起了遥远的老家,和更加遥远的童年。一缕月光一样的笑意,在他的嘴角淡淡泛起。忽然,高空中亮起一颗明星,是那样的璀璨,似乎比那西斜的下弦月还要明亮。恰在此时,一声婴儿的哭声高亢地传来。欧阳观愣了一下,倏地冲进了里屋。
疲惫的妻子软软地笑着,而她的身旁一个肉肉的小人儿,正手脚乱舞地大哭叫着。
寅时,这声男婴的哭声,对于欧阳观冷冷的心境,对于这个冷冷的家境,真的就是一枝梅花破寒而开,日子忽然就热火了,忽然间就芬芳了。
欧阳观从没发现妻子这么漂亮,他这个老男人,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只是扎撒着双手傻傻地乐着。这个早就做过父亲的男人,也忽然发现孩子竟然是如此的可爱,在他心里,这才是他第一个儿子,真正的儿子。
窗外,晨光熹微,星星黯然,唯有那颗星,愈显明亮……
童年,是每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那水一样纯净的日子,清澈、透明、唯美、无邪,动是波光粼粼,静就映了蓝天白云,伴了鸟语花香。
四岁的年纪,真的不叫人生。人生,太过于老气横秋。绵州的欧阳修,也度过了这样一个清澈的童年,清澈得了无尘烟,清澈得没有记忆,清澈得无处可着笔墨。
欧阳修不写,我也不写,真的,无论多么美好的文字,也无法写就孩提那最初的时光涟漪。只有那棵小梅树,一季一季长高。
惊笋欲抽芽
远方,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自己心中的远方吧?无所谓期待,无所谓盼望,无所谓追求,这多是少小年纪的一种小小幻念,时不时在心中泛起,如天边的云朵。那时,也许不懂得远方是什么,只是意念中的一种神秘之地。
不知道你小时候是否有这样的闪念,我却是,常常独自发呆,晴日里有,星夜里有,遥想着不知的远方,没有具体的所指,只是一片茫然的心灵烟岚。
许是因了这孩提时心里的臆念,我才有了后来的背井离乡,从此流浪八荒,至今,依然漂泊在路上。
在路上,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欧阳修来说,那绝对是一种新奇与惊喜。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通往泰州的官道上,一辆马车不急不缓地辚辚而行,车上正是欧阳修一家人。前些日子,一纸诏书到达绵州,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只好奉旨赴任泰州军事推官。一路山水,一路风雨,一路日夜,这一切对于仅仅四岁的欧阳修来说无一不是欢呼,他望着窗外,不时地尖叫着,还时不时地和母亲说上几句,“娘,快看,那山好高好高啊。”“娘,那山上的水一直往下流,是从哪里来的呀?”郑氏用微笑回答着儿子,偶尔还抚摸一下他的小脑袋。而欧阳观闭目斜倚着车厢,略显倦怠,就像他倦怠了官场这般,无心一路的风景。
风景和人一样,看一眼都是缘。可欧阳观不是不惜缘,年近六十岁的他,已经懂得了宿命,就像他和妻子、儿子,虽然相亲相爱,但不会一直车马同行。一个驿站有你,一个驿站无他。没有什么缘是不败的花朵,永远暖在掌心。有风,才有景。风,本就是一种到来和失去,惹你心中的尘埃。
看懂缘起缘灭,你早就不是少年。枯了的年华,已经不惹风雨。欣喜几何,其实正是老与不老的刻度。
泰州,对欧阳修来说,这一个远方,只是他记忆中的一闪念,也许根本就没留下什么,但这里绝对是他人生的转折地,从此那弄水玩泥无忧无虑的童年再无处寻觅。清澈,再无。
小小的他,无从觉悟,命运却已经布下没有退路的格局,没有左右。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折转看似无足轻重,经年再经年之后回望,路,已经是大相径庭的春秋风雨。一磨砺,也许成就了宝剑的锋芒;一苦寒,也许成就了梅花的芬芳。古语不是街头的闲言,往往是大智慧的哲思。的确是。
也许是一路的颠簸吧,到达泰州的欧阳观身体就不曾舒展过,他只是勉力支撑着,不敢马虎于公务,不敢苟且于卷宗,然而,拖沓日久,再也无法坚持,终于躺倒在病榻上。是夜,欧阳观也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拉着欧阳修的手,静静地望着妻子,他那目光里是有许多的不舍,是有许多的希望和嘱托的吧?偶尔亮色一闪,他是否又想起了妻在绵州院中栽下的梅。
爱上一座城,是喜欢一个人。对郑氏来说,悲伤于一座城,是失去一个人。短暂的泰州,却是深渊的抵达。郑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地感受到,原来欧阳观这个五十九岁的老男人竟然是她不能失去的依靠。可不能失去,却生生失去。欧阳观的病逝,让她顿然手足无措,她号啕大哭。小小的欧阳修也大声地哭喊着。其实,他还不懂得悲伤,只是见母亲的痛哭而感到害怕而哭。
欧阳观只是一个底层小官,本就廉洁奉公,又加上他喜欢扶弱济贫,也就没有给家中留下什么积蓄,对欧阳修母子来说,日子实在是难以为继的。好在欧阳观虽上任泰州日子不久,但因为他生前的好名声,有同僚和百姓们接济这个塌了天的家。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郑氏不得不再想其他办法。这个原本藤蔓一样的女人,忽然间要挺起腰成为家庭的廊柱,可实在是无力和无奈。天地苍茫,她竟然发现没有哪里是自己一家人的栖息之地,泪水再次漫溢了她的脸颊。忽然,她的眼前闪现一丝光亮,她想起了欧阳观的弟弟。
三口之家而来,三口之家而去,听着没有什么,却已经不是食可饱,衣有暖的曾经。丈夫离去,小女儿的出生,家,再没有什么可遮挡风雨。
泰州,怕是哪里也不见了郑氏的泪痕?原本是,若没有后来欧阳丰碑一样的身躯,即便是翻遍所有的史料,也不会找到郑氏这样一个普通女人的影子吧?
普通,就是烟尘,悠然散去,再无影迹。
可是,一个母亲来过,在这里留下了她匆匆的背影,在泰州的书志里,留下泛黄的印记。今天的泰州人读起,感叹应该用更多的善良将这母子三人留下。
远行,又一次远行,欧阳修却没了那种新奇,一路默默无语,在他原本清澈的心中,似乎正渐生尘烟和悲苦吧?他开始感觉到了命运的鼓点,正轻轻地敲在他的心头。而郑氏,忐忑着,随州,将是她一家三口怎样的一个远方呢?
随州,终是到了。
一路的艰辛不必多说,一个女子,手里牵着四岁的儿子,怀里抱着几个月的女儿,诸多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让郑氏安下心来的是,她从小叔欧阳晔的目光里,看到了和丈夫一样的良善和温厚。
见到嫂子和两个孩子,欧阳晔一种悲伤涌上心头,想不到和哥哥几年前的分别竟成永诀。他上前一步,抱起欧阳修,他决定倾尽自家的所能,来抚养这一双儿女,以慰胞兄的魂灵。
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些身边或者远方的亲人,没有感觉到那么重要和亲切,但关键的时候,你却会感觉到那种爱是在血液里,一种让你无法舍却的澎湃和撞击。不是吗?
在远方,在某一片荒野抑或公园的角落里,每每看到一株狗尾草的时候,我都格外激动。因为那是小时候老家门口和房檐上的小草。亦似这种亲情,不在岁月里时时摇曳,却一遇春风就点点萌绿,因为那些情感的籽粒早已布满心中。
心若在,绿就起。血脉情深,不在身外。
郑氏虽然出身在没落的望族,粗重的活计还是做不来的,但毕竟非常勤劳,再加上她非常感激小叔子对她一家人的收留,所以也就更为勤苦,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许是父亲的离世,让欧阳修忽然懂事了许多,在母亲的引导下,他对书卷开始喜欢,一本简单的启蒙教材,他常常能看到日落西山。
绵州,欧阳修的出生之地。泰州,他生命的第一个远方。而随州是他小小的又一个到达,然而,这里其实才是他人生蹒跚初步的地方,因为一颗文艺的种子正是在这里悄悄萌芽……
青红春自华
一朵春花的欢颜,一羽秋叶的薄凉,这不是文艺的全部,文艺的四季里,承载了太多太多。没有一颗文艺的心不历尽风霜。
当然,欧阳修的童年,我们不能用太过沉重的词句,但对于一个想读书识字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困难了许多。叔叔欧阳晔微薄的薪酬支撑这一大家子人都免为其难,实在不能为他提供笔墨纸砚、应时的教材,更不要说请教书先生了。好在他有一个识得许多文字的母亲,引导着他在知识的路途上慢慢起步。
郑氏知道,作为欧阳家的骨血,欧阳修是丈夫生命最后的寄托和期望,她对孩子就非常严格。但她明白,玩耍毕竟是孩子的天性,不可过于苛刻儿子的学习,所以她在忙完家务之余,时常带孩子到城外走走。那天,她寻得一片小小的沙地,在那里,她带孩子插草为森林,堆沙为峰岭,划一条沟痕为河流。一家人竟然成了“开创江山”的伟人,玩得好不开心。当一切抹去,又可以重整“山河”。忽然,郑氏灵机一动,抹平一片沙地,用荻秆在那里写下了“天地人”几个字。欧阳修毕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一阵欢呼,也抹平了眼前的沙土,学着母亲一笔一笔地勾画着。
写了,抹去;抹了,再写……欧阳修觉得这特别有趣。于是,晨光里,晚霞中,这里成了欧阳修的大课堂。
狭隘的心胸,是不会有壮美的情怀的。而欧阳修,也许正是沙地上无拘无束的学习方式,成就了他自然、随性、亲和的文风吧?
初心镌刻,一生相随。
沙滩上这个勤奋好学的小小身影,感动了不少当地的好心人,他们十分怜爱欧阳修,常常借书给他,甚至还送一些纸笔。就这样,从草秆树枝画沙开始,小欧阳修渐渐接触到更多的文字。那些借来的书籍,他不仅用心去读,名篇佳作更是反复读诵,甚至抄录下来。那时的宋朝,颇为流行晚唐诗韵,欧阳修在母亲的引导下,也都细细琢磨,那种精巧的构思,深入浅出的格调,深深影响了欧阳修,一直到他的晚年。
勤奋,是成功的捷径。
欧阳修的确是一个极上进的孩子,他不肯错过每一次可以学习的机会。有一次他和母亲在一个庙宇前发现了一座唐朝大书法家笔迹的石碑,他无数次来到这里,小小的手指沿着那阴刻的文字慢慢滑动着、滑动着。从此,这石碑的记忆,也就一直矗立在他的情怀里。后来他为官处处,无不专注于考录金石,从而编就了我国最早的金石巨著《集古录》。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是马上的皇帝,但非常崇尚文治天下,因为他的倡引,宋朝历代帝王都注重文化建设,由此读书之风蔚然天下。在这种大环境下,好学的欧阳修成为一方父母们教育孩子的榜样,大人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和他交朋友。这使得欧阳修身边聚集了一帮渴求上进的孩子,也使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文集书卷,知识更加丰富充盈。
写到少年时的欧阳修,情节无法绕过随州城南的一座宽大的院落,这就是欧阳修的好友李尧辅的家。李家虽然不是权震一方的官宦门庭,但家境富足,上下老小又都以书香为爱,所以家中藏书尤为丰富。李尧辅常常约了一帮小伙伴们到家中玩耍,疏密得当的亭台楼阁之间,参差交错的树木花草之中,就成了他们嬉戏的乐园。
李家大人虽然身处富贵,但绝不为富不仁,对出出进进的每一个孩子都非常喜欢,任他们四处疯闹,从不喝斥。那一天,小伙伴们捉迷藏,一个孩子为了藏得更严密些,钻进了一个大房子的夹壁墙中,狭小的空间里堆了不少的杂物。他使劲儿往里挤着,忽然一脚踩翻了一个筐,哗啦啦滑落出来一堆书。这些孩子本就是好奇的年龄,再加上他们非常好学,便将书收拾到了屋地上,各自挑选自己喜欢的。欧阳修相对这些孩子来说,读的书更多更杂,那些书他大都看过,也就不怎么感兴趣。忽然,一本被小伙伴踩在脚下,非常破旧的《昌黎先生文集》引起了他的注意。欧阳修接触过许多的书典,但“昌黎先生”的名字他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几步向前,翻开书卷,只读了几行,那自然入心的文字,就让他激动起来。他急忙跑到李家伯伯的房内,恳求借阅这本书。
李尧辅的父亲对欧阳修本就非常喜爱,更何况那是一本非常破旧的书,也就很爽快地答应将那书送给他了。欧阳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瞪着一双大眼睛怔怔地看着李尧辅的父亲。等李尧辅的父亲又说了一句:“那书,是你的了。”他才躬身说道:“谢谢李伯伯。”然后转身飞也似的跑出了李家的大门。
欧阳修双手抱着那本书,在大街小巷里狂奔着,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宝贝。
“娘!娘!”他激动地叫着母亲,跑进了家门,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下,呼地扑在了地上。郑氏心疼地去扶他,他把捂在胸前的书看了看,说:“没事,没事,宝贝还好好的。”
《昌黎先生文集》成了欧阳修床边的最爱。
偶然,似乎是生活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但偶然却时常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历史的宏大走向。岁月长河中有多少偶然,让史学家的笔锋一顿再顿,甚至反复转折,也让后来人一一惊诧。
一本书,却是一世缘,成就了一朝文化的辉煌,你待怎惊叹?
夹壁中的那筐旧书,多是普通的书卷和一些破旧不堪的文集,在李家看来,是上不了桌案和书柜的了,被当旧物处理了。若没有那次偶然,也许就会慢慢腐败霉烂。可正是那次偶然,欧阳修恰好在,恰好爱,也就成就了与韩愈隔着朝代的烟雨遥遥相望的另一座文学高峰。
在母亲和叔叔的教育和鞭策下,欧阳修文德双修,进步飞速,小小少年名满千家,一时间春风十里,飞流三千。
涢水虽匆匆,却映照着一个少年的影子,千年更匆匆,却依然见那波光点点。
小小随州,出土了曾侯乙墓编钟的随州,欧阳修也是这里真正孕育的文化奇迹。这个被视为荒薄之地的小州城,陡然间天高云阔,让我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