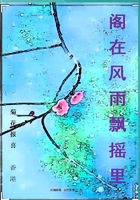仿佛在向我询问,又仿佛在自言自语。
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喜欢作茧自缚,自食恶果,越是挣扎反而陷的越深。”
他落下一枚棋子,黑曜石的映衬下,他的手肤白胜雪。
我不明所以,但我却并不想明白。
接下来。
我未曾答话,他也未曾再语。
我们依旧对着弈。
直到傍晚。
今天的傍晚,火烧云格外的好看。
太阳照进窗中,给屋内打上了斑驳的剪影。
最后,他落下一子,彻底结束了棋局。
他胜了。
他其实一开始就可以轻松完胜。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如今他的结束,不过是因为,时间到了,该说再见了。
有很多时候,他也很懂我。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
将精致的雕花檀木窗缓缓开到最大。
金华阁建造的十分高大,金碧辉煌。
我斜坐在窗棂上。
望着下方此时熙熙攘攘的人群。
街市热闹极了。
晚风吹乱了我鬓角的碎发,若很多年前他的手轻抚过我的脸颊。
我半个身子探出窗外。
伸手从发中取出那支早已萎败的杜鹃花,细细的斟酌。
平静得心如止水。
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
我与楼下的闹市恍若相隔天边,可明明又近在眼前。
夏日温暖的风吹起我火红的衣摆,浓烈的夕阳映照在衣裙上,显示出一种近乎妖冶的橘红。
我静静的望着下方的闹市,我与他们,仿佛是两个世间的人。
萧逸不知何时已走到了我的身边来,离我很近。
我回头看他。
他的脸庞在如血的夕阳下,有种近乎妖邪的美。
我突然间就想起小时候的事。
想起我、他、还有阿芳,我们三人整日的胡作非为。
那时,我们三人是学院中出了名的小霸王。
当然,阿芳其实很听话很乖巧,坏的只是我和萧逸。
但是我们三人常常在一起,阿芳被我们的名声殃及罢了。
现在想想,那时候是多么的快乐。
我不知道他们的虚情假意,至少还能活得自得自乐。
我们一起逃过课,下池塘赤足捉过鱼、摘过荷花,上树采过果子、掏过鸟蛋,还趁着夫子打瞌睡拔过他花白的胡子。
整日嘻嘻哈哈,不务正业。
全然没有身份的束缚,身份的迫不得已。
不知那时的他们,幼时的他们,是否已经很有心机,是否已经学会深藏不漏,是否对我有过半分真心呢?
也许吧。
只是如今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永远也回不到当初的我们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我又想起亲生母亲、亲生父亲、继任母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元琛和妹妹元芳、丫鬟香荷和丹红、腹黑的太子、狠辣的皇帝。
想起当初的他们,想起现在的我。
从十二岁到十七岁,再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这十年,不过是我从岁月过往中偷盗而来。
真正的元相嫡长女元玉早在十年前就死在了那间祠堂里屋的门口。
现在活着的,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那时的我就应该死去,死在虚假却美好的过往,死在天真无邪的童年。
然而我终究还是活了下来。
我太胆怯,太懦弱,太害怕死亡。
而如今的我早已明白,这世间有太多的东西比死亡更为恐怖。
那便是生不如死。
死亡,于我而言,才是最好的解脱。
夕阳的光辉已徐徐落下,只余下最后一抹血色照耀在街边小巷。
我居高临下,将天地尽收眼底。
望着这般惊艳的晚色余晖,我的心中陡然间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
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望进他的双眼,努力地绽开一抹笑颜,对他轻轻的说道:“日落了,说再见。”
下一刻我的身体已如一朵残败的杜鹃从窗口飘落。
下坠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眼角有什么东西反射了余晖,晶莹如水。
他一动不动,就那么看着我从高耸的楼阁上坠下。
我仰面朝上,嘴角却是微微扬起。
我突然间想起轩。
突然间想起和轩初见时他埋掉的那只猫儿,也不知那只猫儿到底因何而死,竟让小小年纪的他那般悲哀,可惜再也没办法问他了。
我突然间想起和轩在酒宴相识时,他唤我作小姑娘,那样老成却并不突兀,我多想对他说,我还想再听他唤我一声小姑娘,可惜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突然间想起轩出征那日临上马前,他与我擦肩而过之际,稍稍停留,在我耳边轻轻的说:我终于明白你那日为何说,你父母不让你与我走了。
我想知道他是否已然全部了解了那些恩怨纠葛,可惜我再也无法得知了。
最后定格在记忆中的画面,是爹娘请医失败后憎恶的脸,阿芳和哥哥似惋惜又似嘲讽的眉眼,以及最后我坠下楼阁的瞬间,萧逸复杂的神色。
一切都该结束了。
下坠的力道,风灌得我很是难受。
而我的心却是无比的宁静与祥和。
是了,我明明也知道,轩如果能回来,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回来了,这五年,不过是我自欺欺人、自作自受。
我望着半红半灰的天空,缓缓的闭上了双眼。
彻底落地的那一瞬间,疼痛传遍四肢百骸。
那种骨头碎裂、头部重击、血液倒流、全身剧痛的感觉,却是那么的令人解脱。
此时此刻,我才是真正的自由了。
我渐渐失去了最后一抹意识……
一抹艳色的残阳落在身上,像是一支哀伤的歌在轻轻的奏唱。
原来这世上,有两种东西最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前者伤眼,后者伤心。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