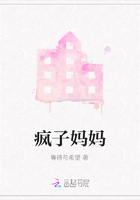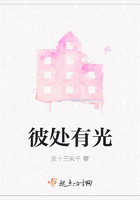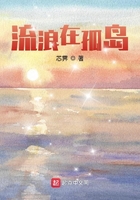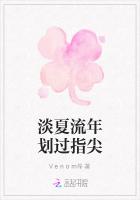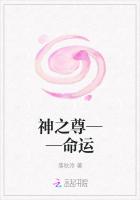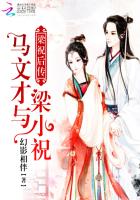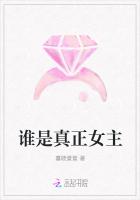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用这个时间,是因为年岁太久,具体哪一年对应的很多事可能已经想不清楚了,毕竟也是上个世纪了不是吗。然而,90年代又好像就在眼前,当人们在谈论90后,95后的时候,是现在正处于最关注社会和最被社会关注讨论的一代。那是我们成长的年代。
那大概是一个腾飞和没落并存的时代。有人下海发家,有人为发家的人打工,有人终于把农村户口改成了非农户口,但却依然入不了大城市的户口。有一些流行起来,但流行的很快会被更流行的取代。
陈先花,我,陈在当地是个大姓,陈家先字辈的孩子,女孩名字里带个花或者梅再常见不过了,虽然总是要解释自己不是“鲜花”,是先字辈的花,不过,好像也并没有更高级,嗯。
我的好朋友,齐思思,我的小学时光几乎都是和她在一起度过的。
好像女孩子天然就喜欢群体行动,哪怕单位只有两个人,一起去上厕所一起放学回家同一段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对齐思思一直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是羡慕,可能是嫉妒,又或者是,我觉得我需要她。
首先我最嫉妒她的一点就是,她家住的离学校可太近了,一出学校门走两步她就到家。每天上学我要提早很多出门,我走到她家门口喊“齐思思”,她居然才起床!然后我就背着书包跟着她看她慢悠悠的刷牙洗脸再去厨房盛一碗粥吃个馒头……再去拿书包,这个时候我就不是第一个到教室的了!不过没关系,她也不是,我们是一块到教室的,这就可以了。
我不是和爸妈住在一起的,别误会,我不是孤儿,我爸妈也没有抛弃我。他们只是,为了赚钱,去了广州打工。嗯,我们这很多家长其实都在“外头”,就是大城市的意思。没办法,我们这里实在是太小太落后了,种地是没有什么钱的,够自己吃就很好了。大部分青壮劳动力都出外务工了,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拿回来的钱虽然不多,但也比做农民收入高多了。其实打工和种地,本来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作,但我总觉得打工更高级一些,毕竟大城市总归比黄土地更好吧。所以我内心是骄傲的,别人要问起我爸爸妈妈,我总会很得意地说他们都在广州呢,仿佛我的爸妈都是广州人似的了。
不过其实大部分的出外务工的都是只有夫妻一方会“出门”,就是出外打工,这样孩子也有人照看。一部分会是夫妻双方都出门,爷爷奶奶还年轻带着孙儿。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我,是由亲戚照看着。齐思思的爸妈也是都出门了,去了上海,齐思思也是由亲戚照看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更加有了亲密的理由。
对了,我们的学习都特别好,不是我考第一就是齐思思考第一。
在为数不多的和爸妈相处的时光里,爸爸教了我认字和背诗,可能因为这些比同龄人早的积累,小学的课程真的都太简单了。
齐思思的话,应该也是因为她爸爸教过她吧,不可能她天生就比别人厉害。我不管,肯定是她爸爸也教了她的,肯定是这样子的。
虽然在旁人眼中,轮流第一是一种很良性的状态,但对我们可不是,我要得了第一她会默默地不高兴和我说话都劲头都弱了点,她要得了我可能都会故意不和她说话的。当然这也并不影响我第二天上学还是会在她家门口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