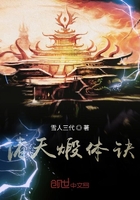凝香刚拍哄着惜墨睡着,与丫头们计算着沈冲天出行日子,聊些家常闲话,忽听报说知府和守备带人闯入,要查抄沈府。凝香心中四顾无人,只得吩咐乳母丫头看护好小姐,无奈自己抛头露面,带人站在屋下,直面来人。
一群人直入内堂,文超夹在人群中,见到一位妇人,二十岁上下,满面怒容环视众人,对质道:“此地是沈府,乃是私宅!你们私闯民宅,还有没有王法!”
知府轻蔑地斥道:“一个妇道人家,厉害什么!私宅?只怕是贼窝吧。收到线报,沈冲天真实身份乃是天狼皇子,私潜入我国中,隐藏身份,意图不轨。如今举国严查天狼奸细,你家是头一个!”
凝香冷笑一声:“线报?那个吃饱撑得线报,造谣中伤!”
知府等的就是这句话,否则今天他也不会让文超带人跟着,就是将仇恨引向出首之人,自己金蝉脱壳。他假充公断道:“沈冲天的义兄,文超文公子出首。怎样,他的话还能有错?”
不用说,下面三个带头的,除了穿官袍的知府和守备,平民那个定是文超了。凝香横眉立目骂道:“文超,你个背信弃义,求荣叛友的小人。枉公子与你八拜之交,多年亲如手足之情,全都喂了狗!如今你趁他不在,暗地勾结官员下不实之罪,栽赃陷害公子,还强闯入他家,肆意翻抢搜刮,抄没他的东西,拘禁他的家人,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文超并不回答,转身对知府道:“府台大人,我的事情已完结,剩下就有劳大人。至于捉拿奸细的事,全是大人功劳,小子不敢居功。只是一件,这个女子是沈冲天的侍妾,是他在中原所纳,为我地地道道的中原人,所有亲友都知道,身世倒是清白,也与沈冲天所为无关。不若由我做个保人,带走她如何?”
知府看看凝香,又看看文超,笑笑不语。
文超话音落,见凝香身边的两个丫头立时站在前面护住她,遂指挥家丁将三人一并扭了手,强行拖走,把沈府的烂摊子交给知府便离开了。
凝香和两个丫头被一路带回文家。文超将凝香单独带入书房,这才假惺惺道:“姑娘受惊了。一切均是沈冲天种下恶果在先,只是带累了姑娘。其实我还是心疼凝香姑娘的,刚才我若不出声,任由官府的人带你过堂,以姑娘的花柳之质焉能受得住啊!再说姑娘内闺之人未必知道他在外面所为,你大可不必因此事受牵连,遭这份罪。”
凝香只是焦急地问:“孩子在哪?”
文超疑惑:“什么孩子?噢……原来沈冲天有个孩子。天狼奸细的孩子,自然也是小奸细,肯定在关押奸细的地方。”
凝香怒道:“你敢伤他的孩子,他一定会把你剥皮抽筋的。”
文超讥笑着分辩:“可是冤枉!我连里屋门都没进,没动孩子。凝香姑娘先关心自己吧。”
凝香目不斜视,正色道:“你想说什么?”
文超继续道:“姑娘应该知道,沈冲天是天狼人。假使你不知道,他那一家子满口天狼话的家人,总不是别人强按栽赃吧?当年他来中原时,在天狼国的身份是小皇子,是现今天狼国皇帝的兄弟。他趁着当年两国关系缓和,贸易往来频繁之际乔装进入中原。他说此来是寻亲,还说他的亲人都是修行之人,不见外人。我问你,他所谓的‘亲人’如今都去了哪里,都做神仙飞走不成吗?那不过是他一派胡言,所谓亲人不过是天狼密探而已,或是任务完成,或是身份败露仓皇离开。现今两国战事欲起,全国境内严查天狼人,像沈冲天这种必是逃脱不了的。姑娘跟着他只会受连累,别说你是中原人,一样没有好结局。也许他身为天狼皇亲,还能侥幸有命回去,你可惨了,两边都不会容你。所以我劝姑娘看明白情势,也给自己留条退路。”
凝香至此已明白文超的意图,她不动声色继续问道:“以你所言,我该当如何?”
文超听见,忙劝道:“我知姑娘在沈冲天身边数年,况且他一向宠爱你,很多他的情况恐怕只有你最了解。因此我不会废口舌去撬别人的嘴,把那些家人交给官府去收拾吧,我只问姑娘。沈冲天这些年与天狼朝廷往来的书信,还有他的宝印,我当年是见过的,所有与天狼有关的东西都在哪里?只要说出来,不劳姑娘费心费力,我自会取来递交上去。到时候我与姑娘都是头功一件。”
凝香终于听明白,原来他们只知道沈冲天的身世,却找不到证据,不足为惧。因此顺着文超的话向下打岔,冷笑一声:“他宠爱我?他若真宠我何不把我扶正,还会娶别人进门,还会跟你们日日流连,夜夜买醉?你们这些狐朋狗友勾引的他不知在外做些什么勾当,反倒来找我要证据?我一个女子,房门不出,知道什么国事,什么奸细,什么证据!”
文超见凝香说话条理分明,言辞伶俐,句句无一字实证,只得言道:“看来凝香姑娘记性不太好。也罢,既然来我家做客,反正沈冲天也不在,就让我好好招待姑娘。姑娘则安心住在我家,莫再惦记家中。什么时候姑娘想起些什么,自可找我。”说罢吩咐下人:“将凝香姑娘带到柴房锁起来!”
自此后,凝香整日被锁在方家的柴房之中,身边的两个丫头被派到别处做粗活,她独自一人,无人照料,音信不通,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形,也不知道惜墨、还有沈府一大家人都去了何处,更不知道沈冲天在何处,何时能找到自己,解救自己离开方家。
沈冲天带着人拼命赶路,终于进入武林,却听见路边茶舍人们谈论,说是武林抓住一大家子天狼奸细,为首的竟然是天狼皇子。沈冲天这一吃惊不小,家中出事了!他不敢冒失进家,带人躲在远处观察,只见沈府已被查封,崭白的封条糊住大门,门上落锁,外面有守卫的士兵,看样子是守株待着沈冲天这只兔子撞进来。
沈冲天唯一担心的是府里的人,凝香、孩子、管家还有所有沈府的人,都在哪里?自己好不容易离开京城,不能在这里自投罗网。周遭的朋友,这个时候唯恐躲之不及,未必会有人帮他。沈冲天忽然感觉自己好无助,他带着身边人化名住进不远处一家客栈,等待时机。
晚饭时,绛纹忽然一手扶住他小臂,沈冲天略侧头,听绛纹在耳旁低语:“公子,进来六七个精壮男子,一直用目光搜寻着,不知是不是找咱们。”
沈冲天镇定低声道:“无妨,这一路上不是说没见到影像布告吗?说明这边形势还没那么紧张,镇定,别让人看出端倪。”他细细倾听着来客的动静,思索着安全离开之法。
这时,就听一个男子高声嚷嚷:“你们说我惨不惨,还不容易得串宝珠,绳索还断了,如今十八颗已经找齐,还有第十九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另一个男子也高声应道:“可不是,这串珠子,第七颗,就是最大那颗是真好,要是再找齐第十九子,就齐全了。”
其他在堂下吃饭的旅客心中纳罕,都说人在外,财不外露,这伙人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宝似的,恨不得嚷得全天下都听见,只怕脑子有病。只有沈冲天听到,掀起心中波澜,因为在天狼皇宫,他在一众皇子中排行就是第十九,而排行第七的,就是当今天狼国主龙少枢!
沈冲天当机立断,也高声道:“店家,半个时辰后送吊热水,再有一壶烫好的烧酒,到头房丁字号,要快,稳妥些,我等着。”
店家急忙回道:“好嘞!”
沈冲天带着绛纹和一个丫头住在头房,四个下人住在相隔不远的一间差房。沈冲天回到房间,端坐椅子上,安静等着。先是有人敲门,丫头开门见是店家,忙接过东西,递上几文跑腿钱。等店家刚离开,又一阵敲门声。沈冲天平静地吩咐:“来了,开门吧。”
门开后,进来一个人,对开门的丫头道一声:“有劳。”听声音正是晚饭时高声叫嚷的那个。
来人站在屋内也不说话,也没动静,沈冲天侧耳听听,言道:“无妨,没有外人,我眼睛不方便,离不开她们,她们也听不懂天狼话,直说吧。”
来人扑通一声跪地,行天狼礼,以天狼语呼道:“微臣参见殿下。”
沈冲天点点头:“你是?”
来人道:“微臣契氏阿止,还有六个同伴,我等同为殿前御林军,受皇命来中原。”
沈冲天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阿止解释:“是殿下的赤红马,马后腿上有我天狼官家特有的印记,还有那串银铃铛紫流苏,极其好认!”
沈冲天满意,大加赞赏道:“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我正愁身边都是柔弱之人,不能办事。我的府里有兵士把守,说明里面有人,今晚咱们想办法回到府里去,把人救出来。”
阿止有些犹豫地回道:“殿下,越过中原士兵带人出来,实在太难,万一被发现,无法脱身。我们既寻到殿下,就不能不顾及殿下安危。”
沈冲天忽然有些焦急:“我的女儿、女人、天狼宫人,都困在里面!”
阿止忠直劝道:“殿下,此事须从长计较,如今风向变了。查抄天狼奸细只是一个借口,据线报,不出三五日,军令就会下达,咱们就要困死在中原了。我们既有皇命在身,自然遵从皇命,望殿下不要为难微臣。”
沈冲天质问:“怎么?你还要把我捆回去不成!”
阿止俯首:“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法,失了殿下,我们有何面目回去面君!”
沈冲天忽而起疑:“是陛下派你们来的?他如何未卜先知。”
阿止凄然道:“是太上皇。当年殿下在中原遭难,音信全无,太上皇和太后担忧,因此选出臣等,扮做汉人,深入中原,打探消息,其后一直未归国。一则探听中原动态,二则,一旦有变,护送殿下周全归国。”
沈冲天亦心中凄然:“姨爹……”
阿止继续劝解:“正是。殿下当年在都中,何等英明决断,识大体,常得太上皇夸赞,如今万不可因小失大啊!”
沈冲天叹口气,思索一时,问道:“车马可备齐?”
阿止立时回答:“只待殿下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出发。”
沈冲天回道:“我身边这六人都要带上。”
阿止应声:“这是自然。”
沈冲天当即决断:“阿止听令:带上你的人马,即刻跟我出发。我带你们去一处地方,那里有一条暗道直通府中。你跟我进去,剩下的在外面备着车马接应,不论能顺利出来几人,子初准时出发。”
阿止叩头:“得令!”
沈冲天继续吩咐:“绛纹,到下面,找到店家打包干粮,带足十几个人三天口粮,剩下的路上再补充吧,买好交给他们装上车。你通知咱们的四个人,收拾细软行装,粗重碍事的,全不要了,即刻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