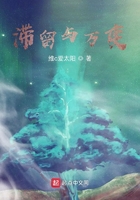密林之中,才被解救不久的半兽狼人和他的魔狼兄弟顾不上休息片刻,就急冲冲的沿着记忆中的路线,带着刘蒙多和金刚快速的穿行。
刘蒙多是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寂静森林深处居然能碰上这两幼年期的冰霜魔狼,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出手相救的原因。
潜意识里他感觉这两魔狼一定跟霜狼氏族部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简单询问之后,这两个倒霉蛋迷迷糊糊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焦急的说他们的母亲有重伤在身,最近一段时间伤势复发急需他们回去照顾。
为了探寻那一丝丝的可能,刘蒙多和塔嘉娜打过招呼,便带上金刚一同前往魔狼兄弟的住处。
四个家伙沿着崇山峻岭一路疾驰狂奔近一个小时早已出了魔猿家族的领地,终于来到了一片满是杂草和低矮灌木丛的山丘。
拨开面前比人还深的杂草,一个三米左右高大的幽暗洞穴豁然出现在刘蒙多的面前。
凝神静听,洞穴深处还不时的传来轻微的低声哀嚎,仿佛承受着巨大的莫名痛苦。
魔狼兄弟闻声气都顾不上喘便急忙冲了进去,不多时呜咽之声便响成一片。
刘蒙多站在洞口平复了一下心情带着金刚也跟了进去。
摸着洞壁弯弯绕绕的走了二三十米,前面便传来一片亮光,几步过去,一个百来个平方的开阔空间便出现在了刘蒙多的眼前,洞穴顶部有一个簸箕大的开口,阳光便顺着开口照射了下来。
等眼睛适应了洞穴中的光线,出现在刘蒙多眼前的画面顿时让他心神一震。
居然是她。。。霜狼氏族酋长杜隆坦的魔狼伙伴阿贝莱.塞格。
刘蒙多一眼就认出了她,他还记得婴儿时出于好奇拔过几根阿贝莱身上漂亮的银色毛发。
曾经冰雪般的银色狼毫早已化作一身杂乱的枯黄,阿贝莱.塞格此刻正蜷缩着虚弱无比的干瘪身躯匍匐在地上的一层厚厚的落叶堆中,口鼻中呼出的气息早已变得微弱无比,生命已然快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刘蒙多红着眼眶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一脚一个踢飞了两个扑在阿贝莱身上的蠢货。
两个哭哭啼啼的倒霉蛋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体重给本就虚弱不堪的母亲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迅速的摸出空间戒指里储存的水袋凑在阿贝莱的嘴边给她喂了几口,阿贝莱本来无力搭拉着的眼帘仿佛有了力气,忽的张了开来,用着空洞无神的眼睛不住的打量着面前这个赤裸着健壮上身的兽人少年。
她太虚弱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突然静止了,只有阿贝莱原本混浊的眼神慢慢的变得清明再到精光涌现昭示着这个寂静的空间还有变化。
阿贝莱感觉自己的状态是从未有过的舒畅,仿佛身上的重担终于离她而去,轻盈自在。
而这种感觉却是在这个兽人少年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才突然涌现。
生命奥义之——回光返照。。。
这个兽人少年的面部轮廓依稀与杜隆坦和德拉卡有几分相像,再加上他身上的那股隐隐约约熟悉的气味,让她始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她就是想不起来眼前的这个兽人少年究竟是谁。
时隔多年,曾经抓着她的鬓毛吊在脖子上玩耍的婴孩早已长变了模样,她要是还认得出来就有鬼了。
慢慢的她的目光又变得疑惑了。。。
“尊敬的冰霜魔狼阿贝莱.塞格阿姨,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霜狼氏族部落酋长杜隆坦和德拉卡的儿子,我的名字叫——古伊尔。”
察觉到阿贝莱眼中的迷茫不解,刘蒙多哽咽着赶紧自报家门道出了自己的出处。
“哦,古伊尔,可怜的孩子,真的是你!”
得到刘蒙多的亲口回复,阿贝莱激动了,虚弱疲惫的身躯也情不自禁的抖动了起来。
“咳咳。。。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你,直到我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撑我的脚步,想不到你真的活了下来,这些年一定过的很艰难吧!”
看着刘蒙多的装扮,阿贝莱.塞格一激动不料胸中一口瘀血上涌,卡在许久不曾说话的咽喉,剧烈的咳了两声才化作嘴边的一丝殷红,不由得又对他这些年的遭遇感到深深的不安。
这也难怪,刘蒙多刚刚一路疾驰狂奔身上脸上满是沾染着尘土的干涸汗迹,全身上下就套了个兽皮围裙,勉强遮住了要害部位。
要不是看这两年发育的太过迅猛,整天漫山遍野的吊着乱晃实在有伤风化,他根本就懒得围这玩意儿。
那一脸衰样要说比流浪汉也差不了多少,就差旁边没个垃圾桶了。。。
久别重逢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阿贝莱.塞格最终还是离去了。
当年霜狼氏族部落领地被突然袭击,虽然氏族酋长杜隆坦带着部落勇士顽强抵抗,但最终寡不敌众在体力不支之后倒在了袭击者的屠杀下。
在最后时刻,杜隆坦用尽身体里的最后一丝力量为自己的魔狼伙伴杀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才让阿贝莱.塞格逃离出这地狱般的屠宰场。
逃离出来之后,阿贝莱躲在远处等着这群屠夫撤离后又返了回去,想要看看还有没有幸存者,可是入眼处遍地都是曾经族人那残缺不全的尸骸,而袭击者的尸体却全被收走没有留下一丝出现过的痕迹。
阿贝莱忍着伤痛找遍了整个领地才在河边的芦苇丛里,找到了一个受伤太重已到了弥留之际的兽族勇士,勇士看见阿贝莱的出现,用尽最后一口力气才告诉了她酋长儿子的摇篮顺着河流漂走的信息。
于是她便开始沿着河道寻找,可一直寻到了这寂静森林深处也没有看到摇篮的踪影,再加上身体的伤势不断恶化,阿贝莱不得不在这里停下脚步寻了一处洞穴养伤。
由于阿贝莱先前已然怀有身孕,没过几个月后还生下了两个孩子,照料孩子的艰辛自是不言而喻,而这对她身体的伤势更是造成了近一步的恶化,最终只得在这洞穴之中蛰伏,直到今天。
冥冥之中,命运的齿轮将刘蒙多带到了她的身边,终于让她能够放下心中的执念坦然迎接死亡。
看着阿贝莱.塞格残留着血迹的嘴角挂上了一丝微弱的弯曲弧度,刘蒙多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走的很安详。
兽人的字典里永远没有什么生离死别可言,软弱的泪水只有粪坑里的蝇蛆才配拥有,只有战斗、战斗、再战斗,才能更好的保护身边的一切。
捏住裸露在胸口外的一截早已布满锈迹的断刃,手指稍一用力折磨了阿贝莱.塞格十余载岁月的罪魁祸首便被拔了出来。
是一把三十多公分长的双手重剑的断刃卡在了干瘪的胸骨之间,幸好剑锋避开了主要器官并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这才让阿贝莱.塞格拖着伤躯活过了十来个春秋。
随着断剑的拔出,一股散发着浓烈腥臭的脓血也随着伤口不断的溢出滴落,慢慢的寖透了地上的一层厚厚的干枯落叶。
殷红的血迹在干枯的落叶上笔走龙蛇,像极了一副摊开的泼墨画卷。
只不过这墨,却是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