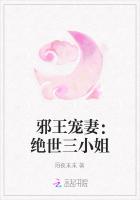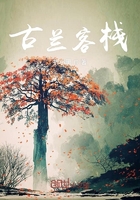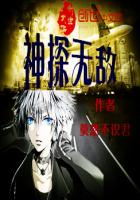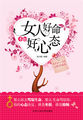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的代表人。1889年获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博士学位,1928年获诺贝尔奖。其哲学宗旨是建立一种以哲学为基础的新的“形而上学”,以摆脱近代科学所采用的抽象的、分析的理智方法,并借助于直觉把握真正的实在,故称为“直觉哲学”。柏格森的哲学显然与唯心论和唯物论都不一样,他一方面对法国的传统,如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保持欣赏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以实证科学研究自然界时,也肯定精神上开展的可能性。所以,他思索的是:到底人的生命意义在什么地方?人的生命意义如何界定?
“哲学家大道”与午夜阳光
4岁那年,柏格森一家来到瑞士的日内瓦,这个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的世界名城,深深吸引着柏格森。高耸的勃朗峰的雪顶倒映在波光粼粼的莱蒙湖上,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然而在日内瓦,对这个未来哲学家一生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些湖光山色,而是城内的一条大街——哲学家大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是由于这儿离柏格森父亲任教的日内瓦公立艺术学校比较近,或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柏格森一家正好住在哲学家大道。虽然当时幼小的柏格森显露出了某种哲学家的气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预示着柏格森今后一生的道路。
在柏格森6岁那年,他和父母旅居在北欧的一个国家。一天,已经是午夜时分了,然而铺满大地的不是暮色重重的黑暗,而是耀眼夺目的阳光。柏格森面对这一自然界的奇景,木然不动,似乎在一刹那间化为一具蜡像。他感到吃惊,内心充满了好奇。他沉浸在神话的幻想里,是不是太阳神阿波罗想让他的孪生姐姐月神阿耳忒弥斯多休息一会儿?神话是哲学的母体,也许这午夜的阳光正哺育着未来的大哲学家的头脑。他久久地观察着这白昼的绵延,这午夜的阳光是地球北极圈以北地区特有的“白夜”现象,对于这样的奇特现象,柏格森怎能不入神呢?他神情专注而严肃,彷佛忘记了母亲就在他身边。母亲慈爱地望着儿子,没有催促他上床去睡觉,也没有用话语去打扰他,她知道,这午夜的阳光正撞击着小柏格森的心灵。
童年的柏格森,像其他男孩子一样顽皮和淘气。在他六七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口的坏牙了,但他害怕去看牙医,因为牙医对于坏牙没有一点仁慈心,总是残酷无情地把它们一个个拔掉。于是,他一旦坐上牙医的椅子,就故意拼命叫喊。后来,牙医为了让小柏格森安静下来,总是往他的口袋里塞50半个法郎,这样他才勉强漱一下口。他知道半个法郎可以买到10条大麦糖,他还能猜出,这是他父母和牙医之间商量出来以使自己安静的办法。所以,他依然我行我素,仍旧采取对抗牙医的态度,结果他父母让步了,没有让牙医把柏格森的坏牙全拔光。小柏格森的顽皮和淘气,从中可见一斑。
讲座明星
1859年10月18日,柏格森出生于巴黎一个犹太音乐世家,9岁起他就在在巴黎孔多塞高级中学读书,在校10年间,他在自己所学的所有课程上都获得过奖学金。中学校长在他报考大学的推荐信上写了这样的话:“柏格森是本校最优秀的学生。”
1881年,柏格森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合格教师”证书。1897年,他担任法兰西学院讲师,3年后被聘为教授,主持“希腊罗马哲学”和“现代哲学”讲座,开始了在法兰西学院20多年的讲座生涯。他的讲演思想深邃、推理严密、言辞美妙,极受听众欢迎。以至于,每当柏格森讲课时,离开讲还有一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听课的人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等待着。其中有教授、大学生、传教士、官吏、军官、社交名媛……教室里座无虚席,甚至连讲台边、过道上、门口和窗户上都挤满了人。他讲课时,听众屏息倾听,寂然无声,犹如在教堂祈祷一般。待他讲完,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然后欣然离去。
柏格森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使他名声大振,一时间出现了“柏格森热”,他的讲演被认为是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的大事,追逐时髦的巴黎人都慕名前往听课,贵妇人们甚至把柏格森的讲堂变成了社交沙龙。
这个哲学家也是外交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僵持阶段,法国此时已经精疲力尽,迫切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在西班牙取得外交胜利的柏格森,受命于危难之间,前往美国游说。柏格森在华盛顿呆了几个月,人们认为他在促使美国参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以法国政府代表的身份与威尔逊总统进行了两夜长谈。有人对此评价道:“也许正是因为他这两夜的长谈,才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局势,有了日后的大转变。”把美国的参战归结于柏格森用语词打动了威尔逊,显然是过分夸大了柏格森的作用。不过柏格森在美国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才能确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年前,柏格森以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美国人面前,如今他以外交家的身份来招待新大陆的记者们。有一次,三个记者不约而同地叩响了柏格森的房间,柏格森正要出去从事外交活动,但又不能把堵在门口的记者赶走,于是决定来一个“闪电战”。他拿起笔对记者们说:“请各位把来意和问题全都说出来吧。”他一面倾听记者们的话语,一面奋笔疾书。当三位记者话音刚落,柏格森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面做出送客的姿态,一面向三位记者各递过去一张纸,微笑着说:“你们所问的问题,以及所要的答案,我都写在纸上了。”三位记者拿着纸片,个个都对柏格森如此敏捷的头脑敬佩不已。
就在1917年4月,美国政府抛开“中立”的面具,对德宣战。5月28日,美国的潘兴将军带领两千名士兵开赴法国。6月5日,美国34艘驱逐舰从昆斯顿出发,投入太平洋上对德国潜艇的攻击。柏格森再次为法国政府取得战争胜利立下了功劳。
连续不断的“意识流”
喜爱看电影的读者,一定很熟悉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高明的导演常常巧妙地运用这一手法把观众引向艺术意境。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曾举过一个例子,要说明两个逃跑的俘虏的长期流浪生活,只要表现不停行走的脚就行了。那些脚在不停的走动,坚实的军靴变成了破鞋,破鞋变成了碎片,包在脚上的破布化成了碎布块,最后,流着血的脚还在急速地行走。这些镜头放映不到三分钟,可是观众却以为时间过去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什么用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能使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到艺术的效果呢?因为,我们的意识是不断变化着的“流”,于是就可以在导演的暗示下,把这些镜头连成一片,接受导演传递的时间信息。柏格森认为,这种连续不断的意识活动过程就是绵延。
柏格森指出,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时间、空间与艺术欣赏者所在的时间是有距离的。比如,上面的例子中,艺术家表现的时间是长期的流浪生活,表现的空间是某个战地,而观众看这些镜头的时间不足三分钟,所在的地点是电影院。因此,柏格森说:“艺术的目的在于麻痹我们人格的活动能力,或者说是抵抗能力。”艺术家选择一些容易引起情感的表面标志,以即刻调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意识流,使其接受艺术家暗示的观念,引起和艺术家所表达的感情的共鸣。于是,“时间、空间在艺术家意识同我们意识之间所筑起的一道高墙就这样被拆去了。”他认为,绵延作为人的心理深层次的意识状态,是不易被察觉的。然而,人们的艺术审美感的获得,是同这种绵延的意识之流的作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