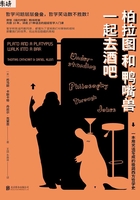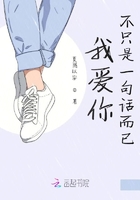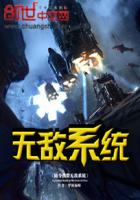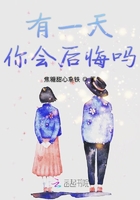弗洛姆(1900——1980)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出生于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童年的孤独和成年后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促使他要从哲学上找到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弗洛姆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爱的艺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等,他认为,自由给人类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入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
孤独的童年
1900年3月23日,弗洛姆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这是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酒商,生活在这样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家庭中,在他看来,周围环境就像是一个中世纪的世界。然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弗洛姆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理想和崇拜的对象。“我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一半是古老的,因为它具有真正犹太人的传统;一半是现代的,因为我是在德国上的学,在法兰克福,因而我又具有当时每一个德国青年所具有的东西。但是,我仍然很孤独。不仅因为受到德国人的另眼看待,还由于我所生活的那个传统古老的世界。”
弗洛姆感到孤单,主要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首先他是独子,而且父母是老来得子。他的父亲性情暴躁,只知道为了赚钱而生活,母亲则整天郁郁寡欢、情绪低落,这都让小弗洛姆感到寂寞和困扰。另外,他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商人而感到羞愧,在他看来商人只知道为赚钱而活着。于是他变得很孤独,总是期待有什么东西能将他解救出来。
在弗洛姆12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刺激很大的事情。他认识了一位25岁的姑娘,是一个漂亮又富有魅力的画家。但她订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约,却总是陪着她那位丧妻的父亲。在弗洛姆看来,她的父亲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索然寡味的老人。后来她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姑娘不久以后也自杀了,并留下遗嘱说要和父亲葬在一起。这个消息极大地震惊了弗洛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俄狄普斯情结,也没有听说过女儿和父亲之间的乱伦之恋,但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弗洛姆在大学一接触到弗洛伊德的学说,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想从中找到解决自己困惑的途径。
战争与成就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弗洛姆年仅14岁。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萌发了很多的问题,战争使他感到疑惑和苦恼,促使他思考人类行为的根源,于是他走上了探索人性和社会生活规律的道路。弗洛姆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别的任何事件决定了我的成长道路。”在他后来的学习中,更进一步看到了社会历史环境和发展对个人人格形成、个人行为的深刻影响。由于社会文化力量的重要,那么就应该去分析这个社会的结构,从而理解社会中的人格结构。
1929年,弗洛姆回到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并从事心理治疗,他一生的研究工作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指导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兰克福学派是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派,其宗旨就是以人道主义、人性论为基础。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对当代工业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弗洛姆正是在这一学派的影响下,开始关注群体的命运和宏观的社会趋势。他把性格分为两个部分:“社会性格”和“个人性格”。“社会性格”是性格结构中的核心,为同一文化群体中一切成员所共有。“个人性格”是同一文化群体中各个成员之间行为的差异。在他看来,性格是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影响而形成的,而一旦形成了性格特性,又会推动社会进程。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小店主,他有强烈的积蓄冲动,并且憎恨浪费,而对于他来说,想生存就必须节俭,那么这种冲动对他就大有帮助,这便是性格的经济功能。此外,有积蓄欲的人是其性格使然,如果他能按自己的欲望积蓄,他还会在心里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这就是性格的主观功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的性格,即社会性格,转化为个人在社会中必须履行的客观职责,人的精力就会变成生产力,成为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实,这是弗洛姆提出的对理想社会的要求,即一旦某些需求在性格结构中发展起来,所有与这些需求一致的行为既能使人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又能使人在物质上成功获得实际利益。只要一个社会能够同时满足个人的这两种需求,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心理力量会黏合社会结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弗洛姆,着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和批判当代工业社会的各种现象。在这方面,弗洛姆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曾一度是弗洛伊德的粉丝,然而却并不完全赞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本能学说”,他不否认人性的历史性,但却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此外,弗洛姆还深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张扬始终是马克思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弗洛姆曾经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与弗洛伊德不同,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是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即劳动入手的。如果说在对人性及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弗洛姆是融合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话,那么在社会批判方面,弗洛姆则更多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
1934年弗洛姆为了逃避纳粹的的迫害,定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他到美国后,先后在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在弗洛姆执教和研究过程中,他慢慢将自己的思想融入自己的人格理论中,他将性格划分为两大类:生产的倾向性和非生产的倾向性。前者是健康的性格而后者是不健康的、病态的性格。生产的倾向性就是弗洛姆心中的理想人格。生产性的人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理想境界和目标。
非生产的倾向性可划分为四个类型:
接受倾向性这种人没有生产和提供爱的能力,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完全依赖别人,是被动的接受者。
剥削倾向性这种人并非依赖自己进行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从他人那里索取东西,对他人进行攻击或榨取,喜欢利用人。
贮藏倾向性这种人通过贮藏而获得安全感,他们的哲学是“资产和财富就是安全”,他们与人疏远,人际关系表现为退缩。
市场倾向性这种人在各个方面表现为随雇主的需要而变化的性格特征,弗洛姆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有丧失个人独特性而变成纯粹机器人的危险。
以上四种非生产的倾向性性格只是“理想类型”,而不是对某一特定个体性格的描述,即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弗洛姆认为,非生产性人格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增加生产性人格的因素。
弗洛姆心目中理想的生产性人格,是一种重于给予和奉献的人格特征。而他倡导的是将每一个个体的性格培养为与社会性格相一致,如此能够让个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进程。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弗洛姆提出了他格外重视的社会因素和手段,那就是教育。弗洛姆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在于使个人具备将来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特性,就是把个人的性格塑造得与社会性格相近,使个人的欲望与其社会角色的必然欲求相一致。所有社会的教育制度都决定于这种功能。
毒蛇的小屋
在美国,曾经有几个学生向弗洛姆请教:心态对一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弗洛姆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就把他们带进一间黑暗的房间。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很快就穿过了这间伸手不见五指的神秘屋子。接着弗洛姆打开了屋子里的灯,此时,学生们才看清楚屋子里的布置,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间屋子的下面是一个很大很深的池子,里面蠕动着各种毒蛇,包括一条大蟒蛇和三条眼镜蛇,有好几条毒蛇正高高地昂着头,朝他们“嗞嗞”地吐着信子。就在这蛇池的上方搭着一座很窄的木桥,他们刚才就是从这木桥上走过来的。
弗洛姆看着他们问:“现在你们还愿意再次走过这座桥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过了片刻,终于有三个学生犹犹豫豫地站出来了。其中一个学生一上去,就异常小心地挪动着双脚,速度比第一次慢了好多倍;另一个学生则战战兢兢地踩在小木桥上,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才走到一半就挺不住了;第三个学生干脆弯下身来,慢慢爬在小桥上爬过去了。
弗洛姆笑了:“我可以解答你们的疑问了,这座桥本来并不难走,可是桥下的毒蛇对你们造成了心理威慑,于是你们失去了平静的心态,乱了方寸,慌了手脚,表现出各种程度的胆怯——心态对行为当然是有影响的。”
梦是无需翻译的
弗洛姆对弗洛伊德释梦的著作相当的熟悉,他在美国芝加哥分析学院工作期间,他的一个助手塔木德对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问题很感兴趣。
有一天,塔木德到弗洛姆的工作室去见他。
“弗洛姆教授,我昨天接待了一个年轻的妇女,她对我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梦。”塔木德说。
“她做了一个什么梦?”弗洛姆显得也很感兴趣。
“她说在梦中,她挽着她丈夫的手在门口散步,看见一辆马车刚好停在她家门口。突然,马车开了,两个警察从马车里跳了出来,径直向她们走来。当警察走到她面前,向她出示了他们的证件和拘捕证。她还没有发问,警察就把她推向那辆马车。那时,她要求和丈夫说几句话,交代一些事情再去警局,可是那两个警察不同意……到了警局,他们指控她犯了‘杀婴罪’,怀疑她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她听到这个指控后非常生气,向警察高声喊叫,于是就醒了。”塔木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个女人的梦。
“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梦。”弗洛姆点点头说。
“后来,她问我这个梦是否预示着一些什么?”
“那你是怎么对她解释的呢?”弗洛姆问塔木德。
“我问她‘你希望被警察拘捕吗?’她回答说不希望,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愿意自己去找那些麻烦呢?”塔木德露出非常疑惑的表情说。“那你有没有问她,为什么警察要指控她犯有‘杀婴罪’呢?”弗洛姆问。
“我问她了,她说‘怎么可以想象我会自己杀死自己的儿子呢?’我对这个问题也不明白,所以过来请教你。”
“这个梦是不需要解释的。”弗洛姆说。
“可是,弗洛伊德不是说,所有的梦都是表达了做梦者的一种愿望吗?”塔木德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
“我觉得,弗洛伊德的这个原则可以解决许多做梦者的问题,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做梦者产生梦的原因。”弗洛姆虽然对弗洛伊德很崇敬,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会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
“弗洛伊德说‘一个没有翻译的梦就像是一封没有拆开的信’,那个妇女的梦究竟应该怎么翻译呢?”塔木德问。
“弗洛伊德用翻译这两个字眼,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准确,梦不需要翻译。梦语有自己的语法和形式,它不可能和现实世界的词语完全一一对应。”弗洛姆显然对弗洛伊德的“翻译说”存有异议。
“那你认为这女人的梦是不需要解释的了?”塔木德问。“
是这样的,梦不是描述一种事实,而是传递一种感觉。或许梦中的感觉比清醒时更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