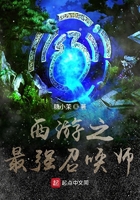不同地方的医院可能千差万别,但是每进一个医院要排的队都是大同小异的。父亲在贵阳等到了我,坐了两天的火车后,我耳朵背后的包块向下移动了不少,并出现了红肿症状。
因为当天到贵阳时已经是晚上,我和父亲在贵医旁边寻找住处。父亲经常受人之托带病人来到此地,所以他很熟悉环境,很快带我进了一家小旅馆。小旅馆老板报了价后,父亲说:“你家这里我经常来,我知道行情,就三十块钱两个单间,经常住的。”
小旅馆的老板有些无奈地点点头说:“也就是你经常来的才开给你,其他人这个价格是肯定住不了,既然是老客户,就跟我来吧。”
父亲付了钱,我们跟在老板后面上了楼,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最小的房间。小旅馆的每个“单间”都是隔出来的,房间之间是一层薄薄的三合板,把一个普通房间隔成四个房间,然后支起一米宽的木板作为床,放上泛黄的棉被作为座位铺盖,就成了一个单间。
在房间中除了躺下后能有足够的空间,其他任何动作都会让房间显得局促。当你床上躺下,各种汗味和脚臭味能让人一直头脑恍惚,混杂鼾声说话声又能让人头脑清醒,父亲经常出入这种地方,我很难理解他是如何适应的。小旅馆并不大,但是人却不少,整晚上都能听见人声嘈杂。没有窗子,但是听见穿墙而来的叫喊声,隔着墙也能猜到隔壁个娱乐会所。
生命没有高低之分,但是生命却只以高低的形式来表现。
父亲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个伟大的形象,他慷慨智慧、坚韧负责、急人之所急,只要有他出马,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他的庇护下生活成长。相比和朋友的侃侃而谈,此刻的父亲,在面对生活成本时却显得太过小心翼翼,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也许是外面的喧闹,或许是心绪的繁杂,又或许是脖子上板块的疼痛,我一夜未睡,只是在黎明之前恍恍惚惚眯了一下就被父亲叫醒。父亲说:“趁早我们得去排队,不然怕今天得不到检查。”
路边的小摊总是比任何人都早。我们出了小旅馆,路边有个小摊卖油条豆浆。父亲问我要吃几根油条,我肚子早就饿了,但是看着父亲渺小,我莫名其妙的生气,我说:“我不吃!”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他平静地说:“早上要吃点东西,也不知道我们要多久才能检查,不吃挨不住。”我用沉默代替了语言。父亲买了四根油条,给我两根,但是我生着闷气走在前面。
天还没亮,我原本以为会很快就会挂号就诊,但是走进挂号大厅,我才发现里面人山人海,每一个挂号窗口都有几十个人在排队。父亲对我说:“你先找个地方坐着吃东西,我去排队。”
我没有说话,而是径直走到队伍后面排队,父亲见了也不再说话,他知道我脾气犟,只是走到一边把油条都吃完。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很反感,不知道从何而来又对之无可奈何,我尽力要将之抛之脑后,却又难免在表情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成功挂号后,排队看病,医生在我的包块上压了压,然后开单,说:“先去缴费,做完检查之后把结果拿回来我看。”我看了看单据,要抽血化验和做B超检查。问了采血室个彩超室的去处,我穿插在人群之中,换了一个又一个科室,终于釆了血,但医生说要下午四点才能拿到结果。当我去到彩超室正准备排队时,旁边的护士直接说:“先做个登记,今天检查的人已经排满了,要等到明天才能做,你明天早上八点直接来做检查,不用排队。”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过,原本还期望今天就能拿到检查结果,没想到连检查都做不完,我心情更加郁闷。父亲一直跟在我的身后,除了问给我做检查的医生一些问题,其他没说一句话。在知道明天才能检查后,父亲说:“先吃饭,然后等明天再来检查,也不急在一时。”我和父亲出了医院,在旁边随便炒了个饭,坐在路边吃起来。
在吃过饭后,我把心里酝酿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我对父亲说:“爸,要不你先回去吧,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拿到结果,就算拿到了结果,也不知道还要做什么检查,你先回家,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免得两个人干等。”父亲说:“先看看结果再说,结果都还没有出来,万一要做手术,你一个人怎么办?”我坚持说:“就算要做手术肯定也要等好几天,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在上海时做B超都不用排队,做手术都要等一个星期,那在这里做手术肯定也要等。”
父亲面露不快,他邹着眉头说:“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方便,我来都来了,最起码得看到一个结果,要手术也好,要做其他的也好,有人和你好照应。”我说:“我这边有几个同学在的,临时有需要我也可以找他们,我晚上去和他们住,也可以省点钱。”父亲不快说:“能花多少钱!”我又坚持说了几句,不得不和父亲冷战起来,父亲知道我脾气犟,最后终于松口,说:“那等下午把釆血的结果拿了,我看看再走。”
下午我拿到了血常规结果,父亲看了说没有异常,我心里也松了口气,便说:“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过段时间都会自己好了。”父亲说:“还是要以检查结果为准。”我顺势说:“你先回家去,等我有什么结果再打电话给你,应该不用做手术。”父亲沉默了一会,说:“那行,不管什么结果都往家里打个电话。”
临走前父亲又叮嘱了一些话,我送父亲上了火车,便去了小壶的住处。小壶来到贵阳已经四个月,他和他的哥哥住在一起,他哥哥给他找了一个公司,他在公司从学徒做起,每个月就只拿一点基本的生活费。好在住在他哥哥的地方,每个月为他省了不少房租。说起工资,小壶说:“惨得很,天天上班,却连上网的钱都没有,要不是房子是我哥租的,房租交了几年,我现在连房子都租不起,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虽说房子是小壶的哥哥租的,但是他哥哥在外地做业务,已经在广州定居,一年到头都难得回来一次。小壶也因为哥哥的人脉,在贵阳落了脚。
小壶请我吃了个火锅,我知道他的情况,告诉他没有必要破费,随便吃点就行,他说:“来到这里,就算我这个月最后几天饿肚子,也不能不请你吃一顿,如果我去到上海,难到你会让我随便吃碗粉吃碗炒饭吗?”他还是一样的耿直,一样的心直口快。
我们像在高中时一样,两人挤在一张床上,谈天说地,彻夜难眠,相互诉说着分别的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还有各自的遭遇和对生活对社会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