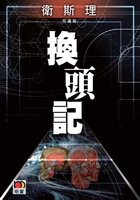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死老头儿!您就别追我了!”声音由远及近,有些沙哑。
一名身穿白衫的少年,边跑边回头喊。白衫不白,应该是许久没换洗,已经脏兮兮的,似乎蒙了一层灰。白衫变成了灰衫。
少年约莫十五六岁,五官棱角清晰,颧骨分明。尤其是眼睛,炯炯有神。
跟在少年后面追的,是一位穿黑色长衫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棒,边跑边呻吟,气喘吁吁。男子身型消瘦,似乎一阵风都能吹倒。
“死老头!求您了!别再追了,成么?您说您跑也跑不赢我,再跑您这身子骨都要散架了!”
少年满头大汗,哈着气,仍断断续续,不停说话。
集市喧闹,车水马龙。这里是清河镇,清河镇位居洛宁国东南。镇虽小,但商贾较多,大户人家随处可见。当然,贩夫走卒,地痞混混三教九流的人,也确实不少。
黑长衫中年男子被人群挤了几次,差点摔倒,一把扶住路边的豆腐摊贩,直摇头,叹气道:“孽种啊!我赵老四这辈子是造的什么孽!有你这么一个孽种儿子!”
少年回头见男子没追,便停下擦头上的汗,大口喘气。
他确定中年男子是不会再追过来,便缓缓扒开人群,一脸怪相,凑到男子身边。
“好,我叫你声爹,您说您这是何苦呢?”少年捏紧男子手里的木棒,嬉皮笑脸地说。
赵老四长叹气,道:“活祖宗,你这是要把你爹给气死啊。”说着说着,便大声咳嗽。
少年赶紧轻轻拍赵老四的背,低下头,笑着说:“看吧!您说您都一大把年纪了,非逼着我去念书做什么呢?学堂里的事,你根本不知道。我回家跟着您卖豆腐,不是很好么。”
“学堂里什么事?”赵老四盯着儿子问。
少年吊儿郎当地说:“说了你也不知道。”
“你!”赵老四原本被少年拍打几下后,咳嗽已经停了,但听到这句话后,又剧烈咳嗽起来。终于是没忍住,气没缓过来,一头栽倒在地上。
少年没见过这阵仗,连忙拍打着赵老师的脸,又是掐人中,又是大喊。
过了好大一会儿,赵老四才缓过来。人群中有好事者,议论纷纷。
“现在的年轻人啊,真不是不孝顺。”
“看这人长得仪表堂堂,谁知道也是个败家子。”
“哎!家门不幸!爹都差点气死了。”
这些话,少年听得清清楚楚,他恶狠狠地盯了一眼这些围观者。“你们懂个屁!肉食者鄙!”
“哟呵!他骂我们懂个屁!”人群中有个胖子,一把推开面前的其他人,吆喝起来。
少年一手扶着赵老四,一手拿着木棒,道:“就说你们,怎么着?”
胖子上前几步,伸手拦住少年。“你有种再敢骂一句试试?”
少年仔细瞄了一下眼前这个胖子,心想:此人牛高马大,要是单挑,我肯定不占优势。更何况,周围还有这么多人,万一打起来,我岂不是被打成肉饼。
“怂了吧?小子!”胖子笑嘻嘻地。他一把抓住少年手里的木棒,说:“这样,我不跟你计较了。你乖乖叫声爷爷,我就饶了你!要么,就从这里钻过去!”
少年怒目圆睁,见他指着自己的胯下,恨不得一巴掌拍死眼前这个胖子。但自己身单力薄,打肯定打不过,走肯定也走不了。
“快叫爷爷!”人群中有人先带头吼了起来。
“你叫不叫?不叫就从我胯下钻过去!”胖子一把扯掉木棒,正准备动手。
“慢着!你急什么?”少年故作沉思状,挠着耳朵,斜视着胖子,眼珠子滴溜溜转,道:“这样,你看我爹都晕了,一会怕是没命了。人命关天,等我把我爹送回去,我们约个地方再比试一下,单挑你一人。打不赢你,悉听尊便。”
胖子哈哈大笑,笑完一脸鄙夷,说:“没那么容易!你小子想跑,当我傻大个么?”
胖子说完,一只大掌,捏住少年的手腕。
少年顿时觉得一阵酸胀疼,连忙“啊”地一声,马上求饶:“好了!好了!你厉害,大哥,不,爷爷,你狠!”
胖子一脸凶相,又说:“算你小子识相。”
“爷你个熊!”胖子刚一松手,少年低声又骂了一句,骂完赶紧嬉皮笑脸,说:“那我们可以走了?”
胖子哈哈大笑,说:“孙子!今天看在你叫爷爷的份上,放你一马。三天后河边小树林,咱们单挑。你不来的话,我烧了你家豆腐铺。我可是知道你家在哪里的。”
少年拄着木棒,架着赵老四,慢悠悠地往回走。
手腕上一阵酸疼。每痛一下,他都想把胖子拿来碎尸万段。他一脸严肃,朝路边狠狠地啐了一口痰,厉声说道:“娘的!老子一定要把胖子教训一顿!”
**********************
镇尾,靠山一处农家院子。
厨房传出饭香味。一位红衣妇人正在灶台前忙着做饭。锅里是红烧豆腐。
“晚霞,我回来了!”少年架着赵老四走进院子便喊。他将赵老四扶到院子的石凳上坐着,赵老四没坐稳,一下子扑倒在石桌上。
少年也不管,扔掉木棒,径直朝着厨房走去。
“这孩子!没大没小,晚霞是你叫的?你喊一声‘娘’要死么?”红衣妇人从厨房出来,差点撞上少年,嗔怒着说:“山河,快洗手,准备吃饭。你爹回来没?”
少年叫赵山河。从小到大,他都是将红衣妇人喊作“晚霞”。妇人是赵老四的老婆,全名陈晚霞。
陈晚霞见赵老四趴在院子石桌上,指着赵山河问:“你爹怎么回事?是不是又被你气晕了?”
赵山河有些无奈,嬉皮笑脸地说:“晚霞,你说我爹这个死老头子,为啥非要我去念书,念书有啥用?他又不知道学堂怎么回事。我在学堂吃喝piao赌,就piao没干过,浪费他的钱,他也不知道。哎,大街上那样追我,我还要不要在清河镇混下去了嘛!”
陈晚霞不搭理他,拿来一根竹条,狠狠抽了赵老四的臀部。
赵老四忽地站起来,“嗷”地一声:“谁打我!”他看见陈晚霞手里的竹条,又低声说:“老婆,你这是······!”说完赶紧起来,一溜烟钻进厨房,不一会,饭菜全端出来了。
赵老四以前也经常被赵山河气晕。一生气,气没顺就晕了,歇息一会又好了。
“真是怕老婆!我今后成家了,一定不能当个怕老婆的男人。”赵山河想到这里,嘿嘿笑起来。
赵山河随时提防着赵老四要出招,吃饭时只好屁股半坐着石凳,便于迅速起身逃跑。
赵老四往嘴里扒几口饭,便往陈晚霞碗里夹菜,嘿嘿说道:“老婆,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山河念书的事?”陈晚霞说。
赵老四唯唯诺诺,说:“是的。他一定要去念书,否则我们没法交差。”
“没法交差?”赵山河插话,“我念书,你们需要给谁交差?”
陈晚霞不作声。赵老四瞪了他一眼,道:“回头我送你回学堂。”
“死老头子,你不说给谁交差,我是不会去的!”赵山河端着饭碗,站起来嘀咕道。他担心赵老四突然起身“出招”——比如一只筷子朝他的头敲来!
这么十几年,赵老四经常这样,出其不意地向他“出招”。做豆腐时,随时扔过来一把黄豆;吃饭时突然一筷子敲过来;一起并排时,随时可能一脚横过来······
刚开始,他没警惕性,经常不是被打得鼻青脸肿,就是晕头转向。后来他习惯了,面对任何人,都有些警惕心理,随时提防对方“出招”。甚至有时候会设圈套,搞些恶作剧。
自此,赵老四自然是没少吃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