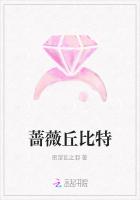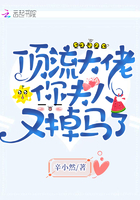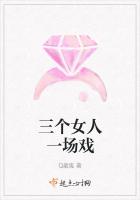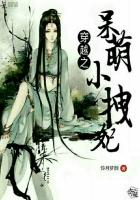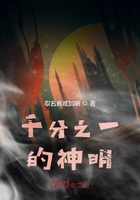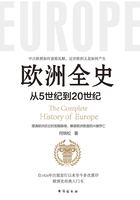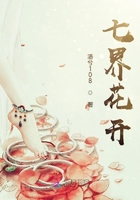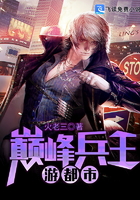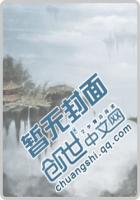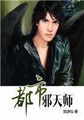景莘莘再次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她躺在堂屋熟悉又陌生的大铁床上,盯着门外从东侧锅屋里漏出来的微弱的火光。
这里是鲁东省的农村,锅屋是这里厨房的方言叫法。
她借着门口仅有的微光,慢慢从床上爬下来,因为太小,铁床又高,差点摔她一个屁股墩儿。
踉跄一下赶紧扶着床沿站稳,她差点忘了自己现在还不满两岁,走路都不稳当,就这样爬下来没摔着算好的了。
天寒地冻的冬夜,屋里连那种最老式的瓦数很低的灯泡都没开,其他保暖的设施就更没有了。
之前宋玉兰怕景莘莘冻着,只把外面套棉衣的罩衣罩裤脱下就把她塞进被窝里。所以,此时景莘莘身上还裹着之前那身用大红花布包着棉花做的连体棉衣,身上并不怎么冷。
只是一双小脚上仅套着一双破了洞且明显肥大的棉袜站在红砖铺就的地面上,刺骨的寒意自脚底直窜脑门,把景莘莘冻的直哆嗦。
扶着床沿在原地跺了两下脚,她习惯性的扯着嗓子,奶声奶气地喊了声:“妈妈~”
接着锅屋里就传来动静,一个小小的黑影进了堂屋,摸索着来到景莘莘身边,扶着床头的铁架踮起脚尖,凭空挥了两下就扯到一根绳子,轻轻往下一拉,“啪”的一声很细小的声音响起,接着原本漆黑的屋子便染上了微弱的橘黄。
“妈~阿莘从床上下来了!”
景莘莘还没来得及适应这微弱的灯光,就被来人踉踉跄跄的勒到锅屋。
谁让对方也还是个孩子,同样都穿着笨重棉衣,根本就抱不动本就有些胖的景莘莘。
黄泥土墙茅草棚,红砖矮灶大铁锅。几乎堆到屋顶的杂草和柴火,坐在矮灶前烧火煮饭的妇人。
这是这个时代农家人最常见的一幕。
宋玉兰正拿着一双鞋底被磨得光滑的红色小棉鞋放在灶前烤着,见景薇薇费力的勒着景莘莘过来,抬起左手一把将她捞到自己的大腿上坐正,借着灶里烧的通红的火光,轻轻抬起景莘莘的下巴,仔细看着她摔的发紫且红肿的嘴巴。
“嘶……疼!”
景莘莘本想张口说话,结果忘记自己嘴上有伤,一时大意扯到了伤口,疼的她泪眼汪汪。
“不疼不疼!姐姐给呼呼就不疼了,乖啊~”不等宋玉兰出声安慰,一旁才八岁的景薇薇就已经凑过来对着景莘莘的伤口轻轻吹气了。
一丝清清凉凉的风拂过,痛意果真减轻了许多。
这时宋玉兰已经为景莘莘穿好被火烤的暖烘烘的棉鞋:“阿莘,跟姐姐去堂屋,妈妈盛饭。”
景莘莘闻言乖巧的抓着姐姐景薇薇的手,慢慢地走回堂屋。
这个时候的农村没那么多讲究,景莘莘家里也就四间房的宅基地,盖上两间大瓦房,东边堂屋放上当下买得起用得上的家具:也就一大一小两张床东西横放靠着北墙,中间放一张大号的大八仙桌隔开,大八仙桌上放了宋玉兰的嫁妆——两个放衣服的大柜子,大床靠东墙的床头再放一张写字台,靠着东南角立着一个盛放碗筷吃食的菜橱,而堂屋进门就靠西墙放着一张小八仙桌,即餐桌。
景莘莘端正的坐在桌前的小板凳上,紧紧的盯着泛黄的墙上挂着早已撕了大半的日历。
阳历1983年12月8日。
农历癸亥猪年,冬月初五,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