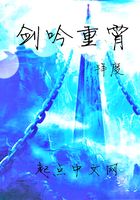谭莱说道:“这个你不用担心,地我都选好了,而且我也认识起地产做生意的人,有政府关系、有工程队,就系需要本金而已。”张鹤仁爽快地道:“要多少钱你就讲个数目,我比你就是了。”谭莱点点头,然后讲道:“我勘研了很久,选中了在北角一块地,而且有位漳州籍的朋友,看中北角多福建人、鹤佬,有意在北角发展地产。他很有兴趣同鹤仁哥你合作。鹤仁哥,你想想,起楼做地产这生意以后一定大发财,总好过一辈子卖毒品呀。说不定这个就是你的转机!”
张鹤仁听得深以为然,还是有些不放心:“讲到这里你不过就是需要钱而已,香港地有钱的比我多的是,为何单单要找我?”
谭莱到这里神情有些怪,低声道:“除了地和那高楼,要奉请神道上驾,在起这地基时候还必须要一样东西。无了这东西,其他都是白费,那神道上驾是留不住的。”
张鹤仁“哦”了一声,大感好奇,问:“是什么东西,要靠我去办?”谭莱说道:“正是,这方正地基必须‘打生桩’!”
“打生桩,这是什么意思?”我忍不住插口打断。
佳叔双眼精光闪动,沉声讲道:“以前迷信,凡动土起楼,必然冲动地灵或地煞,须以活人牲祭,做为地桩打入方可动工。如此就能保土木顺利,家宅平安。”
“我顶你个肺,这么残忍?”我听完不寒而栗。
张鹤仁虽然以前在乡下听过,但此刻听到谭莱这样说,任他在江湖上闯荡多年都有些胆怯:“真的非要生桩不可?”
谭莱讲道:“非此不可,而且是成事关键,那生桩还有讲究,要四个童男,两个完璧少女,如此纯阳纯阴之体,方可济事。那童男要在十岁以下,那纯阴女体要在十五岁以上。”张鹤仁心里暗自骂道:‘浦你阿摩’还要这么麻烦。口上讲道:“你叫我哪里去找呀,这可不是随便的事情。”谭莱笑着说:“当然了,这种不见得光的事,自然就要请鹤仁哥你来办了。以你在道上的的势力,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呀。”
佳叔点点头,说道:“你‘塘边鹤’当时风头正盛,手下众多,做这件阴鸷事确实不难呀。最后那几个生桩就被你弄来了?”
张鹤仁脸上一阵红,一阵青,再无那文雅儒正的风度,不知是点头好还是摇头,最后长叹一声:“系我该死,也不怕有报应,一时迷窍昏心,居然信了那姓谭的话,帮他捉来了生桩。”
我问佳叔:“究竟是什么邪恶神道,要用这‘生桩’的残忍手段来供奉。”佳叔话:“神道本无善恶,招引的人心性邪恶、用在坏处,那神道就是邪恶。若是就这样将生桩打下去,虽然是残忍阴毒,但也不会搞到这位张生现在这样,那谭莱有问题。在打生桩的时候他一定做了其他手脚。”
旧时民智未开,民间有风水迷信认为,凡兴土木、起楼必定冲撞地神阴灵,须以童子之身活埋做地基以为人牲献祭,方能安抚有司神灵精怪,务求土木工程顺顺利利,不然就会意外频频,导致不能完工,可能会令到参与的工人有人命毁伤,甚至会有害主人家宅。
十分讽刺的是,当年的张鹤仁听信那个印尼华侨谭莱所言,为了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无须再做毒品损阴德的生意,去堂堂正正做个正当商人,却泯灭天良真的指使手下去偷拐了四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又用钱财利诱拐骗了两个十六、七岁的离家出走的无知少女。
再将这四个“人桩”交予了谭莱,由他处置。谭莱跟张鹤仁讲到:得了这少阴、少阳的‘生桩’,在合适的时辰打落选在北角的这块地皮之下,再配以暗合五行风玄之数来的起的大楼,不但可以使张鹤仁的大劫化去,从此他更可以如鱼得水,在地产发展这方面“猪笼入水”,堂而皇之做个上流生意人。
我问张鹤仁:“你当年就无想到那个什么谭莱有这么好人。请的这个神灵来安在那地皮之下,总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你呀?”
张鹤仁叹气道:“当时我是迷窍昏心,只想转运破劫,也是因为我做毒品亏心,所以对这请神化劫深信不疑。那谭莱说话总像有种魔力,教人打心底就相信他。”
到了那晚上进行仪式,张鹤仁吩咐心腹手下在四周严密戒备,他自是知道事关重大。虽然那个年代什么为非作歹的肮脏事情都有,但若让外人发现他们在“打生桩”,那是非同小可,搞不好自己要蹲大牢,得不偿失。
佳叔听到这里十分留意,问:“那个谭莱先生是怎么处置几个男童和少女?”张鹤仁回答:“那些‘生桩’抬到来工地的时候,全部都裹了白布,脸面也看不到,一动不动,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或者是被谭莱迷昏了不一定。”他语气平淡,讲起这几个无辜男童、少女时,好似就是在提起几件物件一般。佳叔又问:“白布上可有画着什么图案或纹样?”
毕竟过了几十年,张鹤仁也是一把年纪了,努力地回想了好一会儿,兀然说到:“我记起了,那个白布上好像画着只麒麟!”
佳叔“哦”了一声,十分感兴趣:“是不是有青黑颜色相杂,左右各一只?”
张鹤仁仿佛瞬间被佳叔打开了回忆的盒子,悚然道:“对,对!佳叔你当时就在现场看到?”
佳叔没有理会他,摇头道:“这白布上画的图案不是麒麟,你再想清楚一点!”张鹤仁闭上眼再努力地回想,灵光一现:“不错,头像龙没有长角,身子像老虎狮子那样的猛兽,四足利爪,没有尾巴,看起来很是凶猛。青头黑身,很是怪异,我以前从未见过。当时有问过谭莱,他说是麒麟,是仁兽可以祈福,减去‘生桩’的怨气。”
佳叔听到这里倒吸一口凉气,用手揉揉太阳穴,我连忙问他有无事。佳叔想了好一会,又摇头:“不可能呀,不可能是那个人。”
我奇怪问道:“佳叔,你说的哪个人?你怎么好像这么清楚当晚的情形?”佳叔说:“这个谭莱所用白布裹着‘生桩’,上面还画着各一对兽像,根本不是民间迷信‘打生桩’会做的仪式。那对画在布上有点像麒麟的野兽,好像有个名堂叫‘玄青龙狮’。”
“我所知有一派请神道宗,召请的所谓神灵,与正神瑞兽背道而驰。本来麒麟是仁兽,但这‘玄青龙狮’虽然看似麒麟,但乃是阴极至寒,若然召请之人本性不良,为人奸毒,那这龙狮所发挥的神力也会变得十分阴邪。”
张鹤仁颤抖着声音说道:“佳叔,谭莱请的这个什么玄青龙狮,真的能帮我化劫吗?这么多年我确实风生水起,做地产开发由香港做到深圳,无事不顺。地皮说买就买到,什么工程都毫无阻碍。”
我冷笑道:“你就顺风顺水这么多年了,那几个无辜男童和少女就被活活打在地基下面,你晚上做梦不会吓醒吗?”
张鹤仁立即就像被雷劈了一样,道:“这么多年来我都以为已经将这件事忘掉,直到两个月前腿上现出这两个人头印,实在是匪夷所思。搞到我吃不安睡不宁,就想起当年这件亏心事。”说完就跪在佳叔面前不停扣头:“佳叔大发慈悲救命呀!”
我说道:“你现在不过是腿上出现两个人头印而已,虽然有点可怕但你不还是大活人一个站在这里,也不见得会危及你性命呀。”
张鹤仁摇头,道:“我担心的不止是我的性命,而是我家里人。从两个月前开始我的家人已经开始变得古怪。我疑心就是和当年种生桩请了这‘玄青龙狮’的缘故。”
佳叔问他道:“你家里有什么人?”张鹤仁自然老实回答道:“有我太太,两个儿子一个小女儿。儿子都已经结婚,有儿媳妇和五个孙子、孙女。”我是越听越气:“你这丧尽天良的地产奸商居然还家庭幸福,儿孙满堂一大家人,又赚这么多钱,真是无天理。”
佳叔好像未卜先知:“你说的古怪是不是家里人开始吃起泥土了?”张鹤仁听到,望着佳叔如看到神佛一般,声音发抖:“有好几晚半夜我就发现,我太太和跟我住在一起的女儿,夜半三更一起在客厅饭桌上吃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泥土,两人面色像僵尸一般,无论我怎么叫她们就没有一个理睬我,都像是中了邪一样。直吃到满口污泥,才回到床上。但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像没事发生过,洗漱完了就恢复正常。”
我想象着张鹤仁半夜惊醒,看到太太与女儿如木偶一般围坐在餐桌上在吃泥,那确实是容易把人吓尿。
玄青龙狮这派请神法道,确实是以地为本,一旦将神灵法相安奉在其下,能将方圆周遭生灵精气汇聚为行法召请者所用,但是未听过龙狮法相需用“生桩”做人牲祭奉。
那个叫谭莱的家伙用了几个可怜的男童、少女埋在地基,并不是作为生桩的用途,而是被他做了手脚,变作了“阴身”,吸收龙狮法相所取的生灵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