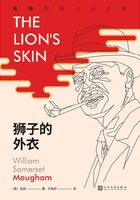“您看……那桌子上又是珍珠,又是珊瑚的,多晃眼啊。要是缺一件、少一件,我怕说不清楚。”
“瞧你说的,把自己当成什么啦?这些七零八碎的玩意儿,没什么好稀罕的。”德吉说着起身,这时她才认真地端详娜珍,见她一身简朴,于是说:“你这身上也太素净了,来来……”她伸手把娜珍拉了过来,抓过桌子上的一副玉镯,套在她的手腕上。
“少奶奶,这……这可使不得。”娜珍推辞说。
“你这小手腕跟白瓷碗似的,正配这镯子。喜欢吗?”
“喜欢,少奶奶,这得值多少钱啊?”
“可能值十头牦牛,也可能一钱不值。那得看戴在谁手上。”
娜珍装听不懂,自顾自地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德吉看着她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得意。
娜珍凑近镜子,亮出手腕看着,扭头说道:“少奶奶,太谢谢您了,这可真漂亮。”
“这些东西你要是喜欢,看着拣几样吧。”
“真的?”娜珍情不自禁地拿起一串红珊瑚项链,一边往脖子上比画,一边说:“我从来没戴过,他也从来没送过我,真好看。”
德吉一听“他”,有些反感,她说道:“好看,就拿走吧。”说罢,她起身走了。
女仆不屑地冲娜珍撇了撇嘴,也跟着出去了。
德吉面无表情地走在走廊里,女仆跟在后面,嘟囔:“少奶奶,这个女人真不自量力,那么贵重的东西她也敢要。”
德吉继续在前面走着,没言语。
“您要依着她,她非得寸进尺不可……”
“你说什么呢?”德吉训斥。
女仆低下头,不言语了。
“当主子,就得有当主子的样儿。既然进了德勒府,她也是二少奶奶,对她,你们今后要放尊重点儿!你看她穿得那么寒碜,丢的是我们德勒府的脸。你明天去八廓街的店铺上给她取些穿的用的,挑好的拿。听说那家北京商店,新进了一批杭州丝绸,你去看看,扯几块回来,给她做几套像样的衣服。”
“啦嗦。”女仆应承着。
白玛的伤好了许多,他坐在房间的卡垫上读着经书,娜珍从外面进来,身上挂着几件珠宝。她把珠宝从身上摘下来,放在桌子上。
白玛看了一眼,不快地问:“哪来的?”
“少奶奶赏的,她戴旧的破烂东西。”娜珍说。
“阿妈,你过去一心向佛,不染世俗之气,现在是怎么啦?”
“你想说什么?觉得阿妈活得没点儿骨气?贪图浮华?”
白玛瞥了她一眼,不再言语,眼睛又回到了经书上。
娜珍望着儿子,心绪难平。白玛不谙世事,单纯幼稚,这让她忧虑不安。她现在还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自己的儿子,你比德吉更有资格拥有德勒府的财富、爵位、荣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我要帮你夺回这一切!
她随手把几样珠宝抓起来,摔到地上。白玛惊讶地抬头望着娜珍,很是不解。娜珍狠狠地说:“这几个镯子、项链算什么,根本就不入我的眼!”
夜深了,外面下起了大雨,雷鸣电闪的。女仆侍候德吉上床躺下后,退出房去。扎西宽衣解带,准备上床,他伸头看了看假寐的德吉,逗她说:“睡着啦?我知道你没睡。”他见德吉不理自己,于是用手捅她说:“你装,你再装。”他又故意在德吉耳边打呼噜。
德吉笑了,推开他说:“讨厌,跟野驴叫似的,难听死了。”
扎西上床搂德吉,德吉扭捏地说:“让下人看见。”
“看就看见呗。噢,你是贵族,要注意身份。哎哟,我怎么摸上少奶奶的床了,这可是犯上啊,要剁掉手脚的,我还是外边睡去吧。”扎西说着要走。
德吉终于忍不住,扑到他怀里,撒娇:“你又念经,絮絮叨叨的。少奶奶怎么啦,少奶奶也是人,也得睡觉,让贵族见鬼去吧。”
两个人亲昵地相拥在一起,忽然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谁在外面?”德吉警觉地问。
娜珍可怜兮兮地推门进来,她小心翼翼地凑到床前说:“少爷、少奶奶,外面打雷我害怕,听见你们还没睡,我就来了,躲会儿。”
德吉见她冻得发抖,下床给她拿了件衣服披上说:“打雷下雨有什么好怕的,别受了风寒,快回去睡吧。”
这时,又是一个雷电闪过,娜珍一声惊叫,跳上床,钻进了被窝。
“娜珍,你这是干什么?”扎西生气地说。
“我每次遇到这种天气都吓得要命,大多都躲到姐妹的屋里去,今晚我没处可躲。少爷、少奶奶你们就别轰我了,我是让外面的雷声吓破了胆。”娜珍可怜巴巴地说。
“我看……你的胆子比谁都大!”德吉铁青着脸说。
“我不是成心要冒犯您……少爷,自从我回到府上,您就没理过我。”
“当着少奶奶的面说这种话,太放肆了!”
“少奶奶也是女人,她最理解我。”
扎西闻听,知道她要闹事,于是压着火说:“你睡这儿吧,我走!”他起身下床,朝屋门走去。德吉气不打一处来,也随扎西一起出去了。
娜珍见他们走了,笑了,她左右环顾了一下说:“走就走吧,我一个人睡,宽敞。这间屋子就是华丽,雕梁画柱的……被子也软。”说完,躺在了床上。
扎西和德吉一前一后进了佛堂,两个人的脸上全是怒气。德吉气哼哼地说:“还有这种没羞没臊的人,算我瞎了眼,当初就不应该让她进门。”
“就让她把我们俩的睡床给霸占了,不行,我去把她轰走!”扎西气愤地说。
“轰,轰什么轰?整个拉萨城都知道我们家接回来个妖精,你不是还要摆宴给她正名吗?”
“那也不能让她这么张狂啊?这今后还了得!”
德吉怀疑的目光看着扎西,她突然问:“我就奇了怪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张狂?扎西,少爷,你有事儿瞒着我吧?”
扎西低着头,半天才说:“那天……我真喝醉了,我也不知道我都干了什么。”
“真不要脸!”
“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喝醉了,喝醉了也算失身啊?”
“算,算,就算!”
扎西气得大声号叫:“哎哟,我扎西喇嘛一生一世守身如玉,就让她把我糟蹋啦?不行,我去把她拎出去!一刻也不能等啦,现在我就去!”他冲出佛堂,直奔卧室。
扎西刚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白玛站在走廊尽头,望着窗外。扎西冷静了许多,他好奇地观察白玛。白玛掏出那管汉笛,轻轻地吹了起来,汉笛的声音回响在夜色中,仿佛穿过雨幕,抒发着千古悲凉的情思。白玛沉浸在音乐之中,并没有发现他身后的扎西。
太阳照进德吉的卧室,暖洋洋的。娜珍在床上醒来,她见窗外已经风和日丽,起身去推开窗子,感到很惬意,她转身要回床上,突然吓得一声惊叫。原来扎西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冷冷地盯着她。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吓死我了!”娜珍喘着粗气问。
“你说吧,到底想干什么?”扎西问道。
“没想干什么,打雷,我害怕!”
“胡扯!”
“你吼什么?真以为自己是德勒府的主子啦!你有今天,最该感谢的人是我。”
“你什么意思?”
“你不用跟我装腔作势,在这个府上谁都能摆布我,唯独你不能!”
“你说什么?”
娜珍边整理衣服,边搔首弄姿地来到扎西面前,她俯下身,盯着扎西,嘴唇都快贴到了他的脸上,才说:“你是明知故问,哈哈……”
德吉站在房门外面,满脸狐疑,听着里面的谈话。
娜珍放肆的笑声,让扎西一激灵,他脸色有些僵硬,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娜珍的脸忽地冷了下来,口气强硬地说:“你根本就不是其美杰布,你是他的影子,假的!”
扎西惊异,马上又冷静下来。
“呵呵……其美杰布大腿根上有一个疤,那是我们俩一块去哲蚌寺拜佛,他为护着我被野狗咬的,你大腿根上有吗?来来,脱了让我看看。”
“在尼姑寺那天晚上你就知道啦?”
“我们是二十年的夫妻,他身上长多少根汗毛,我都数得过来,你能瞒得过我吗?”
“你想怎么样?”
“二十年了,我跟其美杰布偷偷摸摸,受尽了人间的非难、指责和白眼,今天我儿子名正言顺地回了德勒府,母以子贵,我只想过点儿舒坦日子,安度余生。我还能怎么样,我有什么不对吗?”
“好吧,我就给你母以子贵。”
“只要你肯帮我,我绝对守口如瓶。”
扎西透了一口气,于是说:“你昨天晚上也太过分了,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其美杰布……”
“难道少奶奶不知道你不是其美杰布?大家都在装糊涂,我才不信你呢,你要是真肯帮我,就要给我正名,分我财产!”娜珍打断他说。
“我要是不答应呢?”扎西反感地问。
“你爱答应不答应,担惊受怕的又不是我。拉萨河里的鱼再温顺,你要把它逼急了,它也能翻出几个浪来不是。少爷,噶厦政府不会容忍德勒府乱了骨系!”
扎西火了,上前把她拽过来,拉着她往外拖:“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德吉闻讯跑过来,拦住了他们。
扎西愤怒地说:“你有什么招儿就去使,去噶厦议事厅,去布达拉宫,看我怕你?”
娜珍恶狠狠地盯着他,充满了仇恨。
德吉赶紧打圆场说:“娜珍,你要喜欢这屋,就住在这儿吧,我跟少爷去住佛堂。少爷,走吧。”她连拉带拽把扎西弄出屋去。
娜珍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环视四周,得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