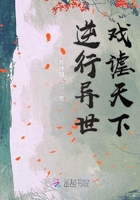多吉林活佛点化他说:“诸法有常规,但常规又随时空而变化。正如当年莲花生大师在印度身穿薄纱僧衣,而到了藏地却要改服厚厚的氆氇,在印度他素食果腹,可来了雪域高原却要喝酥油啖牛肉。常规可以变,唯有心中的信仰要持之以恒。这才算领悟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真谛。”
“弟子还是心有顾虑。”
多吉林哈哈大笑,点拨他说:“扎西啊,我告诉你吧。你和次仁德吉前世曾经是古印度的一对飞鸟,一雌一雄,负责向世界上的鸟类传扬佛法。经过三十六次的转世,你们再次相遇,这意味着从前那段因缘未尽,理应结合。”
扎西大惊,说道:“上师,我曾在您这儿受过比丘戒,就算是前世有缘,我如果对女人产生爱慕,有违教规!”
“这还不好办,作为上师,我可以授给你比丘戒,你也可以把它奉还给我,不就完了嘛!”
扎西闻听,忙趴在地上,给上师磕了一个等身长头。
一个小喇嘛坐在多吉林寺的大殿台阶上吹着汉笛,笛声悠远而孤寂。多吉林和扎西缓缓走来,老活佛对他说:“你在寺里住下,三天之后,我在本尊菩萨前给你举行仪式,收回戒律。”
“全凭上师安排。”
多吉林冲着小喇嘛招了招手,小喇嘛收起汉笛朝这边跑来。多吉林轻声地对扎西说:“这个小伙子叫白玛多吉,很机灵的。”
白玛多吉跑到多吉林身边,恭敬地说:“师傅,按照您的吩咐,招待德勒少爷的僧房已经准备好了。”
“好,你这几天要好生侍候施主,不敢怠慢。德勒少爷,你随他去吧。”
扎西谢过上师,跟着白玛多吉走了。他一边走,一边问:“小师傅,今年多大啦?”
“十八。”
“家是哪儿的?”
白玛多吉摇头。
“摇头什么意思?”
白玛多吉忧伤地说:“我的师兄师弟,有的来自安多,有的来自西康,有的来自北平,还有的来自蒙古,那里就是他们家。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你打小就在寺里长大?”
“是。自打我记事儿,就跟在活佛身边,我把活佛当作我的阿爸啦。”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不苦。这些年您经常来看我,给我布施。我发了愿,把您给我的那些银钱攒到一起,等攒够了,我要给护法神献千盏油灯。”
扎西似乎明白了。
他们转过一个街角,扎西试探地问:“有两个噶厦的苦役犯在附近的寺里服刑,你知道吗?”
白玛多吉想了想,问道:“你是说几个月前刺杀仁钦噶伦的那两个人吧?”
“对,就是他们。”
“他们不在多吉林寺。”
“那在哪儿?”
“关在西郊大寺后面的院子里,和那些黑骨头的工匠在一起。有一次,我去西郊大寺跑腿,看见过他们。”
“如果你现在带我去,还能找到他们吗?”
“能,应该能。”
白玛多吉带着扎西来到了西郊大寺,他们远远地看到,瞎了一只眼的汪丹和洛丹正在院子里和泥修院墙,他们骨瘦如柴,浑身上下泥猴子一样,在喇嘛监工的督促下,吃力地干着活儿。
扎西看着他们,心情沉重。
白玛多吉问道:“德勒少爷,要我过去把他们叫来吗?”
扎西想了想说:“算了吧。”他转身往回走。
白玛多吉善解人意地说:“这里的苦刑犯本来就罪孽深重,他们两个不知受了什么人的指使,胆大包天,刺杀噶伦,受的惩罚就更重了。”
扎西停住脚步,问道:“白玛,你跟这里的人熟吗?”
“有两个师兄常到多吉林寺学经,跟我很熟络。”
“那就好,回头我多给你留些银钱,你帮我个忙,让你那两个师兄多照顾照顾他们。”
“我明白。”
扎西又回头看了看汪丹和洛丹,然后一脸无奈地和白玛多吉离开了。
三天后,多吉林活佛在本尊菩萨前给扎西举行了仪式,扎西把上师授予他的比丘戒,又奉还给了多吉林活佛。仪式结束后,多吉林活佛送扎西出了山门,白玛多吉牵着扎西的马走在他们身后。
扎西停住脚步对多吉林说:“上师,您请留步。您再送我,我更舍不得走了。”
多吉林活佛笑道:“你这个花舌子,在拉萨城里学坏了。你的心早就飞回德勒府了。”说着,他又神秘地凑近扎西,对他耳语起来:“我告诉你吧,昨天晚上马头明王托梦给我,我看见你走在彩虹之上,这是吉兆,说明你将来要经历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上师,您这么说,我就更糊涂了。上次您给我的偈语,我就一知半解。我每次站在拉萨河边的玛尼堆前,都想不明白,那堆玛尼石怎么会飞走呢?”
“那就要靠佛法的神威了。”
“弟子愚钝,还是想不明白。”
“机缘到了,水到渠成,你自然就明白了。走吧,回拉萨吧。”
“上师不回头,弟子不敢走。”
“那好,我先回去了。”多吉林活佛仙风鹤骨般地回寺里去了。
扎西走到白玛多吉面前,接过马缰绳,对他说:“白玛小师傅,这几天辛苦你了。”
“不辛苦。活佛说你不是等闲之人。”白玛说。
“活佛是抬举我,逗你玩呢。不过,我倒是真喜欢你,又机灵又懂事儿。”扎西说着,把手上的念珠撸下来,递给白玛说,“这个送给你,希望你潜心诵经礼佛,弘扬慈悲精神。”
白玛多吉接过念珠,深鞠一躬,说道:“谢谢施主。”
德吉回到德勒府,她想起女儿的嘱托,于是让刚珠把强巴叫来。强巴从外面进来后,恭敬地弯腰站在她面前,轻声地说:“少奶奶,您叫我。”
德吉打量着强巴,问道:“强巴,你来府上多长时间啦?
“回少奶奶话儿,差不到两个月就来府上一年了。”
“你一直侍候小姐,现在小姐也不在了……府上也用不上你了。”
强巴紧张,他扭头看刚珠,刚珠面无表情。
德吉拿起一张契书在强巴眼前晃了晃,问道:“你看这是什么?”
强巴抬头看去,摇头说:“我不识字。”
“这是当初把你从安多头人手里买下的人身契。”
强巴不知德吉要干什么,吓得跪在地上,央求道:“少奶奶,您不要卖了我。您和少爷都是好人,从来没打过我一鞭子,没踢过我一脚。虽然小姐不在了,我愿意在府上接着侍候少奶奶,我手脚麻利什么都能干……”
德吉打断他说:“德勒府上上下下也不缺你一个。”
“少奶奶,您还是要赶我出门啊?”强巴哭着说。
德吉一扬手,刚珠划着一根火柴把人身契点着了,灰烬落进盘子里。
“这是小姐的意思。你忘了?我给你人身自由,强巴,你走吧。”德吉说。
刚珠拿过一个钱袋子,在手里掂了掂,对强巴说:“你命里造化,摊上了好主子,这是少奶奶赏你的洋圆,还有这个,给你自由身的文书。接着!”
强巴哭了,不接,继续央求着:“少奶奶,您是活菩萨,我不离开您。少奶奶要是嫌我碍眼,就把我放到外面的庄园去,我喂马、种地都是一把好手。少奶奶,您留下我吧。”
“我看到你,就想起小姐,心里难过。你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去找他们吧,也了了小姐生前的心愿。”德吉伤心地说。
刚珠把钱袋子递给强巴,强巴不接,刚珠硬塞给了他。强巴把钱袋子抱在胸口,泣不成声。
德吉又说道:“你也是个实诚人,就冲你这点,小姐就没白疼你。我也打听了,你老婆孩子又被卖到了隆子宗,她们在龙色的庄园里。我给龙色少爷写了一封信,你带上,去把老婆孩子赎出来,看哪儿好,再买一块肥地,好好过日子吧。”
强巴离开了客厅,去了德勒府的后院,他采了很多野花来到兰泽的房间,把花儿插在各种各样的瓶子里,摆在兰泽的床头、梳妆台上、卡垫上。他转身走到门口,回头再次环视房间,已是泪流满面,他恋恋不舍,最后跪在地上,冲着兰泽的床磕了一个响头。然后,起身离开了房间,离开了德勒府。
强巴恨不能像天上的苍鹰一样有双翅膀,马上飞到央卓身边。可是,他又害怕去龙色庄园,因为农奴命贱,整天不是被人打骂,就是被人卖来卖去,他不知道央卓和孩子是否还在龙色庄园,是否还活着。他发誓,要拜遍路上遇见的所有佛像、佛塔、佛寺,希望天上的神佛能看见他虔诚的心,保佑他能见到妻子和女儿。
拉萨河里漂着兰泽的水床,经幡依旧,鲜花依旧。水床随波漂动,漂到岸边,搁浅在石滩上。河浪不断地卷来,河水拍打着水床。突然,兰泽咳嗽起来,她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茫然四顾,挣扎着坐了起来。
远处的河岸上,有一支十几个人的康巴商队,他们牵着牦牛、骡马缓缓而行。兰泽听到了牛铃声,想呼救,却一阵晕厥,倒了下去。
一名伙计突然看到了河边的水床,他停住脚步,对身边的同伴说:“你看那是什么?”
同伴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了半天才说:“好像……唉,上面躺着一个人。”
“去看看。”两个人朝河边跑去。
商队管家大声地问道:“你们干什么去?”
伙计举了举手里的皮囊,说道:“水囊没水了,灌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