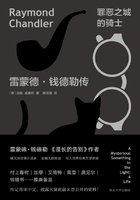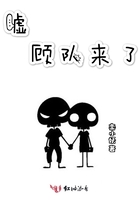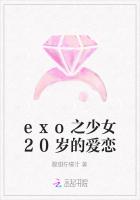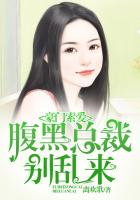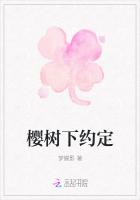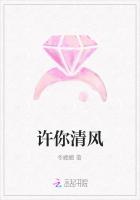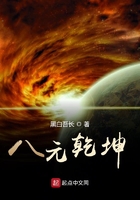我和中国的缘分
倪波路
我和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85年4月。爷爷和父亲讲故事时,我曾多次梦见过那片神话般的土地。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阳光透过薄雾照耀着大地。随着Alitalia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我几乎感觉到浑身的血液都涌向了大脑,那是一种幸福的眩晕,让人欲罢不能。我想象这个时候母亲会细腻地说:“小心点,这可不是寻常的血啊……”就像我们在欧洲常说的。我自豪地感受到我的“贵族血液”随着喜悦的迸发而喷涌,仿佛是中国的焰火。
我记得自己下了联合国的车辆——我是来设在中国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公室工作的,职责是监督开发项目——走过几近荒凉的长长的小径,偶尔在两侧可以看到乡下人或者农民的老马车。尘土真多呀,我心里说。不过明媚的天气预示着我对中国的第一次造访会很愉快和幸运。
起初的几天我被安排住在一个的便宜旅馆,联合国的行政官员告诉我说这是工资和补贴的“官僚炼金术”。所有的这些当时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不久,我便搬到了当时北京唯一的五星级酒店——建国饭店。前后简直是天壤之别。一边是简陋的便宜旅馆,但是那里的职员有着发自内心的热情;另一边是完美的豪华酒店,这里的门童和服务员虽然恭敬却显得疏远。
我忍不住观察这些年轻的男女职员漂亮的外表。天呐,我想到,四百年前来到这儿的意大利传教士得忍受如此的诱惑,真是可怜……在这样绚丽缤纷的世界他们需要怎样的耐心、祈祷和坚贞!
最初在办公室的几个月,我都在熟悉工作,还试着研究中国人复杂的思想。有些时候,当地工作人员的习惯会让我很是意外。我几乎感觉自己是一个侦探,为揭开谜团而搜寻各种痕迹。比如,下午4点,办公室的走廊里就会出现大片的水迹,就像有人拖着刚刚捞上岸的大鱼来回走过了一样。我鼓起勇气到各个房间去探个究竟。我发现,就在下班之前,在明媚的四月天下午,中国的工作人员会去盥洗室冲个冷水澡,之后回到各自的办公室,脸上容光焕发,一幅满足的神情。尤其是女人们,会拖着漂亮的湿漉漉的长发,就像刚刚出水的美人鱼。
时不时地会有新开发项目的中国同僚来拜访我:大部分是上了岁数的男人,他们友善、朴素,有绅士风度。
他们都穿着或蓝或灰的“中山装”,戴着大檐帽——抑或是苏联风格的毛皮帽子。很快,我学会了如何区别来客们的出身,他们虽然外表差不多,但有的是“白手起家”,只有很少几个出身名门望族。
张至善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在来我的办公室之前,他给我的秘书打了好几通电话,谨慎地询问我是不是纯正的意大利人;我是怎么样的意大利人:友善的还是粗鲁的,有没有教养,文雅的还是随便的,我说话是不是温柔,我的态度是否恭敬。
我那未经世事的中国秘书把这些悄悄告诉了我。我不得不剖析自己的性格,努力把自己和张教授想象中的完美意大利人对号入座。
他终于来了。一个面带笑容的成熟绅士,笑得很健康也很有礼貌。他长得很高大,很粗壮,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出现发福或笨拙的痕迹。相反,他面颊红润,带着笨重的皮手套,好像是骑着摩托车过来的。不过他最惹人注目的地方还是他的头发,白雪一般,梳得很齐整。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这里的人们过了30岁就开始把头发染黑了。
张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系主任。他告诉我,他十分欣赏意大利文化,钦佩过去那些伟大的意大利旅行家们的勇气和远见,如马可·波罗、哥伦布、利玛窦等。那天早晨,张教授和我一起讨论,交流文化。随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在延续这类话题的探讨。
真是奇怪!我原以为,只要提及意大利的文化,当时的中国人可能只知道马可·波罗,原来他们还知道那么多!我对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每件事情,张教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比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求知欲”。意大利17世纪的哲学家维柯正是因此被奉为“历史的老师”。如果没有对新发现的求知欲,没有对新鲜事物的喜爱和关注,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就不会在中国留下他们深远的足迹。
当张教授到了从大学退休的年纪时,他对我提到他的人生目标:向中国人民展示西方世界的卓越人物,尤其是与中国搭建文化桥梁的意大利人。他说这一直是他父亲,一位清末资深知识分子的心愿。当时,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道:“但是我父亲的心血已经丢失了。”那是一份手写的《中国纪行》的中文译稿。多亏了意大利人,珍贵的手稿才失而复得。
那么,手稿失而复得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呢?这就是下一章的内容了。张教授多年以前就想亲笔记录下来,在此我就把这件事交给张教授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