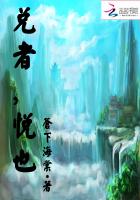从修辞化的历史到历史化的修辞
这就是□□□主义带给美学的政治形势。□□主义的回应是将艺术政治化。
——本雅明(此处引者删去五字)
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本雅明的格言似乎有不同的(假如不是完全相反的)对应。无论如何,只要有足够的敏感,谁都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的宏观历史是美学化的、话语化的、修辞化的历史,而这也正是所有严肃的中国当代写作者所面对的。本辑收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当代文学状态的描述、论述,这些文章大都基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文学如何切入社会历史?
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有多种,最普遍的是简单地呈现历史,似乎历史的客观性是不证自明的。这里的悖论是,“写实主义”实际上蕴涵了最为彻底的(尽管也是最为简单的)主观主义,因为只有绝对地信任和依赖主体呈现客体的能力,才有勇气宣称文学写作能够准确地再现现实。在所谓的写实中,表层世界的一个角落被文字化了,深处的或别处的盲点依旧无法触及。写实主义所写的不可能是完整真实的社会历史,而只可能是遭到思维筛选的、经过主体过滤的历史想象。从理论上说,写实主义无法区分什么是原生态的现实,什么是面具化或包装化的现实,而历史的逻辑(或无逻辑)往往就淹没在这种主体化的现实之下。那么,在众多情形下,这种自我依赖的写实主义便有可能把历史简化成黑白分明的神话。这就是现代中国主流历史写作的辉煌业绩,似乎历史的辩证法仅仅存在于绝对正义与绝对邪恶的对抗过程之中,而写作主体永远代表着正义的历史主体。
这种写作的罪愆在近年来要么从主流话语成功地进入了大众视听文化,要么急速转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对历史意义的虚无主义理解彻底抛弃了历史的深度模式。商品时代汹涌的暗流有力地推动了对历史的闲适把玩:时间的距离使剧痛升华,凝聚成怀旧的收藏或古玩。历史中的创伤被有意无意地掩盖、忽视、装点和涂抹,历史遗物仅仅提供了趣味和自娱。从实质上来说,这是胆怯地逃避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历史在材料的层面上获得了重视。对历史的抽空在某种程度上是主流话语失效后的后备策略:历史的隐秘的动力机制(不管是否能够真正被认知)被再度规避了,另一种幻觉弥漫在后历史的迷雾之中。
作为语言的构筑和修辞的产物,历史(书写的、口传的或哪怕是影像的)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实。相反,修辞化的历史是不断的曲解、掩饰、捏造。那么,当今无法避免的迫切课题便是,如何解除语言的遮蔽(魔法),如何解构主流修辞(包括宏大叙述)的文化垄断。这种解构不是置身主流修辞模式之外剥夺其合法性(这种另置主体中心的企图再度落入了主流历史模式的窠臼),也不是置身历史之外的超然观赏(这种缺乏自我意识的间离往往抛弃了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从邪恶中掘取乐趣)。解构的要义在于从作为历史的修辞和作为修辞的历史之中(而不是之外)开启其无法弥缝的罅隙,而这种罅隙在我看来正是当代历史用修辞来掩盖的东西。
当代文学再度显示了修辞的力量,只不过这一次,修辞以自我否定的面目出现。这种否定也是对美学化的历史情境的自我反观,常常呈现为反讽和戏仿。这样,修辞就不仅是一种文学技巧,而且是诉诸历史记忆的一种文化努力,是同过去、同他者和自我的诘问或对话。
广义地来说,修辞作为文学模式(或文化模式)所规定的不仅是语言思维的基本形态,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是文学的形式本身,而不是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具有直接的社会意味。中学语文式的文学批评常常习惯于游移在形式批评和社会批评之间难以落脚。尽管“怎么写”(形式)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写作的关注,然而一旦涉及社会历史,批评总是毫不犹豫地求助于“写什么”(内容)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形式社会学”的理论阐述,但它试图通过批评实践来探讨文学形式(修辞和叙述模式)的社会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