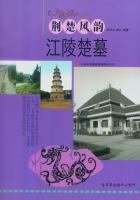《红高粱》:诗化的人性及其悖谬
如果没有“我爷爷”在最后一刻的奇迹般的站起,用石雕式的想象完成某种神圣象征的功能的话,《红高粱》的内在悖谬或许还不那么显见。应该说,《红高粱》的形式能力的确是在对酒神精神的集体狂欢和把人畜一同屠宰的血腥图像之间展示出一种启示性的战栗,然而随之而来的古典悲剧式的庄严仪式却把这种战栗转化为升华,于是观众的视感复归于静穆之美,一种咏叹圆明园式的古老母题把被毁摧的、被撕裂的人性颤颤巍巍地撑竖起来,成为虚假人格的美丽纱幕,一如影片多次重复的镜头——迎风飘舞的高粱——所隐喻的那样。残破的人的废墟,之所以还有悲剧性的力量,大概在于张艺谋依然悲叹着那种失去了的美(九儿倒下的瞬间被延展而强化),依然怀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怀旧情调并欲以此反衬出先前的自由潇洒的生命个体,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怀旧或悲叹早已显得那么虚弱。
于是,《红高粱》和大多数同样才华横溢的第五代导演的影片一样,陷入了一种特殊的两难境遇:它既看穿了传统影片中伪饰的现实意象,又在否弃这种伪现实主义而张扬一种用原始色调和古典悲剧混合而成的人性觉醒的同时,给自己蒙上了一层新的伪饰。假如有人打开《探索电影集》这本书,一定会发现这里所选的剧本除了《黑炮事件》之外,其余全都可归为“返璞归真”型,这种现象并非仅属偶然。不难看出,《青春祭》、《猎场札撒》和《盗马贼》以蛮荒之地的淳朴或野性为自然人格的理想,《黄土地》和《海滩》在文化批判的矛盾反思中也不时带有对蒙昧的恋乡感,《良家妇女》(和《湘女萧萧》不同!)则干脆为纯洁的爱情安排好了令人满意的尾声。所有这一切在《红高粱》中进一步被诗化展示了(尤其是重现了《一个与八个》中的与鬼子光着头拼杀的场面):尽管遭受了剥皮的残忍,人格依旧伟岸,落日依旧辉煌,高粱依旧炽烈地飘动。这一切是美的,但可惜是伪饰的美,是在人性被灭绝后的虚幻的梦。《红高粱》的“返璞归真”从一开始就已定型了:无论是嘶喊的歌声、洒脱的豪饮,还是粗拙的野合,无不洋溢着对原始的自由人性的勇敢张扬。这一切虽然被突如其来的法西斯暴虐意象打断了,但影片仍不忍心舍弃它们以把这种由情感张力构成的反讽性持久化。是的,影片需要用终结的悲壮给它的观众一帖抚慰剂,使他们把残酷升华为人格的悲壮美。
但这种诗化的处理正是我所说的第五代电影的悖谬之处。必须意识到的是,如果现实无法被诗化的话,人性同样无法被诗化。在今天,电影中的这种诗化了的人性(哪怕是原始的、自然的)同样伪饰了某种人的真实境遇。如果电影的理想是诗的话,那么它首先应当是反诗化的,因为只有在剥除了诗化的虚饰意境的幻幕后,诗的电影才可能本质地显现:电影在逐渐正视现实的同时,也必须开始正视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