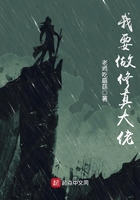第二天上朝,枢密使秦源告假,这回倒不是因秦林之事而故作姿态,而是因为秦源的夫人于氏于昨日夜间为秦源生了一名大胖小子。柴勐听说之后,赐给秦源幼子一把长命锁,一柄玉如意,命吴成代替自己前往祝贺。
吴成来到秦府之后,看到许多东京官员闻风而动,有送字画的,有送金银珠宝,有送果蔬茶点的,当然也有送玻璃器皿、水银镜的,最特殊的礼物乃是来自昌国的最新物件香皂,也不知道送礼之人有何门路,居然能拿到二十余天前昌国刚生产的物件,要知道,这香皂便是在东京沈氏的店铺中也没有销售,除了宫中,只怕这里便是东京的第一批香皂。
满面春光的秦源听说内侍省主管太监奉官家之命赐下厚赏,连忙大开中门,迎到前院,叩谢皇恩。来凑热闹的官员纷纷告辞而去,秦源将吴成引到密室,这才拉下了脸。
“秦相,为何做此面孔?”吴成笑道。
“吴总管,你何必明知故问,”秦源冷笑道,“国师已亡,内人虽诞下国师之种又能如何?没有国师做内应,一切都是泡影。新任国师纯元子自持身份,与我等并无往来,既使以吴总管精通武艺,也动不了那人分毫。”秦源这里所说的那人便是当朝皇帝柴勐,自从慧通大师死后,秦源和吴成二人便结成了攻守同盟,立誓除掉柴勐,灭掉沈家一族。
“秦相,家师虽然亡故,但家师留下的遗物中可是有朝廷众大臣家眷失贞的铁证,有这些铁证在手,不怕那些大臣能翻出什么浪花。至于纯元子,更是不值一提,只要能抓住兵权,火枪之下,再高的武功有什么用?”
“兵权?!我那亲侄子刚被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就差一步便可手握重兵,结果被沈氏父子坏了大事,实在可恶。如今,官家对我似已起了疑心,再安插亲信插手殿前禁卫,势比登天还难。”
“既然亲信不好安插,不如秦相亲掌兵权。”
“枢密使如何能掌握兵权,大周从无此先例。”
“如今这局面,何必贪恋枢密使虚名,不如辞掉枢密使的职事,向官家申请去西夏前线领兵。”
“西夏前线已安排沈括前往主持局面,官家未必肯将他换回来。”提前沈括,秦源便气不打一处来。
“等西夏战事稍有起色,官家见事有可为,谁去都能获胜,便无需让沈括在前线久待,要知道,现在沈括现在已封为国公,若再获大胜,便封无可封。而秦相尚未封公,倒是可以借此机会捞一个军功。以秦相枢密使主管天下兵马的职事,向官家争取节制三路兵马的职位,自然手到擒来。其实,军功事小,只要掌握了兵权,则大事可成。”
“那国师这私生子呢?国师已故,似乎不必再立这小孩子为帝。”
“秦相,我劝你识相些,以你的身份地位,想学那篡汉之王莽还差了些,顶多学学曹阿瞒,挟天子以令诸侯。”
秦源心里面颇为不喜,但吴成武艺高强,明有柴勐为他撑腰,暗中有北辽的背景,对他的讥讽也不敢表示不满。“吴总管高明,秦某受教了。”
吴成看了秦源一眼,得意洋洋地说,“只要那昏君一死,我等便称家师此子乃昏君私生子,然后将晋王、齐王、魏王杀个干净,满朝文武大臣只好认命。”
“只是得背负绿帽之名。”秦源苦笑道。
吴成哈哈笑道,“有谁真会认为你秦相之子会成为官家私生子,只不过敢怒不敢言罢了,只消过上几年,稳定了朝局,待辽人南下,你便可以迁都江南,做你的皇帝去了。”
秦源愣了一下,试探着问道,“吴总管,你虽是辽人,但自幼在大周长大,想来和北辽并无感情。如今,大周已拥有火枪利器,足以荡平西夏、北辽,我们何必再寄人篱下?不如你我二人以秦岭、淮河为界,永结兄弟盟邦,岂不美哉。”
吴成叹了一口气,“秦相,我不管你这话是真是假,承你的情了,如果我没有净身,尚有后人,还会动此心思。可是你看我这残缺之人,能享今世荣华富贵便心满意足,哪会考虑身后之事。况且,你以为汉人有火枪,辽人便没有?自从上个月大辽听说这世间出了火炝之物,便组织人手多方打探,虽然没能抓到做火枪的工匠,但火枪的形状、如何装弹、射击早就搞得清清楚楚。这火枪说到底,不就是一根铁管,里面装上火药,然后把弹丸打出去吗?大辽有不少汉人工匠,迟早会造出火枪来。”
秦源自然知道有吴成做内应,大周有任何紧急军情,都瞒不了北辽的耳目。
“过些日子,这些从昌国归来的工匠便会失踪几个,到了那个时候,大周有的,大辽一样会有,可是大辽勇士的勇猛、数以万计的铁骑,大周却不会有。你我二人离了大辽,依然如无根之木,所以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遵守约定,为大辽打下这片花花世界,然后与大辽划江而治。辽地苦寒,有江北之地繁衍生息,已经心满意足,秦相扼守长江天险,自然能保江南百年平安。”
“当初我与北院大王约定以秦岭、淮河为界,怎么又成了以长江为界?”
“北院大王的心思,非我所能妄加猜测,但是我想提醒秦相,与大辽做邻居不是什么好事,江北之地,无险可守,迟早会丢,不如集中力量依托长江天险,建立铜墙铁壁。这些都是后话,说到底还是看双方的实力。”
秦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如今已上贼船,只盼北辽能信守承诺,勿行卸磨杀驴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