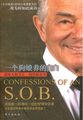爱因斯坦于1933年冬天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他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院,这是美国最进步的一所学校。弗莱克斯纳博士创设这所学校主要是为那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创造在自己的学术专长范围内继续进行研究的机会。这位美国教育家是仿照自由时代的德国大学而创设他的学校,开始时只设立一个数学系,但很快又增加了一些相关科系。
按照弗莱克斯纳博士计划,他所聘请来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们不仅要在课堂上与学生见面,更应该亲自指导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学生与老师的挑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他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遭到不公平待遇。最初,该研究院设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大楼,1940年,迁到普林斯顿郊外几千米的大楼内。
在高级学术研究院内,爱因斯坦教授享受到最大的自由。他不必定期上课,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他对美国大学校园内的随和气氛感到十分高兴。爱因斯坦以前所认识的那些德国教授,随时都要装出政府官员似的严肃面孔。但在研究院及普林斯顿大学内,教授们都很随和。某位教授可以在闲暇时从事园艺或打高尔夫球,也可能出现在橄榄球比赛场地上,热心地为普林斯顿球员加油。往往在同一天晚上,这名热情加油者,又可能担任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的主席。
在普林斯顿,一位教授可能拥有十几项兴趣,或是像爱因斯坦一样,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爱因斯坦第一天被带去看自己的办公室时,学校人员问他需要什么设备。
“呀,”他回答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纸和粉笔。哦,对了,还要一个大的纸篓,至于为什么要大的,因为这样子我才能把我所有的错误都丢进去。”
在研究院里,爱因斯坦博士继续进行他多年以前在柏林所作的“引力场”的研究工作。这个“统一场”的理论,包括引力、电力磁力以及原子核中的力量,这可以提供原子能。爱因斯坦以前的目标是用一项理论来解释这三种不同的力量。
就像他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二十年后,对一位摄影人员所说的:“你拍好照片,就等于完成了工作。但在理论上就不同了,工作永远没有完。”他又说,“目前有两个年轻人跟我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日常问题。”
爱因斯坦很幸运地拥有一些聪明的年轻数学家及物理学家充当他的助手,他们为他解决了许多费力的计算工作。其中一位是黎格波·英斐德博士。英裴德永远记得,当他以前在柏林举目无亲时,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真情。现在英斐德的祖国波兰已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通过爱因斯坦的影响力,他才得以安全逃到美国。
英斐德希望能被获准与他最敬爱的人一起工作。他等待任命,却久无下文,因而显得不耐烦。爱因斯坦温和地安慰他说:“不要急,有许多问题等待了好几个世纪才得到解决,你再多等两个礼拜也无妨。”
与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知道如何保持耐心。英斐德也拥有一种发现者的永恒兴奋情绪,他在自传《寻觅——一名科学家的诞生》里,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我属于科学家的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兴奋的好奇时期。在那段期间内,除了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问题之外,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并不重要……我们也许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找出正确的实验方法。我们必须尝试不同的方法,在黑暗中摸索。而我们一直知道,一定有一条宽阔而舒适的大路,通往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种情绪,不管是爱因斯坦或是一位学生,从事第一项研究时,都曾体会过这种痛苦、失望与喜悦的滋味。
他们两人在一起作了许多次长谈,并从谈话中整理出他们两人合作的一本著作《物理学的演化》。这本书出版之初,英斐德将一本先行赠阅的版本送给爱因斯坦,但爱因斯坦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出版商问了英斐德许多次:“爱因斯坦喜欢这本书吗?”这叫英斐德博士怎么回答呢?因为爱因斯坦教授根本未曾打开过这本书。
“某项工作一旦完成,他对这项工作的兴趣也就随之消失了,”英斐德说,“这同样可适用于他的科学论文上。后来,很多人拿了这本书请他签名,以致使他养成一种习惯,每当看到那本书的蓝色封面时,他就会自动去拿起钢笔。”
在这本书推出的前一天,纽约一家大报的记者在晚上11点打电话给爱因斯坦博士,请他对这本著作说几句话。
“我所能说的,都已经写在书上了。”爱因斯坦回答得很干脆,然后随即挂上电话。
这位记者是否曾费神去阅读《物理学的演化》,从而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不得而知。但确是有很多人争相购买,使得这本书真的成为一本畅销书。英斐德同时很惊讶地发现,在一个星期之后,这本书的销量更大,甚至超越了畅销一时的卡耐基著作《如何结交朋友及影响他人》。
爱因斯坦仍然不发表评论。他对这本书已没有兴趣,就像他以前曾经出版过十本书,但立刻就将它们忘掉了。
他的一位助理,班尼斯·霍夫曼描述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人员讨论某项问题的情形说:“爱因斯坦教授总是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他把自己的头发卷在手指上,沉思一会儿。然后,就会想出答案来。不过,有时候要花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就像在柏林一样,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家也很快成为音乐和闲谈的中心。这位白发、满面笑容的博士,成为附近小孩子们最欢迎的人物。他们都很喜欢述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欢度第一个圣诞夜的情景。
在圣诞夜里,一群小孩子前去按门铃,当爱因斯坦出现在前廊时,他们就开始唱起圣歌来。他很专心地听着,但在演唱完毕后,有位小男孩要求给他们一样礼物,他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礼物?”爱因斯坦问道。
“哦,人们通常赏我们几毛钱。”
“等一下。”爱因斯坦博士说。
这些小孩子认为他是要到屋内去拿钱。但几分钟后他再度出现,穿着皮上衣,戴着一顶小帽,一手拿着他的小提琴。
“我跟你们一起走,你们唱歌,我拉小提琴。”爱因斯坦说,“但你们一定要答应分给我一点钱。”
在他们到达美国后的最初几个暑假里,爱因斯坦一家人找到了一处宁静的避暑胜地,使爱因斯坦可以再度享受驾驶游艇的乐趣。有一次他把游艇开上了沙岸,被一位划船的小男孩发现了。
“怎么了,先生?”他叫道。
“这儿的水太浅,必须等到涨潮后才能离开。”爱因斯坦回答。
“要不要我去找艘大一点的船来把你拉出来?要等四小时之后才会涨潮呢。”
“不必了,谢谢你。”
“但是,你在这四小时之内怎么办呢?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对这位好奇的小男孩摇摇头。“我会很愉快的,我可以坐在这儿想问题。”他回答说。
爱因斯坦教授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的同时,艾莎则试着使他们现居的房子像他们的柏林老公寓那般舒适。熟悉的家具和照片使她不致觉得太寂寞,她知道他们不是短暂访问这个友善而陌生的国家了。已届中年的她,发现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她经常想家,怀念她从小熟悉的景色及人物。她想不通,为什么丈夫那么快就能适应美国的生活!
这时又传来她的女儿伊莎在欧洲死亡的不幸消息,使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她非常悲痛。幸好她的另一个女儿玛嘉特也搬到普林斯顿,才使她稍感慰藉。
随着他们一家搬到美国的,还有爱因斯坦博士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小姐。她现在必须回复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信件,像是:“能否请您运用您的影响力来影响柏林的美国领事?我的家人和我都得不到签证,而等待签证的人又那么多。如果我们不赶快离开德国,可能就太迟了。”有位学生要求帮助他进入美国大学;一位逃出德国但留在西班牙的犹太科学家,请求爱因斯坦推荐他在美国担任一项研究职位,多么卑贱的研究工作都可以。
爱因斯坦一向乐于协助不幸的人们。现在他比以往更热心地向这些陷于绝境的难民们伸出援手。曾经有一次,有人问道,为什么他同时推荐四个人去担任某一家美国医院的X光医师?
“我推荐四个人去担任同一个职位,”爱因斯坦承认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而且我也叙述了这些理由。相信医院方面会视才而录用的。事实上,他们是这么做了。”他对于不能拒绝这四个求助者的这件事,似乎觉得很不好意思。
在到达美国后不久,爱因斯坦博士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为犹太难民们筹募生活基金,结果募得六千美元。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不愿抛头露面。他认为自己所能办得到的只是自由捐款,以及利用他的名气支持他所感兴趣的团体。但现在,由于情势需要,爱因斯坦开始撰写文章,并在电台发表演说,攻击日渐严重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他以绝对的权威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他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逃往美国最有成就的犹太难民。
在纽约世界博览会期间,巴勒斯坦也在会场设立自己的展览馆。每当某一个国家的展览馆揭幕时,那个国家的大使就要向美国大众发表欢迎的演说词。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仍在英国控制下,并没有自己的大使,那么应该由什么人来代表巴勒斯坦致欢迎词呢?负责的委员会考虑了许多位杰出的犹太人。最后一致认为,再没有谁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更能代表犹太人。
不久,他甚至接受劝告,穿上僵硬的衬衫和礼服,出席纽约的一项午餐会,庆祝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技术学院在美国成立高级研究所。尽管他为人谦逊,但这一次似乎很高兴特拉维夫的物理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此时希伯来大学也拥有了自己的校区,可以俯视整个耶路撒冷,该校接受了爱因斯坦捐赠的相对论原稿,并把它视为一项最宝贵的礼物。
巴特莱·克拉姆在他的《丝幕之后》一文中,谈到爱因斯坦给他的印象:……他走进房内,使我们的听证活动受到打扰。虽然当时有另一位证人在作证,但当房门打开,听众们一见到他们在报纸杂志上经常见到的那个熟悉的人影时,立刻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满头白发几乎垂到肩上,步伐缓慢,看来好像是从圣经故事中走出来的先知。哈奇森法官大声呼叫遵守秩序。后来轮到爱因斯坦发表证词时,哈奇森法官说:“那些认为我刚才阻止他们向爱因斯坦博士表示欢迎的人,现在可以向他表示欢迎之意了。”房内立刻响起了如雷的掌声。爱因斯坦博士低声向身旁的一位朋友说:“我想,他们应该先听听我要说什么,然后再鼓掌。”……
曾在柏林出现的那种对爱因斯坦的英雄式崇拜,在美国又再度出现。有一次爱因斯坦在匹兹堡对一群科学家发表演说,演说完毕后,他退到礼堂的贵宾室,布幕开始降下。有位狂热的听众竟然跳上讲台,抢下爱因斯坦刚才用来在黑板上讲解理论时所使用的粉笔。他虽然拿到了粉笔,却被急速降下的布幕打中头部,当场昏倒。
当以相对论为题材的影片在纽约的美国历史博物馆放映时,许多无法挤进去的观众曾企图把大门推倒。第二天早上一家日报的头条标题是:“博物馆的警卫被科学迷制服,警方驰往增援。”另一家报纸的标题是:“四千五百人为了观看爱因斯坦影片,在博物馆大打出手。”
在爱因斯坦一家人搬到普林斯顿三年后,麻色街舒适的老家生活方式因为艾莎的生病而受到影响。以前她经常在屋内跑进跑出,一会儿在厨房里为她的丈夫准备他喜爱的茶点,一会儿又跑到客厅,对一位访客说,不可以打扰她的先生。
在妻子弥留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爱因斯坦并未到研究院为他准备的办公室去,他都是留在家中二楼的书房里研究。从大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到艾莎十分喜欢的那个花园。他经常将桌上的一些文件推开,试着翻阅书架上的几本书。不久,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坐在他妻子的床边,很少说话,只是静静聆听她诉说在德国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有时候,她会提到她的女儿伊莎:“她是那么漂亮,那么年轻,竟然去世了。”一旦勾起慕尼黑儿童时代的回忆时,她就会谈到爱因斯坦屋后的花园以及爱因斯坦最喜欢躲藏的那个树丛。“你那时候真是一个很不友善的小男孩,你总是躲着玛加和我。当她嫁给你在瑞士最敬爱的一位教师的儿子时,我们都太高兴了。我希望她能早点来看看我们。但我想我不会在这儿见到她了。”
在艾莎去世几天之后,英斐德前往麻色街拜访,家里的人告诉他,教授已回到研究所的办公室工作了。
英斐德感叹地说:“只要爱因斯坦还活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