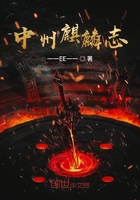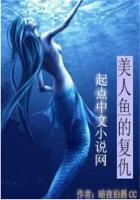夜静阑珊。
浓重的夜色稠得好像化不开的墨,一轮下弦月悬在东方空中,好像一滴清水滴进其中,却怎么也化不开这浓墨重彩。
有微凉的夜风轻松吹进大殿如入无人之境,混杂着焦味和血腥味,吹鼓了袁珏伤和李恩的衣裳,猎猎作响。
原本犹如仙境的大殿已经化成一片废墟,青玉扶着阿桥回到破败的殿中。李恩和袁珏伤在灰烬中背靠背坐着,焦尾琴就放在李恩手边。刚才那一招消灭掉了大半的妖怪,剩下的妖邪也都作鸟兽散,四处奔逃。
袁李二人都没事,青玉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受伤最重的反而是阿桥,她腹部和脚踝各有一片衣衫被血染红,面白如纸,娇喘连连,在青玉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回到殿中。
“快来帮她。”
袁珏伤先站起来从青玉手中扶过阿桥,把她扶到一根折断的柱子下让她倚着柱子坐下,李恩站在原地没有靠近,她还在想真谷主对她说的话。
“她刚才去追薛朝宗,被他打伤了。”
“那薛朝宗呢?”
“死了,只可惜让袁珏明跑了,没有为青兰报仇。”
青玉神情落寞,阿桥抿起嘴有些内疚。
“对不起,你是为了帮我才让他逃脱的。”
“不怪你,以后还有机会。我刚才看了,腹部是皮外伤,脚踝伤到了筋骨,暂时没办法正常行走,不过都是妖,好好休息几天也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先帮你包扎一下吧。”
袁珏伤不由分说先用天伤剑把阿桥伤口周围的衣服小心翼翼的割开,露出胜雪的肌肤,还有一道道丑陋的疤痕,这是之前阿桥因为帮助袁珏伤受到的惩罚。伤痕唤醒了他心底的愧疚,他轻叹一声目光并未久留,而是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道布条,先帮阿桥包扎住脚踝的伤口,又撕下一大片裙锯,解下腰封把布片缠在她的腰上,动作轻柔又仔细。
阿桥低头看着袁珏伤帮自己包扎时认真的神情,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痒痒的,看向他的眼神不自觉温柔似水,李恩心里却翻江倒海一样难受。
包扎完毕,袁珏伤一抬头就对上阿桥温柔的目光,两人目光交缠片刻都有点不好意思,袁珏伤干咳一声。
“这是报答你之前救我的恩情。”
“我知道。”
两人有一搭无一搭的说着话,那边青玉把李恩拉到一边,李恩先一抱拳向青玉道歉,“对不起,把你的宫殿毁成这样。”
“无妨,本就是身外之物,只是此次谷中折损不少兵将,想要再恢复恐怕要花上一段时间了。”
“这件事说到底也是因为我们,还有青兰。”
“不怪你们,一切都是天意,由不得我们决定。对了,她怎么样?”
李恩知道他说的是真谷主,她点头微笑道,“她很好。”
只有简单的三个字,但青玉却像个孩子一样咧开嘴角灿烂的笑了,李恩听出笑声中的苦涩却没有戳穿。
“她倒是成了甩手掌柜的,把烂摊子留给我自己躲清静去了,也好,不理人间俗事,不受红尘扰,比我们这些人要好得多了。”
“只是兰花谷的重担要落在您的肩上了。”
“这点李姑娘不用担心,反倒是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我也这样打算的。”李恩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他们带着焦尾琴一走,无论是钱塘妖市还是袁家的追兵都会集中注意力对付他们,就不会再找兰花谷的麻烦了。
李恩再次抱拳向谷主告辞,走到袁珏伤和阿桥身边,声音冷若冰霜,“我们该走了。”
袁珏伤转身背对阿桥蹲在地上,把后背留出来。
“我背你。”
阿桥一愣,同时也看到李恩脸色变得很难看,她犹豫一下却还是爬上了袁珏伤的背。李恩快步走出大殿,走到他们前面把他们远远甩开,袁珏伤想追上去解释可是他动作幅度一大阿桥就会叫痛,只能稳步慢慢的走,他们一前两后分别往山下去。
阔达空旷的废墟中,青玉之前的那把座椅还剩下一半,他坐在上面,看着他们的背影双目茫然。在他们走远之后,突然从殿外方向,就是刚才截住袁珏明的地方有一颗金色的珠子飘出来,停到谷主面前半丈远处,青玉喜不自胜,声音颤抖,“青兰,是你吗?”
那金珠没有回答,青玉伸手想要触摸珠子,那珠子却往后退了退,他的手停在半空,颓然落下。
“以后就真的只剩下咱们俩了。”
青玉的喜悦瞬间转为落寞,那珠子好像能听懂他的话一样,缓缓靠近青玉,在离他眉心还有三寸的时候突然加速,金光一闪而过径直穿过青玉眉心,他的脑后喷出白色的脑浆溅到仅剩的半边椅背上,随后直直往后一倒,脸上的表情依旧怅然若失,除了眉心那个洞以外,根本看不出来他已经死了。
那颗金珠子离开宫殿,离开兰花谷,消失在了无边夜色中。
袁珏伤背着阿桥走得慢,回到山脚下那家客栈的时候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太阳洒下了第一缕阳光,带着舒适的暖风和濯濯晨露一起降临人间。
袁珏伤觉得通体舒畅,人一放松下来就觉得有困意袭来,回头看到阿桥已经在他背上沉沉睡去,他也眯起眼睛打个哈欠,拐个弯就到了客栈门口,门外马车已经停好。
李恩斜倚在车上,头微仰,正在享受阳光,橙黄色的光芒在她脸上勾勒出温暖的轮廓,车门旁系着用来收起门帘的白色丝绦垂在她的面前,被风吹起拂在脸上,虽然她闭着眼睛不带表情,但袁珏伤能感觉到她的心情不错,刚才的不愉快好像抛到了九霄云外,嘴唇微动,好像还在哼歌,她的右腿缩起来被双臂抱住,左腿耷拉着在晃来晃去,看上去天真无忧。
袁珏伤偷偷走近她,想听听她在唱什么歌,可是李恩早就听到他的脚步声,他一靠近就停止了低吟,睁开杏眼看着他。
“上车吧。”
袁珏伤点头,李恩下车帮他把阿桥扶进车内,在座位上放着一套新的衣裙。
“你进去车里坐着吧,我来驾车,那衣服是给她的,一会儿她醒了自己换上。”
“还是我来吧。”
“我看你的样子很累了,进去去坐着吧。”
李恩硬把他推进去,袁珏伤发现另一个座位上放着个油纸包,拿在手里还是热乎的。
“我刚才饿了,正好遇到一家点心铺开门早,自己吃饱了顺便给你们也买了点。”
袁珏伤注意到她用的是“你们”而不是“你”,他感到这个词语有种暧昧的感觉,被称为“你们”的两个人之间好像都有种亲密的关系,让他觉得不自在。
他走到车外放下帘子,坐到车头的另一边。
“不是让你进去休息吗?”
“我不累,那个”他搔搔耳后,“我背着她是为了报恩,有一段时间我们被关在一起,我逃跑的时候也是她帮我打掩护的,所以我总觉得欠她的。”
“是吗?”李恩说的轻描淡写,毫不在乎,但心里还是介意。
袁珏伤打开油纸包,一股清香扑面而来,纸包里包了十几块各色的点心,他一眼就看到其中有三块梨花酥,这是李恩最喜欢的小点心,她打小就喜欢吃梨,还有一切和梨有关的食物菜肴。
甚至有一次为了吃百花楼里独有的梨花糕,特意女扮男装翻墙出去找袁珏伤拉着他去了平康坊,还美其名曰让要他见见世面,两个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故作成熟的打扮一番就大摇大摆的踏进了烟花柳巷。
两人一进去就被迎面而来的软香红玉,莺歌燕语羞红了耳根,他们穿着打扮一看就是有钱人,虽然面庞稚嫩但都生得俊俏,一路上没少了招蜂引蝶。
好不容易来到百花楼在门口交了盘子钱,刚一走进楼里,浓妆艳抹的老鸨子就扭着腰迈着小碎步迎了上来,用怀疑的眼光把他们从头看到脚,心想这两个雏儿毛还没长齐就来逛窑子了。
百花楼并不是上等的妓馆,其中的女子也是姿色平平,独独楼里的一位点心师傅让百花楼的名声传了出来。这位师傅的手艺是跟黄鹤楼的点心师傅学的,出师以后想到京城来闯一闯,被这位眼亮的妈妈发现,花大价钱聘回百花楼里。
这位师傅最拿手的就是用各种花制成的点心,正好配合百花楼的名字,其中最出名的就要数桂花糕,桃花羹和梨花酥了。
桂花糕香味馥郁,甜而不腻,吃上满满一碟子都不会烦。
桃花羹淡雅清甜,桃花又有美容养颜的作用,最适合楼中女子食用。
梨花酥清甜酥脆,同时保留了青梨和梨花两种香味,是李恩的最爱,她从府里下人那里听了一耳朵这里的梨花酥有多好吃,之后就一直惦记着。
虽然面相嫩,但老鸨子才不会和钱作对,乐呵呵的把他们带到隔断的雅间坐下,同时老鸨子天花乱坠的吹嘘自己的姑娘多么色艺双绝,李恩摆摆手,随即从袁珏伤腰间扯下钱袋看都不看直接扔给她。
“那个不着急,你慢慢挑,先给我们来两盘梨花酥,要快。”
老鸨子下去,有人先上了梨花酥,等老鸨子带了姑娘过来,李恩面前的盘子已经空了,她正往嘴里塞最后一口,嘴里满满当当的说不出话来,端了杯清茶喝了一口把点心顺下去,拍拍前胸才说出话来。
“你们俩坐,对了再来两份梨花酥,还有那个什么桂花糕,桃花羹也都各来一份。”
李恩小手挥个不停,老鸨子听了她的话后十分无奈,这到底是来找乐子的还是来吃的,但还是陪着笑脸下去吩咐。
没多久,李恩面前摆上了六盘点心,袁珏伤坐在旁边靠在墙上看着她吃自己也有点饿了,伸出的手还没碰到梨花酥就被李恩打了回去。
“我怕你吃不完帮帮你。”
“是你多虑了。”
“要不再叫几盘?”
袁珏伤低声下气的问,他们在一起的李恩反而更像老大,喜欢指挥他干着干那。
“你的钱袋都没了。”
“你没带钱?”
“本来带了,不过翻墙的时候掉了。”
袁珏伤扶额,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李恩听到了看着他瘪瘪的肚子,才小心翼翼的从每个盘子里取出一两块,放到一个空盘里推给袁珏伤。
“大爷赏你的。”
袁珏伤嘴角抽搐。
两个妙龄女子被冷落在一旁,任她们怎么挑逗那两人都无动于衷,她们胳膊杵在桌子上,手指绞着头发无聊至极,过了一会看这两人确实对他们不感兴趣,才互相递了个眼神,识趣的离开了。
半晌,李恩酒足饭饱,袁珏伤食不果腹,两人迈着方步走出了百花楼,离开了平康坊。
忆起旧事,他把头靠在车上侧过去看李恩,看得她浑身不自在。
“我脸上有东西吗?”
袁珏伤笑着摇头不语,李恩顺手拿起一块梨花酥塞进他嘴里。
“吃吧。”
一股清甜在他味蕾上扩散,一直甜到心里。
吃了几块点心后他竟然靠在车上睡着了,等他再醒来已经接近中午。
可能是太累了,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不过这一下睡了个够,醒来时容光焕发精神大好。
“醒了?”
李恩侧过头看他。
“嗯,到哪儿了?”
“快到桐庐县了。”
“桐庐县?我们往哪里去?”
“湘西,龙泉剑在那里。”
“你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我告诉她的。”阿桥突然搭话,一撩帘子探出头来,夹在两人中间,她的脸色已经没有之前那么苍白,而且也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薛朝宗死前说的。”
“他怎么会把消息泄露给你?”
“他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有什么不能出卖。”
“那你信他吗?”
阿桥不语,回忆起薛朝宗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向自己求饶的样子。
人被逼到绝境时为了保命说出来的话,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