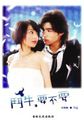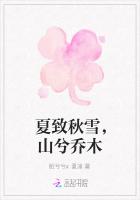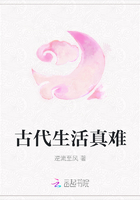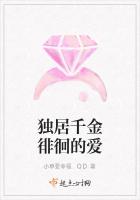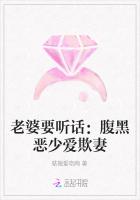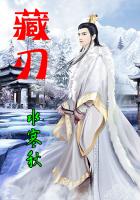赤螺坑村被一条自东往西的赤螺溪隔开。村有潘姓和梁姓两姓人家,各有百来户。梁姓的人居住在溪的北边;潘姓居住在溪的南边,要过溪。溪面八九丈宽,过溪无船,也无桥。溪中三十多块大小不等的石块,一半没在水中,露出水面的一半成了行人的路,俗称“石跳”。下雨天发洪水,溪两岸的人自然不能往来,遇有急事就用竹排。
潘姓与梁姓结怨不和由来已久。听长辈们讲,一代传一代传下来的说法,是因为私塾学堂选址时大动干戈,火并致死人。 梁姓与潘姓两姓都同意建私塾学堂。培养有文化的下一代子弟是件大好事,常在长辈们惦记和设想之中。可是选学堂地址,选来选去不合适。选在梁姓居住一边,潘姓不同意;学堂地址选在潘姓这一头,梁姓不允许。最后经人提议,看潘、梁两家哪姓地头重,私塾就设在那里。地头重不重,用什么来衡量,自然是水,是井水。取来梁姓和潘姓的井水,用同样的瓮罐装满过秤,看哪姓的重些,私塾学堂就设在那里。两姓的人十分赞同。人称:海水不能斗量,可是这回真的要量水称轻重了。没料到,潘姓使诈。在前一天,往井里倒下几百斤盐巴。结果同一瓮罐的井水(盐水),比梁姓的井水重。
最终,学堂就建在潘姓一方,叫“田心坝学堂”。后来发现那口井周边的人一反常态,到溪边挑水、洗衣,这样露了馅。梁姓山民被戏弄,感到莫大耻辱,怒不可遏,抄起扁担、锄头、戟,甚至是火铳,与潘姓的人厮杀、拼命。在双方的搏斗火并中,梁姓二死,潘姓三死,惊动了县衙内,把双方带头闹事者关进了牢。自此后梁、潘两姓结了怨长了仇,不通事不通婚。不通婚一直沿袭到现在。两姓语言不相杂不相容。梁姓讲的是客家话,潘姓说的是闽南话。相互打招呼时,你说你的客家话,我用我的闽南话应对你。双方对对方说话的意思内容都明白清楚,就是不用对方的语言来交流,表示自尊。这个风俗现在不存在了。 潘姓家里死了人,设有神位灵牌,一直供奉在家里的客厅里,不仅占位置,逢年过节要祭拜。烧香烧纸引发火灾,失火屡有发生。在省城做官的潘祖德,有一年回来后,提议学习城里人和外地人。祭先祖,纪念祖宗,不一定要设个神位灵牌,更不要在家中设神龛。同姓同祖同宗的建个祠堂,有设神位灵牌的集中放置在祠堂内,没有设神位灵牌的在先祖牌上刻下芳名,以纪念和祭拜。他是当大官的,是潘姓的光彩。他金口玉言。
既然潘姓上下都赞成,那就定下来。至于花费开销问题,按每家的男丁摊,每丁一个光洋,不足之数由潘祖德支付。经费解决了,接下来是选址,选在什么地方合适。 选址十分难。在潘姓居所外三个方向都不行。风水先生最后看中的是村头老枫树旁那块地方。风水先生振振有词认为,东西走向的赤螺溪,到村头,就被一座高山挡住,溪水直拐往南流去。不到百米,下泻龙潭,有两级的瀑布,名叫“载霞瀑布”。溪北面峰山自此延绵千里,高峰兀起,龙脉在此,庇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祠堂的大门对着东来之溪水,宛如流金装入口袋,佑潘姓子孙万世富贵。此地乃风水宝地也,其境极佳。风水先生斩钉截铁说:“经数十年之山,涉几十秋之水,尚未见过如此绝妙之宝地,千载难寻。千万不可错过,否则悔之晚矣。”
大家听风水先生这么一说,心热手炙恨不得现在就在那把祠堂建起来。 “什么?村头枫树头,你们潘姓要建祠堂,那是什么章法?”梁彭祖迷惑不解大为恼火对潘姓来人说。潘家人急着要动手建祠堂,潘祖德说不可莽撞,要与梁姓的人吹吹风,通通气,千万不能为此两家又闹起来。
因此潘祖德派三个能说会道的人与梁姓族长梁彭祖谈起此事,话未说完,梁彭祖大光其火:“你潘祖德要建祠堂,我梁彭祖更想建祠堂。也不看看,枫树在溪的哪边?要建什么也轮不上你们潘家。”潘姓来人马上说:“梁族长,息怒。我们是与你们商量商量。枫树头那是公地,我们两姓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你们不问问,枫树前,那棵桑树,是谁栽的?栽树做吗用?”梁彭祖话说得很重,意思很明白。枫树头那块地是梁家先占着的。“谁栽树就是谁的地。这还用声明吗?祖传的法子你们还不知道吗?那棵桑树,现在已枝繁叶茂。那桑果,你们潘家大概也摘着吃吧。现在还说那块地两家都能用,岂有此理。”
潘姓来人见梁彭祖没有通融的余地,很是焦急,见梁彭祖身后的人越来越多,感觉不妙。弄不好闹成僵局,那就砸了,便起身说:“我们下次再来,请梁族长多包涵,我等告辞。” “不用再来了,就是请你们潘祖德来,也谈不成此事,大家相安,好自为之。”梁彭祖也起身将来人送至门外。
第二天,有通报,潘祖德求见。梁彭祖觉得不理会,恐不妥。命人将茶盘洗净,重新烧水沏茶,他立在门外,恭候迎接。
“潘官人,您到寒舍来,屈尊降贵,小人不敢当。”梁彭祖一套客套话。 “彭祖小弟,不要客气,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老兄我从省城带回有两瓶洋酒,是法兰西的,不成敬意,请笑纳。”潘祖德说着,把酒放在茶几上。他一身灰色中山装,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潘祖德坐定后,梁彭祖用手一甩对襟开长衫的下摆,相对而坐。梁老四在旁沏茶。 “彭祖小弟,恕兄直言。潘姓要建祖祠,就是选不好地方,选来选去还是枫树头那块地好。如果地选不好,上对不住祖宗,下对不起子孙,你说是不是?”潘祖德开门见山。 “枫树头那块地,我们先占用了。我们也想在那建一座祖祠,你们是不是另选地基?”梁彭祖不让。但对对面坐的当官有学问的潘祖德,梁彭祖语气不是昨天对三个来人那样吆三喝四。 “昨天我去县城办事去,让他们先来几个人向你禀告一下。他们言语粗鲁,多有得罪,请老弟见谅。” “实不相瞒,村头那块地,我们梁姓不能让你们建祠堂。” “我们协商协商,望老弟通融一下,你们梁家也在那建一座。” “我踏过那地皮,建两座太小了。再说,两姓祖祠挨一块,争气争光,不合情理,也多碍事。”
“依老弟之见,如何处理?”潘祖德以退为进。 这一下把梁彭祖难住了,他想对方让自己拿主意,说明对方宽容大量,礼让在先,有理让三分。如果强撑下去,伤了对方脸面不说,也显自己小家子气。梁姓暂不建祠堂,日后还是要建的。就是不建祖祠,也得留着给自己百年之后用。几年前自己相中那块地,所以种了桑树寓意吉祥。如今桑树有盘子粗了,年年结桑果,很是富有生机。他想到这里,权衡来权衡去,放弃那块地实在可惜,万万使不得,于是,不管对方意诚语善,脱口而出:“那块地我们先占用的。”
“这样吧,我们把那块地和那棵桑树都买下来,你看怎么样?” “这……” 在场续茶水的梁老四,冷不防插了一句:“双方都想要这块地,又只能建一座,不然就抽签,抓阄。” “你插什么嘴,滚……”梁彭祖怒斥梁老四,“滚”字要出口,碍得潘祖德在场,改口“还不快出去”。 “哎,这倒不失是一个办法,抓阄,谁抓到谁建;抽签也行,由第三人做一长一短的竹签,抽长的为胜。”潘祖德和颜悦色说,“如果我们赢了,把你那地连同桑树都买下;我们输了,就不提此事。” “我想想,这到底行不行。
”梁彭祖认为,如果自己没抓到阄,也没捞个胜签,那不是白搭了吗?抽签、抓阄显然公平,但这块地是自己先占用的,岂能拱手让出,心中不悦。想到梁家历来有“秀才满林”之雅称,读书的人多,有到省城的,有出国留洋的;梁姓文人多,读过洋学堂的梁家弟子能掐会算,能写会画,能拉会唱,琴棋诗画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还有负有名气潮剧戏班子。梁家人才多,何不来打擂台比艺呢?这可比抓阄、抽签胜算多。虽然没有人在省城当官,但比文竞艺略高潘姓这是公认的。比文竞艺这是梁家强项,绝对比潘家高出一筹。想到这里,他眯着双眼,对潘祖德说:“我看,不如我们两家来个比艺?”
“比艺?只要不斗武就行。如果斗武闹出人命来,有悖建祠堂的宗旨了。老祖宗在天之灵也寒心,不安宁。”
“是比文竞艺。” “怎么比法?说来听听。” “教我们两家弟子的耿先生,你是认识的。”
“我认识。是个热心肠的满腹经纶的哲人。” “叫他做中间人。由他来出题,三局二胜。”
“噢!没文化素质的后代建不好祠堂。就是比下去,祖宗也会原谅,后代也认份。激励读书,教子有方读与耕呀。好!就这么办。”
“让耿老先生出题和主持比艺的事,是你去联系,还是我与他商量?”
“我同老弟一块去学堂,同耿老先生会面商议。” “好,时间你定。”潘彭祖心中窃喜。
潘祖德、梁彭祖第二天来到田心坝学堂,见过耿老先生。耿老先生是教私塾的,在这个村的田心坝学堂已执教鞭四十多年了,德高望重,众人敬仰,村民敬称他“耿私塾”,他俩说明来意后,耿老先生大为惊讶说:“老朽年事已高,岂能担当此等大任。出题的事,还好说,可评判是非高低,老朽万万不敢从命呀。”
“耿老先生,您出题。至于评判呢,有您、我和梁老弟三人,您大可放心吧,啊!”潘祖德说,又转过头问梁彭祖,“你看呢?”
“我看就这样定了,耿老先生您出题,我等三人评判。”梁彭祖说。
“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责任重大,老朽难担此大任,负不起呀。我看你们到县城邀个官儿来,让他们出题评判。”耿老先生欲再推辞。
“我们是山民野夫,粗疏鲁莽,只要能分个高和低就行,又不像洋学堂、县衙门那样正规,拼死拼活拿名次,决一雌雄,请先生不必推辞。”潘祖德、梁彭祖坚持说服着。
“出哪些、哪类的题?比什么,是琴棋书画,还是对对子?是心计口算,还是……”耿先生还未讲完,潘祖德、梁彭祖几乎同声:“由您老先生定。”
“不!现在我们三人就定下来。”耿先生说。
“那好!您老先生提个头。”梁彭祖附和着。
“这类比赛,不要偏僻,不要太难,要平民化,要两家子弟都靠有谱儿。不光是我们三人当评判官,两家子弟也懂得,也是评判者。”梁彭祖、潘德祖听罢点了点头。梁彭祖说:“比哪类好,老先生您出题。”
“依老朽之见出一些普普通通的吧。还有那规则呢,参赛的人选,怎么定?是当众还是不当众?刚才二位说三局二胜,这恐不行。我们出几个题目,答对的多就胜出。”耿先生说到这里,突然又感到自己责任确实重大。梁、潘二姓历来不和,人称两口滚开的锅,都冒热气。为建祠堂争高低,比赛胜者可以建祖祠,皆大欢喜,失败者没有资格建祠堂,怨气冲天,那还不怪罪我老夫子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夫一生正直勤勉,乐善好施,一生清白,不要为这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但见二位尊长如此厚爱,又不好推辞,进退为难。耿先生想,为了潘、梁两家和好和睦,这才不枉老夫一片苦心。
自己在这里授业执教几十年,要对得起梁、潘两姓民众的厚爱,对得起他们衣食和恩泽。自己要知恩回报,不可亵渎知识,不可亵渎先生之名,不可留下憾事被后人贻笑。他想到自己同梁、潘两姓子弟相处犹如兄弟般的情深,对他们的关切宛如手心手背。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情深意长,自己怎的可以为难他们,甚至伤害他们呢?耿老先生了解潘姓子弟善算,尤其算盘技艺高;梁姓子弟绘画书法好,出了几个名人。潘姓擅长对对子;梁家精于猜谜。自己何不出一些他们可扬长避短的题目,让他们打个平手,互不伤害。老夫子才不愧对他们。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战国时子思认为,“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耿老先生想到这里,对二位说:“二位尊长,出题的事容我想想。刚才说现在就定,不仅困难,且也草率。你们二位,现在回去,明天我到潘府上再议如何?”
潘祖德、梁彭祖表示同意。 潘祖德府上的客厅里摆设气派。一张红木八仙桌,八只檀木龙椅。座钟正指9时,天井旁厨房里,“嗤嗤”冒着热气的铜壶瓦亮。大厅两侧两盆红、白茶花争芬斗艳。耿私塾如约来到。潘祖德、梁彭祖起身恭迎。 大家坐定喝上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