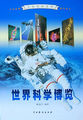“公主,公主不好了,公主”
在宫中竟这么没规矩的喊着,路晼晚不觉眉头微皱,她正在倒弄桌上花瓣的手不悦的放下一片嫣红,抬头看着神色慌张的丫头,从来不习惯约束管教下人的路晼晚也忍不住说上几句:“这是在宫中不比府里,你这样冒冒失失的成何体统”?蝉止听着她的训话倒也不怕似的,自顾自的说着,“公主,实在不是奴婢冒失,您且听完了奴婢的话在责罚也不迟”。“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倒是说啊,我爹娶后娘了啊。”蝉止似是听惯了路晼晚偶尔说的奇怪的话,也不惊讶,只想着把刚才在外面听到的说与她听。
“公主,您可知道,皇上为您选的绝色驸马是东厂九千岁”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一阵坚定又质疑的尖叫声响彻整个蓼坞苑。路晼晚听完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吓得蝉止痴痴愣住,此刻嬿归也跟着进来,看见她家主子又回到那日落水醒来后的神情,吓得几乎要哭出来,两个丫头跪在榻前看着路晼晚不知所措。
“蝉止,你是听谁说的,快一字不落的告诉我,快快快”,路晼晚声音略微有些颤抖,却还不可置信的询问。
“奴婢也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是太妃宫里的景儿,她与御前伺候的小卫子是同乡,是今日景儿去画舫取一副太妃要的画观赏,遇上了同去画舫要画的小卫子,小卫子跟景儿说前儿皇上要画师速速画了九千岁,让他今日来取画。景儿随口问了一句皇上为何突然要九千岁画像,小卫子却说,你守在永和宫居然不知?公主要绝色驸马,皇上便找了”。
路晼晚细细听完,“这么说,只是小道消息真相还未可知是吧”?蝉止点点头又想起什么一样使劲摇了摇头。
“蝉止,你现在立马去御前打听着,把所有听到的消息一字不落的回来说与我听,快去快去,”听着吩咐蝉止应声退下,“诶诶诶回来回来,你不要被人发觉”,看着自家主子一惊一乍的蝉止有些无语却也不敢说什么只得好好去将吩咐的事办妥。
那边蝉止出了门去,看着一旁的嬿归问:“嬿归,你知道这个九千岁吗”?路晼晚其实并没听说过东厂提督其人,只是她意识里东厂绝对不是什么好地儿,方才惊慌确实是先被第一印象唬了,现在稍微镇定一些,要先了解了情况才是。
“独揽大权杀伐决断的九千岁谁不知道,如今的朝堂表面看着是有几位大臣镇着,但是背地里都抵不过九千岁的势力,这是人尽皆知的。”嬿归缓了缓声调,挪了一下姿势,继续说着:“还听说那九千岁相貌堂堂比潘安,武功高强,而且啊,虽然他地位高命号响,也只不过是二十多岁不到三十。”
“才二十多岁就做了总督主啊”路晼晚好奇的问。
“小姐您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九千岁能有今日的权势,全是先帝提拔,不然老爷也不会如此忌惮啊”嬿归小心翼翼的说到。
又自顾自说着突然掩嘴笑了笑,“说来若不是九千岁不近女色,他老人家还挺符合公主选驸马的要求呢”
“不近女色”?
“对啊,”嬿归颔首到,又似乎想到什么立马面若桃红,攀上路晼晚耳边手腕搭在嘴边悄声说:“九千岁非男儿身,怎么近女色啊”
路晼晚听着好没来头,玉手戳了戳丫头脑门,取笑道:“这丫头,什么都懂啊?”一番话羞的嬿归通脸泛红嗔怪道:“小姐大病初愈后,嘴当真是碎了。”
蝉止回来时已是晚膳时分,路晼晚根本没有心思进食,胡乱吃了两口便问着她从前头听到的消息。蝉止说,御前嘴紧,就连前儿的小卫子从画舫回来,也因晚了些时辰被掌事的公公罚去御花园打扫鹿苑了,她没打听出什么倒是老爷来过御书房,许久才离去。
“蝉止,那你可听说过九千岁在宫外纳妾娶妻,或者在宫中有对食”?蝉止摇了摇头说:“这个倒没听说过,只听说九千岁终日忙于政务,只爱弄权没有旁的喜好,人也冷淡多变极难相处。”
听着蝉止如此说,路晼晚心里仿佛噗嗤一声笑开瞬间乌云全散。
“蝉止,你悄悄的再去仔细打听一番,这九千岁从前,如今究竟有没有纳过妾室,有无其他嗜好。一定要仔细,别被发现了”。
东厂
“督主,近日廖乌苑有些动静”,一年轻武士身段男子跪膝参拜道。
“廖乌苑?小皇帝心血来潮封了个小丫头做公主,能有什么动静”?
“这.....”,男子片刻犹豫,低眉思虑神色难为,上座之人见状稍有不悦“嘶”得一声皱眉,年轻男子见此随抱拳道:“督主莫怪,此事实在荒诞,本不想扰了督主,可关系到相府属下实不敢有一丝疏忽。近日属下多方暗中打探,暂无他事,只是,廖乌苑最近一直有人探取督主隐私....”。
“本督能有什么隐私”,那人哼的一声冷笑道
“华阳公主派人打听督主有无妾室,有何喜好等隐晦之事....”说着,男子声音渐弱随低眉不语。
上座人听罢,本阴冷锋俊的面上闪现一丝哭笑不得的诧异,无奈笑道:“她一个未出阁的千金小姐,打听这个做什么”?
“属下不知”。
“先给本督盯紧了,放消息到她耳边,本督从未娶妻纳妾,不近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