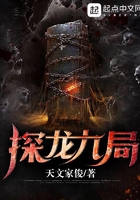是夜。
一抹瘦小的身影疾速在皇宫内院四处流窜,在夜色的掩护下似一道黑影飘过,不留一丝痕迹。
他目标明确的找到一处宫殿,轻轻跃上房顶,爬伏着小心翼翼的拨开一块瓦片,悄悄的朝里望去。
殿内没有任何侍从,皇帝一身明黄色常服站在书桌旁怔怔的盯着着墙上挂着的美人图,画中女子一身狐裘站在雪地中,乌发红唇,仿佛雪地中的一直红梅,粲然一笑,天地都为之失色。他急促的低喘了一声,捂着胸口,苍老的身躯萦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哀寂。
蓦地,他又状似疯癫的大笑起来,直笑得不停咳嗽,苍老的脸上一片通红,带着诡异的狂热,“卿卿,你再等一等,朕马上让她们都来陪你,那些胆敢勾结暗害你的,朕一个都不会放过,她们的那些家族以为向朕施压就能让朕忘了你,哈哈哈哈,朕都记者呢,谁都逃不过,谁都逃不过,都给朕去死,去死......咳咳咳咳......”
“你是不是怪朕让你等太久了?不怕,朕马上就要来陪你了,你且在奈何桥边等一等朕,”他又慌乱的喃喃自语,神情低迷,“朕对你的承诺都记着呢,至死不相负,不不不,不是朕负了你,是后宫那群贱女人,她们嫉妒你,嫉妒我的卿卿,她们都是要给你陪葬的。”
他深深的看了画中女子一眼,渐渐恢复了平静,又成了往日里那个威严深不可测的帝王,苍老的手指在半空中高举了半天,却始终没有胆量轻抚上去,“这几十年间你竟是一次都不愿到我梦中来,卿卿你定是怨我吧,怨我当年没有护住你和孩子,如今,我便让这天下为你作陪。”
叹罢,皇帝小心的吹灭桌上的烛火,大步走了出去,不久便传来宦官尖声呼喊摆驾的声音,一阵躁乱过后,四周又恢复寂静。
黑影依旧是趴在房顶一动不动,仿佛一个雕塑,半响,皇帝果然又悄声返了回来,侍卫四处搜查了一番,回禀并无异常过后,这位狡猾的老人才真正安心的离去。
黑影这才身手矫健的顺着房梁翻进了殿内,在未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摸着黑走到了画中美人目光所对的地方,他仔细的在墙壁上摸索着,果不其然在靠近墙角的地方摸到了一个小小的突起,如不仔细注意,还会以为只是错觉。
顺势按了下去,房内的一个青瓷瓶被机关牵动砸在了地上,黑影怔了怔,反应迅速的打算撤离,殿外却已被闻声赶来的侍卫围的水泄不通,亮晃晃的火把在黑夜中闪耀着,仿佛一头早已蛰伏多时的凶兽,只待猎物闯进来。
......
鹤觅打了个哈欠,泪眼朦胧的看着对面面色不虞的男人,无奈道,“殿下,奴家这都陪您等了一夜了,您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奴家定当万死不辞。”
李懋低垂着眉眼,把玩着手中的玉扳指,目光散落在虚空,神色难辨,“琴师同孤相识也有数月了吧。”
她精神一怔,点了点头,“确有数月。”
“怎得孤突然记起琴师似乎从未惧怕于孤,面见皇姐时也未见惊慌,”他冷冷的看着她,眸中飞快的闪过一丝凶狠,“琴师当真只是如你所言的一介平民?”
“奴家倒也不想只是一介平民,奈何这出身是没法子改变了,又能如何呢。”她不避不让的直视回去,语气淡然,“或者殿下想要换一个更有利的合作伙伴?奴家到底也阻止不得,只不过殿下想要的也就怕是得不到了。”
李懋听完骤然大笑,姿态也恢复了往日的懒散,“孤不过开开玩笑,好奇罢了,琴师何必当真,倘若琴师想走,孤也是不舍得放人啊。”
她站了起来眉眼低垂,似是不快,“主子可别吓奴家了,奴家这胆子一向是小,受不住这般猜忌。”
李懋又是被逗笑了的样子,调侃道,“琴师可是敢同孤的皇姐抢男人,又岂是一般女子,据说前天夏日宴上还有人见到琴师躺在那傅公子的怀中,情意绵绵,当真是好手段,看来孤在此还得提前预祝琴师心愿达成了。”
鹤觅脸上泛起恰到好处的红晕,温婉的嗓音中染上一丝娇羞,“不过是奴家不小心摔倒傅公子帮忙扶了一把罢了......”
“那可不同,”李懋摇了摇头,声音慵懒带着漫不经心的傲慢,“那傅星舒看着良善,实则最为薄凉不过,往年也不乏各色美女往他身上扑,竟是半分不曾沾染,更遑论这般亲密了,琴师可谓是第一人,必然特殊。”
“那主子便可只待奴家的好消息了,奴家这可是牺牲色相为主子想法设法招揽英才,主子可千万好生劝慰劝慰长公主,不要让奴家一片心血付之东流。”言尽于此,她不再多说,只留下剩余的供四皇子自己遐想。
他面色如常,并无太大的反应,只是挥了挥手,“回吧,皇姐心里懂得大事为重的。只希望琴师能信守承诺,不然孤得不到的东西琴师也总该付些责任。”
她恭敬的行了一礼,转身离开。
李懋半躺在榻上,眯着眼睛看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半响低哼了一声,英气的脸庞布满阴鸷,手中把玩的玉扳指应声而碎......
出了楼阁,鹤觅才松了一口气,背后的衣衫被冷汗浸湿,夜风吹过,顿时让她感到背后一阵刺骨的寒冷,打了个哆嗦,她慢悠悠的走进早已等候多时的轿中,细细琢磨着接下来的形势。
六皇子在文臣中赞誉有加,但始终是缺乏兵权的,这是一项致命的弱点,如今的大势也容不得他再前往军中历练积攒威信,前世傅星舒是借了伯安侯府的势从丞相手中撕咬下一块肉来,但付出的代价亦是不小,而后钝刀子磨得丞相不得不反,皇帝也顺势将丞相这方势力彻底斩尽,四皇子也不知为何突然暗害大皇子,行刺皇帝,被发现后流放亳州,在流放途中被手下劫走,再出现时便是伙同蛮族出卖国家。
她揉了揉胀痛的额角,叹了口气,好歹这一世掌握的信息还算多,这局死棋也渐渐被她从旁协助着打开了一道缝。
若无前世最后的记忆,她怕是也要被这一局毫无破绽的棋局给糊弄了,但通过傅星舒后来暗中给她留下的线索,她也总算是知晓了这一切的罪恶,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所作之恶,终有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