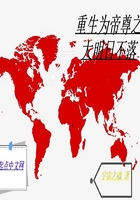二零六年,我和人相约,重游西湖,昔日的酒馆现在变成了奶茶店,我点了一杯香草味的奶茶,坐在木椅上,慢饮,耳边是一首名叫许仙的歌,歌者的声音温润如玉,听得我如醉如梦,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前生。
那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杭州,我的父母顶着收入、住房和供养孩子所带来的经济压力生下了我。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加入了抗金的军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之后我就跟着姐姐和姐夫生活。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没有男孩儿的家庭是很受鄙视的,所以我一生下来就被父母打扮成了男孩儿的模样,并且不准我吃补乳的食物。等我长大后,心理上和男孩儿没有什么差别,生理上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妖。
作为一个人妖,我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和自由。为了维持生计,我在一家药店打工,白天要到山上采药,晚上要跟着药店的师傅学配药,我不喜欢医生这个行业,更讨厌某些药材奇怪的味道,可是现在工作很难找,我又没有文凭,所以尽管日子过得很无聊,我却一直没有辞职。
虽然没有姑娘喜欢我,可是意淫的自由我还是有的,我常常在上山采药的时候偷懒,一个人骑在树上发呆。我希望我的姑娘长得很漂亮还会武功,最重要的是她不可以像我这样遇到一点小挫折小打击就仰望天空泪流满面。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菩萨,也告诉了姐姐,姐姐说是人都会流眼泪,不流眼泪的是妖怪。
采药的时候要在深山密林中行走,遇到毒蛇是常有的事儿,为了安全,我养了一只鸩。我行走的时候,鸩鸟就在我头顶两米高的空中盘旋,一旦有毒蛇出没,鸩鸟就会俯冲下来吞了毒蛇。
有一天早上,我因为贪睡,误了上班的时间,被药店老板狠狠的骂了一顿。我嘴上没有顶撞,心里却很不服气。暗想:你拽什么啊!开个药店有什么了不起的,哼,我以后也要开药店,专门和你抢生意,气死你!
虽然不服气,可吃过早饭,我还是乖乖的带着鸩鸟上山采药去了。到了山上,我故意偷懒,爬到一棵千年古树上,一睡就是半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鸩鸟不在身边。并且听到远处隐约有女人痛苦的呻吟声。
我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一名女子倒在地上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鸩鸟正在撕扯那女子的衣服。我急忙唤回鸩鸟,扶起那女子。女子在我的呼唤下逐渐醒来,可是一看到我头顶的鸩鸟,马上又吓晕了过去。没奈何,我只好让鸩鸟先下山,我背起女子打算带她到山下找大夫医治。可是走着走着,我感觉背上越来越轻,回头一看,却发现自己背着一根木头,仔细一看,正是我要采集的黄连木。当时天色逐渐黯淡,我担心遇到蛇,就放弃了回去寻找那女子的念头,背着黄连木下了山。
一年之中,佛教最大的节日有两天:一是四月初八——佛诞日;二是七月十五日——自恣日。这两天都叫作“佛欢喜日”。我打工的药店的老板信佛,每到佛欢喜日,他都要去金山寺拜佛。金山寺的法海长老和我们老板的关系很好。因为我们老板卖假药,病人吃了我们的药不会好,只好去烧香拜佛保平安,这样一来金山寺的香火就很旺,法海拿了奖金拿分红,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老板去拜佛后,我就得空到西湖玩耍,西湖附近风景很美,常常有貌美如花的良家少女或妇女结伴而行。遇到独自游玩的少女,我就会尾随其后,并不上前搭讪,只要远远的看着,就心满意足了。
有一次,我跟着一个姑娘绕着西湖闲走,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忘了带伞,被淋的好狼狈,这时候,一个看着很面熟的女子走到我身旁,递了把伞给我,然后就走了,我撑着那女子给的伞往家赶,可终究还是跑得慢了点,到家时已经感冒了。感冒后,我去找大夫。大夫看舌苔把脉量体温之后说看不出来我有什么病。可是我明明头痛欲裂双目无神浑身无力还流鼻涕。大夫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仪器,可以给我做一次深入的检查,前提是需要付很高的检查费。我心想保命要紧,就拿两个月的工资付了检查费。检查后,大夫说,原来是感冒了,于是开了点退烧的药给我吃。不曾想我吃了那药,烧得更厉害,烧得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我想,那医生给我开的大概是假药。
在我病危之时,家中来了一个女子,因为她穿着一身白衣服,我就叫她白姑娘。白姑娘喂我吃了点药,我的病就好了。白姑娘说她以前是个兽医,刚在扶桑国的太医院进修完,以后就可以医人了。白姑娘说这年头,人好忽悠,畜生不好忽悠。人病了,你可以让他去检查,肾有病了,你可以先让他去检查肝,化验血化验尿,最后再检查肾。这一趟下来,可以赚很多检查费,虽然这些检查都是没用的,可是病人因为怕死,最后还是得听医生的话。而畜生就不同了,一次两次治不好,人就把畜生杀了,卖肉。这些病畜的肉人吃了之后也会生病,最后还是便宜了医人的医生。
我说:“医生也是人,他们就不会生病么?”
白姑娘说:“他们是医生,懂医理,所以是忽悠不住的。”
我说:“政府难道不管这些么?这些没有良心的医生真该治治了!”
白姑娘说:“是世道不好,现在大家都向钱看,悬壶济世不但会被骂作傻逼,最后还会饿死,毕竟物价都在疯涨,工资却不见涨。”
我叹了口气说:“做地球人可真难,以后我再生病了可怎么办?”
白姑娘说:“我打算在你们这儿开个药铺,问了好几家了,没有合适的房子,我觉得你家这个位置不错,又有几间空房,就进来看看,没想到刚好你病了,就顺便把你的病治好了。如果你能租几间房子给我,以后就不怕生病了,周围的乡亲也会受益。”
我说:“没问题,我以前在药店打过工,你开了药铺,我就给你打杂。”
白姑娘的药铺名叫保和堂,因为她不乱收费,不卖假药,找她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我以前打工的那家药店就没什么生意了。因为老百姓轻易可以看好病,烧香拜佛的人也越来越少。得罪了药店的老板倒没什么,得罪了金山寺的法海麻烦就大了。因为他会法术。
法海约我出来喝酒吃饭,酒至半酣,他对我说,白姑娘是蛇妖。如果我想保命,趁早把房租退给白姑娘,让她走人。
我不相信,说妖怪哪有长这么漂亮的,我还想和她谈恋爱呢。
法海说,你该知道,蛇的克星是鸩鸟,白姑娘租下你家的房子后第一见事就是让你把鸩鸟杀了,这说明她怕鸩鸟,若非蛇类,怎么会怕一只家鸟。你若不信,就趁她不备在酒里放点雄黄,她喝了之后必然会现出原形。
法海的话让我心里有些忐忑,我不愿意相信他的话,却又不能不承认他说得很有道理。白姑娘来得太突然,而且似曾相识,如果我没有认错,她就是那天我上山采药时遇到的受伤的女子,就是那天送伞于我的女子。一连三次,若说是偶遇,多少有些不合逻辑。
回到家中,我没吃晚饭,就躺到了床上,然而并无睡意。
恍惚中,我听到白姑娘的门开了又合上。
次日一早,白姑娘就不见了踪影。
我去了西湖和平时采药的山上,找不到白姑娘,回到家中,看着白姑娘住过的房间如今空空荡荡,她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小时候学堂的先生教我怅然若失这个词,当时不明白,如今体会的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