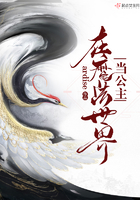从远处的风景而来,那阵阵清风,带着凛冬的温柔跟来春的祝福,只见广阔无垠的大海上,是碧海的颜色,一条雪白的鱼跃出水面,划出一条曲线后钻入海里,直直往更深的海里,就像个孩子把头埋到母亲的胸口一样,总想着自己被包围,总想着就这样不曾离开。
“嘿!快看!”一条渔船上,一个老农夫大声叫着。
海岸上卸货的码头,熙熙攘攘,忙着交易的忙着交易,搬运货物的人继续搬运货物,没有人会为了这么一声没有分量的人说的话而停下自己的生活,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是小白龙啊!”老农夫哭着喊道。
只见原本吵闹的人们,突然没了声响,连呼吸都慢了下来,好像是怕自己多吸了一口气而犯了错误一样。
“让让,让让!”一个衣着华丽的人分开人群,低头做着请的手势,头低的都快碰到膝盖的感觉,在他的引领下,一个留着小羊胡子的中老年人走了出来,“在哪?在哪?小白龙在哪?”语气快的急切。
“谁谁谁?那个谁?喊得快出来!”衣着华丽得人吩咐道,也不知道哪里又抽出一只手来,把别人的凳子挪了过来搬到小羊胡子背后。
“是小人!”老农夫弯腰出来,行了个礼。
小羊胡子一把踢开了凳子,“你弄来干啥?现在都啥时候了,还有坐的空?”并低头附在老农夫的耳边悄悄问:“哪方去了?”
“我瞧着是向着那个方向游了。”老农夫指向了正北方,只见落日的余光铺在那里,像是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一样让人憧憬。
“快去啊!快去啊,开船。”小羊胡子一步子跳上船,“快追啊,快追,抓到了给老爷下酒,你们今年一年的税都可免了。”大家人群里等这句话等了好些时日,一听这么说,立刻从岸边的洞下开出上百条船来,有的是大船,可以容纳两三百个人,有的只是破烂的木船,刚出了海已经散了骨架,只听见两个农夫在海里含着“救命,救命。”
但大家都疯了一样,压根没有人有空去在乎这些。一股脑子百来条船,倒到歪歪,甚至有的还在原地打转。只听见小羊胡子含着:追,追,追,追到了大家发财!
这些人群变得更加疯狂,双眼发红,就像是吸血鬼看到了血液,好色的男人看到了绝世美女一般。
而那条白鱼,快速地游着,鲨鱼跟鲸都给他让路,美人鱼给它送了一个飞吻,大虾跟贝壳为了它敲出水波,只看见一个水下的宫殿,屋檐之上,小白鱼游过。它从一个深秋的河岸出发,海上已经慢慢结了冰,越来越厚,直到它再也看不见太阳的光。
它就这么一直游,一直游……
只听到“呮”的一声,冰上有什么在用什么利器在试图划开冰,随后伴着“哗”的一声,一只白色长满毛的爪子一把抓住了白鱼,从那个冰洞中掏了出来,一把塞到了嘴巴里。仔细一看是一只大白熊正在捕食,两三口吃了下去,看到洞口又有白鱼游过,再伸了下去,一把抓起两三条白鱼来。把视角往上拉,可以看见海上的冰面下,一大群白鱼游过,好多熊都在捕食。而这里早就离开了那个海岸不知道多少远,只见白雪皑皑,再也看不到边际。
“小白!”一个小男孩喊。
只见一只白熊把鱼塞进了嘴巴后,咀嚼都没有咀嚼地开始往小男孩那里跑去。
“小白!你在哪?”小男孩喊着。
白熊跑地更加的快了,在看到小男孩后直接扑了上去,舔了舔小男孩的脸,从嘴巴里掉出那条白鱼来。“哈哈哈哈”小男孩抱着白熊嬉闹起来。
而后小男孩爬到白熊的背上,白熊叼起了白鱼,开始往家里走,只看见不远处冰雕的房子,早已经升起了炊烟。
走着走着,白熊踢到什么似的,停了下来,用右爪扒了扒小雪丘,慢慢露出一个穿着衣服的打着大辫子的人,白熊把她一翻,一张清秀的脸蛋呈现在他们面前。“小白,这是谁啊?”男孩子在白熊背上问。
白熊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人,没有发出声,小男孩见如此就从它背上滑了下来,跪了下来,摸了摸她的额头,滚烫!将手指放在她的鼻子处,还有呼吸。小男孩一把抱起了这个看起来六七岁的姑娘,将她放到白熊背上,脱下自己白绒的厚外套给她盖上,自己也爬了上去,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到了家门口,小男孩打开了们,白熊背着小姑娘走了进去,房子里面倒是很大,完全有两三层楼高,白熊走到壁炉那里趴着,背上的小姑娘在白熊身上盖着外套,烤着火。
“妈,妈,来了个新人。”小男孩喊。
“你这个家伙怎么去了那么久,谁都烧开了,是不是不想吃饭了?”说着从厨房走出来一个穿着灰色布料的大娘,身材倒是有些雄伟,但是两条眉毛又可以看出是个善良和蔼的人。
“不是啦,你来看看,这个女的在路边晕倒了,我给她弄回来了,只是头很烫,你快来瞧瞧。”小男孩拉着母亲走到了壁炉这边,“好嘞,让我看看我家宝贝给我找了个什么样的儿媳妇!”母亲一边取笑着小男孩,一边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确实滚烫,“申屠泽,你把锅里的水弄一些来,我给她擦洗一下。”
申屠泽听母亲这么一说,脸早就红着待在角落里,满脸通红,一动不动,啥也没听进去。
“申屠泽,你再不去弄,我就揍你了,知道么?”母亲的声音更加大了。申屠泽一听要被揍,立刻去弄了一盆开水来,并给弄好帘子,母亲给小姑娘脱掉了衣服,用温水擦洗了身体,把申屠泽干净的衣服给她换上,放到床上,头上温水毛巾敷着,在从白熊躺着的地方拿了白鱼,给她熬了白鱼汤,慢慢一点点给她喂了下去。女孩子就那么散着头发,睡着,发烧的额头慢慢降了温度,她就这么躺在这个平凡的母亲怀里,而申屠泽就在隔壁的自己被窝里,梦里梦见那个姑娘跟他说:那我以后就是你的妻子了。
“不,不是,我救你只是我遇到你才,才……不是因为这个啦。”申屠泽的脸倒是滚烫了起来,把被子一拉过头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