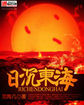白泽细心地擦了擦玉佩,把它放进书架上面的红木锦盒中,那锦盒中,还陈放着另一块刻着雕像的半边玉佩。
两块玉佩放在一起,完美吻合住了,他小心翼翼的抚摸着玉佩,眼神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安详。
他挪动着玉手,旁边再摆放些书籍,严实地把锦盒遮住,好像隐藏自己深处的秘密一样。
听到她质问自己的声音,便向她这边走过来,步履轻快。
硕长的身影挡在她的身前,他的双手很自然的搭在她的秀肩上,用十分温柔的语气对她说道:“因为你很像她。”
她的眼光停滞在他身上,有过瞬间的彷徨。
“是因为我的面貌和白老师玉佩上画那位女子很相似嘛,看来她在老师心目中的位置非同一般。”
她的心情忽然有些低落起来,原来白老师一直对自己好,让自己变成他的特例,是那位和自己长得很像女子的缘故。
“他是我的妻子,也是我唯一爱着的女子。”
栀樆听到这句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从肩头传来他手心炙热的温度,连同他掌心的温度,一起卷入她的肺腑。
“白老师年纪轻轻,就有了家室,真令人羡慕,”她试图推开他搭在自己肩上的手,似乎觉得他一个有妇之夫不应该随便和一个女生有亲密的举动。
包括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动作。
白泽感受到他的反抗,他一反常态,仍由她有些小动作,双手却不打算放开她。
“她死了,我成了孤家寡人。”
他轻描淡写的说出这一句话,眼里却满是忧伤,似乎,提及到了他不愿意回忆的往事。
“啊...对不起...我其实...”
她听到他的妻子死去的消息,心中一震,顿时觉得刚刚自己不该多问他些什么。让他突然回忆起这件事情来,她觉得自己有莫大的罪恶感。
她赶忙道歉,想转移话题,以至于不让他继续悲伤下去。可是,正当她还想要说些什么,白泽洁白如玉的手忽然上移,轻抚过她光滑的脖颈,蹭着她水嫩嫩的肌肤,攀上她清秀的脸颊,最终,他食指指腹停留在她柔软的唇瓣上。
他细微的动作,令她身子一颤。
她本能的想避开,可他却命令似的吐出两个字,别动。
这两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到底威压多大了?空气中凌冽着透骨的寒气,只见桌上盛水的马克杯在颤动,溅出一些水来。
“我来取样重要的东西,取完我就离开。”
此时,天地静止,房间里死一般的沉寂,她喉咙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她想要逃走,却发现她的身体无法动弹。
他另一只抚上她的面颊,像是在欣赏一件绝世的雕刻品,小心翼翼的描绘着她的轮廓,青睐着她一寸又一寸的肌肤。
忽然,他一只手移到她的后脑勺之处,俯身,那惊世骇俗的容颜便凑到她的眼前。她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的看着面前他放大的面孔。
只见他的唇落在他食指之上,与她的唇,只有一指之隔。
随即,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抽走了横在他们之间的手指。
在她放大的瞳孔中,与她两唇相接。
原来,他要取得东西,就是自己的初吻。
她内心仿佛掀起一阵****,脑海中浮现出电视剧中男女主接吻的场景。但是她从未想象过自己和别的男子亲吻的画面,在她的认知中,还未有男女之情,也不知道是什么。
栀樆觉得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
于是她通过喉咙的震动,试图发出一些声音来,可是这些声音经过唇齿的摩擦,早已经融化在那个淡淡的吻里。
他却趁着她发声的时候,一举攻入她的深处,与她的皓齿摩擦,寻找她的香舌,不停的试探它,试图使它敏感起来,引导它和自己缠绵。
难堪之情在她脸上浮现出来,她越是回避,白泽就进攻的越厉害,她只有不反抗,安静的让他索取,并祈祷着这一切快点过去,她想要醒过来。
她觉得这就是一场梦,这样荒唐的场景只有梦里会出现。
他似乎感受到她的妥协,意识到她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丫头。虽然,在他那个世界,这是女子可以谈婚论嫁的一个年纪,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她还只是个无助的孩子。
白泽的唇带着一丝的眷恋离开了她,空气中还有留存有银色的藕丝...
他替她擦了擦嘴,指腹来回抚摸着他被吻得红通通的嘴唇,颇有些得意。
随后,天地回复原来的样子,她可以动弹了,也可以说话了。
“白老师,你怎么可以...”她的眼中夹杂着一滴委屈的泪水,为什么,他明明有妻子,有喜欢的女子,还要这样轻薄她,她实在不懂,他究竟把她当什么对待。
“今天是她的忌日,每年的这一天,我都有些反常,今日误伤到你,抱歉。”他的眼中又恢复往日的真诚,令她有些疑惑,到底怎样的样子才是他真是的模样。
她之所以和他亲近,是因为他能够触及到她内心最柔软之处,同时,他也能够伤害到她的柔软之处。她不知道,他的到来,到底是过来解救自己,还是把自己推向深渊。
罢了,大抵她是另一个人的替代品,他不喜欢自己便是。
“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这里有些闷,白老师,我得去其他的地方检查作业,先走一步。”她很快的离开他的身,抱起桌上那一沓试卷就往门外走。
“栀樆,”他叫住了她,她有些踌躇,但还是转过身来,猜想他要说些什么挽留的话,他说,再见,他对她说了再见的话语。
她闷哼一声,飞快的跑出了办公室。
看着她有些单薄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在她来办公室之前,故意把玉佩,夹杂在她可能需要用到的历史书中...
她在教学楼的走廊外不断的穿行,正好遇到了鸢年。鸢年看出她的不悦,以为她是被谁欺负了,上前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抱着一坨历史试卷,停在那里。
眼神空洞,一言不发。
他看着她怀中的历史试卷,闻到她身上散发的异香,是那个人独有的清香。他虽然没被他教过,但是偶尔经过他的身边,闻到过他身上的香气。
鸢年很确信他是让栀樆变成这样子的,不禁握紧拳头,从她身边冲了出去。
后来,栀樆也很少去白泽办公室问问题,有什么问题她能从书本上找到的答案就自己私底下解决,实在不行,厚着脸皮在班上去问他这些问题。
唯唯诺诺,不像是她的作风。
白泽还是像以前那样,耐心的解决他的问题,保持着对她独有的关心,只是,很难再得到她的回应。
他只字不提那时发生的事情,那样的泰然处之,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再后来,听说白老师在办公室里被突然闯进的男生打了。还听说,那男生,曾经多次在办公室恐吓他,只不过这次,一时冲动,下了狠手。
即使,她不愿相信那个殴打老师的男生是自己的弟弟,鸢年。
那天,鸢年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接受了学校给的处分,回来时还故意在她面前说着,那人被打的有多惨,自己是怎么帮栀樆出了这口恶气的。
她不愿听到他受伤的消息,更不愿违背自己内心,在鸢年面前装作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
她终是忍不住想着,他没有外人看起来的那样脆弱,怎么做到心甘情愿被打的,没人知道那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只是没过多久,白泽便辞职了,论谁劝说也不肯留下。
清理办公室的时候,他整理出很多历史文学书籍,以及自己写了满满知识点的历史书,全都托人给栀樆送去。
踏出办公室那一步时,他转过头,留恋的看了看这个房间。这里曾闪烁过她动人的身影,这里曾有两人亲近的气息,这里曾发生过令人难忘的故事...
往事易回首,却已变了味。
他来的时候,轰轰烈烈,走的时候,依旧带走了很多人的心,听说,不少女老师因为他的辞职而含恨数日,上课也是魂不守舍的。
有人说,他是因为被打了,老师的尊严被践踏,一起之下就走了。又有人说,他是因为觉得在这里教学限制了他的才华,所以去了别的地方谋取发展...
众说芸芸,她不知道她到底该听信那种说法。
总之,他离开了这个学校,她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回到座位,只觉得胃里翻涌,很不是滋味。听着隔壁班历史老师暂代这几周的课,觉得索然无味,忽而猛地翻动着他托人送过来的历史书,一角白色的纸张从里面显露出来。
她扯出那张纸,发现在那巴掌大的纸上,有位女子的画像,纸上的女子,不是玉佩上的女子,正是眼前笨拙的自己。透过纸张,她隐约的看到了他留下的字印。
她摊开纸张的反面,看到那串再熟悉不过的字迹,上面写着:海底月是天上月
栀樆反复念着他留下来的诗句,突然想到自己曾在诗集上读过的句子: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
她铮铮的看着讲台上站着的老师,却已不是他。脑海中回忆起他悉心给自己讲解题目的画面,泪眼朦胧中,他那时说过的话,越发的清晰起来。
“我来取样重要的东西,取完我就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