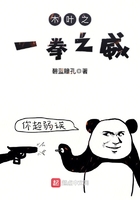在小郑大人的事被揭发之后,郑家反了,联合了齐国残党,意图叛乱。因为郑家的事,夫芫的葬仪办得并不宏大,不全是按着贵妃的规制来的,去吊唁的人几乎没有。韫姜病重难以动身,只得托愈宁亲自去了一趟,聊表心意。
夫芫病逝,韫姜这边也并不好过,她的病多半是心力交瘁所致,现在越发郁结,病就越发难治了。和如命几乎夜不能寐,日日夜夜守着,不断调整药方、亲自煎药,可惜韫姜的身子还是没有起色。
其实和如命和华惠允心里都是有数的,韫姜的身子本就孱弱,后来许多沉疴旧疾,积重难返,能熬到现在都属实是不错的了。
?诗她们轮番来侍疾,再阳也不顾伤势,每日坚持过来给韫姜请安,恳求她宽解心情,能够大安起来。徽延在宫外听得了消息,心痛之余,无能为力,只得借裴王妃,送来丰厚的礼还有问候。可惜力不从心,韫姜的病是“天命难违”,就算能好,命数也就这么些了。
后来尚宫局、内侍监的人轮番来了两趟,韫姜才知道徽予封了她为皇贵妃。皇贵妃的寓意,韫姜心里知道,这既是徽予的心意,一边也是冲喜之举。但韫姜身子羸弱,难以举行册封之礼,亦无法承担协理六宫之权。
因盛妃将事一股脑推到恪贵妃身上,洗净了自身过往的算计,徽予便复了她的淑妃之位和协理六宫之权,由她全权处理六宫之事。
这一日,韫姜忽觉涌上了一股力气,整个人也清明起来,正巧是?诗、黛笙守在一旁侍疾,便小心翼翼地扶她起来坐坐。愈宁见韫姜略有好转之势,原本十分高兴,可转念一想,生怕是回光返照,笑容便衰减了好些。
韫姜把药吃了,虚弱地问?诗:“现在宫里是淑妃管事么?”
?诗此时已被晋为了贵嫔,偶尔会协助淑妃些,她为难地答了:“是,有些下作的宫人说,这后位兜兜转转,总归会是淑妃的。”
“呵,是啊。”韫姜一哂,“等我一死,后位对她而言岂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吗?她最近得意坏了吧?”
“说什么得意……”?诗唉声叹气,“确实挺风光的就是了,惇恪贵妃娘娘一薨,加上淑妃得意,就已经有些姊妹开始去巴结淑妃了。不过姨母放心,不管是婧姐姐、晴妃姐姐、庆妹妹、兰妹妹还有我,都是一心一意向着姨母您的。哪怕将来……也绝不顺从于淑妃娘娘。”
韫姜仰面看着架子床上纷繁的雕纹,眼前一阵晕眩,看来自己是真的快不行了。
她讥笑一下,盛挽蕴真是难缠,事到如今竟然输了个大半,如果她没有徽予的爱护,估计就要全然败在盛挽蕴脚下了。
盛挽蕴她厉害就厉害在坚不可摧的意志,可是这看似坚不可摧的毅力,也是最易碎的。
韫姜拉着?诗的手,冷笑道:“本宫不会要她好过的,本宫大不了拿命去与她争这最后一仗,反正本宫也活不久了。——真是好笑,竟然只有这样才能把盛挽蕴拖下水,太可悲了。”
?诗面带愁容:“姨母不要说这样的话,姨母您会好的。”
黛笙掖了掖眼角的泪,凄哽道:“娘娘,您若有什么吩咐,自管说,嫔妾等必定尽力而为。”黛笙是个看得清的,她知道再说些宽慰之语也是无用了,索性放开些。
韫姜赞许地点点头:“你是个明白人,确有一事要你去做,不过是委屈你了。”
“娘娘不要说这样见外的话,娘娘的恩情,嫔妾铭记在心,为娘娘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虽说当下宫内位份最高的是皇贵妃娘娘,但一应实权都落在盛挽蕴手里,合宫拜见也便都去钟粹宫。淑妃虽然矮了韫姜一头,但谁不知道现在宫里最该巴结的就是这淑妃娘娘了?
盛挽蕴隐忍了这么久,就等的是这一刻,只要傅韫姜一死,满宫里就没有人配做她的对手,中宫皇后也就是她的囊中之物了。这一回,没人会再阻碍她,她会是真正的六宫之主。
但盛挽蕴也把事看得明白,傅韫姜这么一死,就永远会是徽予心里的记挂与思念,与傅韫姜情好的?诗等人,只怕会借着这股东风,聚成一股势力与她抗衡。她势必要培植起自己的力量,把徽予的这份意难平为自己所用才行。
当下现成的就是昭充华郎绮妘,还有佟黛笙,只要把她们拢入自己麾下,紧紧攥着、调-教好了,不怕拢不住徽予的心。昭充华自是不必费心,就是佟黛笙还一心想着傅韫姜,着实难为些,不过这也更好了,同傅韫姜走得近、还同傅韫姜相似,岂不比那桀骜的昭充华更妙?
因而,每每晨昏定省,淑妃都不遗余力地亲近佟黛笙,这日合宫请安,淑妃照例问候了一句佟黛笙。佟黛笙一反常态,亲热地回应了淑妃,且若有若无地递给了自己一个眼神,淑妃立时会意,叫散去后,独独把佟黛笙留了下来。
她亲密地叫黛笙入次间来坐,又上了果子点心,叫她不必拘谨。黛笙告了谢,恭顺地低着头:“多谢淑妃娘娘,从前是妾身不懂事,辜负了娘娘的好心,如今特地要赔罪的。”
淑妃暗中打量了黛笙一番,还是有些警觉的:“妹妹此话怎讲?我们一家姊妹的,说什么见外的话?别再说这赔罪不赔罪的事了。”
黛笙微微笑:“说一句僭越的话,妾身此生算是有福,能神似皇贵妃娘娘,还因此蒙受了圣宠,也算是妾身一辈子的造化了。且说近来皇贵妃娘娘病重,皇上牵念皇贵妃娘娘,妾身借了东风,也颇得皇上关照。”
这一点倒是不假,自打韫姜病重之后,徽予若来后宫,便都是去未央宫,要么就是黛笙那了。淑妃心里的疑虑略打消了些,但仍旧是不动声色的,听黛笙继续说下去。
“昨夜皇上来了妾身这儿略坐坐,看着妾身,也不知怎的,却说想要册封皇贵妃娘娘为皇后的话来。”
淑妃温婉轻柔的神情不易察觉地一惊变,但很快平淡下去,就算封了也不要紧,傅韫姜也活不了多久了,碍不了她的事的。她微微笑:“是好事啊,皇贵妃姐姐值得上皇后之位。”
“是了,皇上的意思多半是为了给皇贵妃娘娘冲喜的。”黛笙一捋丝帕,水灵灵的眼睛一抬,凝望着淑妃,“这话也就罢了,要紧的是后头一句。皇上说这几年不安生,也是因为后宫没个主心骨的缘故,所以闹得厉害了。所以,皇上预备着等皇贵妃娘娘薨逝之后,立淑妃娘娘您为皇后。”黛笙的声音很细微,仿佛只敢说给淑妃听,“妾身惶恐,想必是皇上见着妾身,想到皇贵妃娘娘,才掏心窝子说这样的话的。妾身有私心,来日不求荣华,只想要同妾身的孩儿一起平安过日子。所以今日特来告诉淑妃娘娘,只求淑妃娘娘来日能护妾身和衡儿万全。”
淑妃心内一喜,表面上还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温婉如水:“这话是怎么说,就算本宫来日不是皇后,也必定保你和再衡完全的,你且安心就是了。”有了上回的教训,她这次不敢贸然沾沾自喜,但一旦种下了这颗种子,她就越发满心期盼起来。
她现在离皇后之位,才是真真正正的一步之遥,触手可得,她亲亲热热地招待了黛笙,压抑着心内的狂喜,她终于快要成为皇后了,不枉她算计这么多年。
郑家事忙,徽予还是坚持每晚抽空出来看一看韫姜。这一夜,徽予过来时,才知道韫姜竟是清醒的,徽予喜出望外,问愈宁韫姜是不是好多了,愈宁不敢随意答,犹豫了许久,才哀声道:“今儿,华太医说娘娘大概过不了年节了……”
言下之意,这是回光返照,谁都明白。和如命不肯说,也不肯面对,但华惠允什么都知道,簪桃也哭着说,娘娘不爱听虚伪之词,不若敞开了说。与其给他们虚妄的期待,不如直截了当说明了,还能好好地珍惜这剩下的日子。
徽予站在屏风外,手脚冰寒,觉得今年的秋天格外的冷、格外的凄凉。愈宁忍着泪,沉默地陪在一旁,心内亦有苦楚在不断翻涌。
好久好久,徽予才提步朝里走去,韫姜正靠在垫起的被褥上,听见徽予轻巧的脚步声,微笑着转过头来:“予郎来了。”
徽予一下子停了脚步,呆呆地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殿内的人都乖觉地退了下去,徒留一屋的阒静。
韫姜狠狠忍住眼泪,歪着头问:“予郎怎么不过来?”
他没有回应,只是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过来,他道:“郑家的事处理得快差不多了,他们准备得并不充分,加上朕早有准备,一切了结得很快。郑家的事全部结束之后,朕就能天天在这儿陪你了。”
“好。”韫姜任由徽予握住自己的手,徽予的手是冰凉的,无力的,两相无言片刻,韫姜才缓缓开口,“你封了我做皇贵妃,皇贵妃从来都是皇帝的心上之人,否则不配这皇贵妃之位。”
“皇贵妃又算得了什么。”徽予苦涩地牵动了一下嘴角,“在我心里,你是我的妻子,皇后之位才配得上你。”
韫姜点点头:“生同衾,死同穴。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徽予愕然抬起头:“你肯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答应我。”韫姜抱住徽予,头轻柔靠着他的肩头,“从此以后,只有我这一个皇后,只有我这一个妻子。告诉她们,你爱我,你只爱我一个人。”韫姜心里涌出一股愧疚来,她利用了徽予对她的爱。她也知道,这样无理而任性的要求,徽予是会思虑再三的,只有她快死了,徽予才会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她对不住徽予。
不过也真是可笑,竟然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了结盛挽蕴。岂止是夫芫输了,韫姜也输了。
“好、好,我全都答应你,你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徽予紧紧抱住韫姜,快要落下泪来,“你别走……”现在的徽予,什么都能答应韫姜,只要韫姜高兴,他几乎没什么不能给的。
韫姜吃力地抬起手,捧着徽予的脸:“七日之后就是我的生辰了,我想再看一看烟火,好吗?哪怕只有一会儿,也好。”
徽予的心里在撕心裂肺地疼着,他一味地点头,生怕一动嘴,眼泪也会止不住地掉下来,他不想韫姜难过,也不想她难舍难分地离去。
十月廿日是韫姜的生辰,因在秋时,韫姜很多时候都是抱病的,所以她的生辰并不每年都办得热烈。
何况有过韫姜十五岁及笄的那一场的芳诞宴,其余的也不过都是相形见绌罢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韫姜永远记得那一夜的花火,之后无尽的黑暗她也无所畏惧,只要想起那一夜绚丽的天空,她就能在漆黑之中寻找到一丝光亮。
这明城不全是勾心斗角、也不全是暗无天日,有徽予在,韫姜就不会找不到希冀。
十月二十日那天,徽予如约送了韫姜一夜天的烟火。韫姜身弱不能外出,便在明堂洞开大门,徽予拥着她,陪她看天外的花火,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月似悬。
花火是转瞬即逝的,可韫姜同徽予的感情却日久弥坚,这是韫姜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嫁入明城,被桎梏在这儿是不幸而悲哀的,这里的女孩儿,都被推着走进泥淖,不断地争抢、算计,甚至迷失自我。但韫姜一想到,还有徽予对她的爱,就觉得自己是不幸中的万幸,嫁入明城也成了一件幸运的事。
她躺在徽予的怀里,裹着温暖厚重的大氅,可以闻到烟火过后硝烟的味道,一切都那样美好,现在想一想,她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她舍不得未央宫满架的紫藤萝,舍不得再枫与再阳,舍不得?诗她们,更舍不得徽予,她若走了,徽予该多孤独啊?
与未央宫的风景截然相反,熙正殿的气氛格外浓重。徽予许诺韫姜的事,不会耽搁,封后的旨意、再不立后的誓言,在答应韫姜的第二日就晓谕六宫了,没有一点拖延。他要韫姜临走前知道他全身心的爱。
可是盛挽蕴终其一生的梦就这样破灭了,仅仅那一句话,全都破灭了。她的欢喜、她的期待,一刹那归于虚无,再不立后。她抓住传话的君悦,问了三遍,仍不可置信。
她明明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婵杏噙着泪扶住她,看着整个失魂落魄的盛挽蕴,凄声道:“娘娘,是再不立后。娘娘,您别问了。”确定无疑了,金口玉言,再也不会改变了。
盛挽蕴一身的光芒仿佛在那一瞬间被剥尽了。
今夜的花火虽说是只送给韫姜一人的,但很多嫔御也都会站在自己的院子里观看,这宠爱是独属于韫姜的,但花火的瞬美,是可以彼此分享的。
婵杏扶着失神的盛挽蕴,小声道:“娘娘,今儿皇上放了焰火,特别美,您也去瞧一瞧吧。您别再伤心了,就算做不了皇后娘娘,从此以后您还是宫里最受人敬服的淑妃娘娘,没人能越过你去。没有皇后之名,也有皇后之实啊。”
盛挽蕴两眼呆滞,安神香袅袅的香气也无法抚慰她崩溃的神经。那丝丝缕缕的烟雾,仿佛像蜘蛛的丝线,把她缠绕在一起,逼得她几乎疯狂。
她整个人瑟缩在一起,想要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可是越想冷静,就越是疯狂,她摇着头“不、不、不,我要当皇后,只有当了皇后、我才能实现母亲和父亲的愿望,我才能给盛家带来荣光。我只能当皇后、不、不。”她捂着耳朵,不肯去听焰火噼里啪啦的声音,“贱人!贱人!贱人!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婵杏紧紧抱着失了神志似的盛挽蕴,哭个不住:“娘娘!娘娘!您别这样!”她一直都知道皇后是盛挽蕴的执念,但不想到她偏执至深,竟然会达到这样的地步。
盛挽蕴这一辈子就为了“皇后”二字而活,不论是忍气吞声,还是韬光养晦,不论是低声下气、伏小做低,还是谋求算计,全都是为了“皇后”。盛挽蕴不像恪贵妃那样,皇后只是一种象征,若是做不到,恪贵妃也不会怎样。
她截然不同,皇后对她而言意味着一切,乃至她的儿子,都是她爬上皇后之位的垫脚石。没有人比她更渴望皇后,年幼时日积月累地叮咛和期盼,她自己对自己的寄望,以及盛家的窘境,生生把她逼入了绝境。
“娘娘,兰嫔求见。”宫女小心翼翼地站在碧纱橱外,小声地通报,生怕触怒了最近喜怒无常、形同疯癫的淑妃。那宫女心里暗中腹诽,若不是皇上一心扑在皇后身上,早该来收拾淑妃了,她也不至于受这个气和惊吓。
婵杏才想说不见,却见黛笙旁若无人地走进来了,她一身浅藤紫的滚绣衣衫,若不细瞧,婵杏还误以为是韫姜过来了。她心中一惊,翻身-下榻过来给黛笙请安,黛笙微笑:“你先下去吧,本嫔同淑妃娘娘说说话。”
婵杏讪笑了一下,岿然不动:“我家娘娘玉-体不适,须得奴婢从旁照料。”
黛笙睨她一眼,没有往常的温驯可人,反倒十分盛气凌人:“本嫔叫你下去,你一个奴婢多什么嘴?有什么事本嫔自然叫你。”
婵杏一个恍神,未曾料到黛笙竟有这个胆气,未等她反驳,顾诚一个箭步自后上来,捂住了她的嘴,朝她后脖颈一击,婵杏就昏厥了去。
黛笙自顾自进来,选了一个离淑妃很近的位子坐了。淑妃眯眼看了她半响:“佟黛笙?不、你是傅韫姜……?”
“现在本宫是皇后,你怎可直呼本宫姓名?”果如韫姜所料,淑妃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一面是她原本就心志动摇,另一面淑妃自己方寸大乱,防备之心弱下来,韫姜便趁机命人暗中下了点药石,催发了她的疯症。
“你是傅韫姜?皇后?皇后?不……”盛挽蕴脑中一团乱麻,整个人不受控似的胡言乱语起来,“你怎么会过来?你不是快死了吗?”
“怎样?现在本宫是皇后,而你一辈子也坐不上这个凤位了。”黛笙模仿着韫姜的神态,娓娓道来。她本就是被刻意调-教过的,有韫姜七八分影子,淑妃一时神智混乱,越发不能分辨,便误以为真就是韫姜坐在她跟前。
她凄厉道:“你胡说!这满宫里,除了本宫,还有谁能胜任皇后之位?郑夫芫已经死了,你也活不了多久!等你一闭眼,这后位,本宫唾手可得。那些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片子,谁能是我的对手?”
“你怕是疯魔了,皇上亲口答应本宫的,除本宫之外再不封皇后,你这辈子无缘后位了,来世投个好胎吧。”黛笙睥睨向淑妃,毫不留情。
“是你?”淑妃瞪大了眼睛,“是你报复我?是不是你报复我?!”
“你做了这么多事,害了再勋,也伤及了无辜的白氏,更逼死了郑姐姐。你做出这些事,就该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本宫是要死了没错,临死之前,这新仇旧恨我们盘算盘算。你不是最想当皇后吗?本宫偏偏不要你如意!”黛笙回忆起韫姜说这些话的神情,只觉得句句泣血,字字是血泪。
淑妃跌下长榻:“你这个女人!你这个贱人!”
黛笙躲开扑身过来的淑妃,狠狠道:“你好自为之吧?这份礼,本宫送给你的,你好好珍惜吧,淑妃娘娘!”
她背后传来凄厉的尖叫,淑妃匍匐在地,又哭又嚎,已经几近崩溃。
“皇上。”江鹤悄无声息地过来打了个千儿,“禧贵嫔娘娘来报,说淑妃娘娘的病症更重了些,简直到了言行无状的地步。这也罢了,她、她还口中咒骂皇后娘娘,要皇后娘娘不得好死。”
徽予将手中的奏折一放,剑眉不自觉皱了起来。江鹤觑了徽予一眼,故意说:“当时君悦将皇上的旨意晓谕六宫,到了熙正殿,淑妃娘娘听完之后,就有些异样了。君悦说淑妃娘娘扯着他,足足问了三遍,似乎大为不满。那之后,淑妃娘娘就病了。不过禧贵嫔娘娘安排太医去医治了,这样的事也不敢拿来烦皇上的心。只是现在,淑妃娘娘犯上不敬,不敢隐瞒,才通报了一句。”
一下静默了片刻,徽予才说:“把昭充仪请去熙正殿偏殿。”他一面说着,一面起身往外去,“摆驾熙正殿。”
到熙正殿时,里头意外的一阵静谧,徽予不待宫人请安,就提步往里去。原来盛挽蕴吃了药,才睡下了。婵杏见徽予过来,喜出望外,刚想过来请安,徽予却冷声道:“把淑妃叫起来。”
“皇、皇上……淑妃娘娘才睡下了。”婵杏不可置信,但又不敢肆意违抗徽予。
徽予不耐烦地一挥手,君悦和江鹤立时上来,一个控住婵杏,把她拖拽下去,另一个则同安姑姑一起唤醒淑妃。
徽予在霄华搬来的椅子上坐了,等淑妃茫然醒转后,才一挥手:“都下去吧,婵杏好好查问,旁的人,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办。”
淑妃醒来时见徽予在旁,一时是惊喜的,但耳闻了此话,一下又错愕起来:“皇上?”
徽予的眼珠子冰冷得像一轮宝珠,无情地盯着淑妃:“夫芫走了,姜儿病了,朕想着现在满宫里,只有你有统领六宫的能耐,所以饶你一马,没有戳破那些伎俩,更没有追究你们泼在夫芫上的脏水。你就该感恩戴德,乖乖地当你的淑妃,为朕处理好六宫的事宜。但你真是叫朕失望透顶,白白辜负了朕的宽仁!还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这觊觎后位的心,真是一点没变,还胆敢出言不逊,诅咒皇后。”
盛挽蕴颓倒在床上,难以置信:“什么……”
“你同昭充仪的把戏,以为朕真不知道,能被你们蒙在鼓里么?自作聪明!”徽予想起病逝的夫芫,更是痛心,“夫芫是什么人,她会安排白氏的事吗?!朕隐忍不发,你就该好自为之,现如今你成了什么样子!”
“皇上,您夸赞臣妾了。”盛挽蕴疯疯癫癫地笑了,完全不顾徽予的责骂,“对,皇上,满宫里只有臣妾能统领六宫,臣妾才应该是皇后!皇上!臣妾才应该是皇后啊!”她翻滚下床来,爬向徽予,紧紧攥住徽予的衣袍,不跟松手,“皇上、皇上,求您收回成命啊!臣妾应该是皇后的!您不要信傅韫姜那个贱人说的话,她就是要报复我!她就是……”
“闭嘴!”徽予听到她谩骂韫姜,一下怒气上涌,“你也配叫姜儿的名字吗!”他看着盛挽蕴疯癫的样子,蹙眉嫌恶道,“你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徽予半俯下-身:“就算朕曾经想过封你为皇后,但现在朕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句,你不配。”他忽而一笑,一推桌上的一盏茶,“这是一盏鸩酒,你若喝下去,朕立时追封你为皇后,大赏盛家,你喝么?”
盛挽蕴呆了一下,竟毫无犹豫,一把抓起那茶盏,一气喝下去,口中仍笑着:“皇上一诺千金啊!”
徽予一脸嫌恶,已经到了不想同她多费舌一句的地步:“你真是疯了。”他路过君悦,使了一个眼神,君悦立刻会意,缓缓走进了寝殿。
彼时,郎绮妘正百般疑惑地坐在偏殿的圆凳上,徽予悄无声息地进来,借着窗外的光芒,能看到郎绮妘的侧脸。
她是真的像韫姜,性子却活像是夫芫。所以徽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追究她攀诬夫芫的罪过。她太像韫姜了,让害怕韫姜薨逝和对夫芫心怀歉疚的徽予舍不得处置郎绮妘。
但徽予也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会发作起来,韫姜请求他再不立后的时候,他就都明白了。韫姜想要把盛挽蕴逼进绝路,想要还夫芫一个公道,也想要了结自己最后的忧虑。
那徽予就顺韫姜的心,反正她不喜欢的人,没一个是无辜的。他只不过再也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纵容了而已。也是好事。
郎绮妘注意到了门口的徽予,心内一慌,表面上还是带着笑过来请了安:“皇上怎么叫妾身等在这儿?”
徽予眯着眼打量着郎绮妘,伸手抚上郎绮妘的脸,留恋地摩挲着:“朕是真舍不得你,可惜你辜负了朕的美意。”
郎绮妘浑身一震,美目不自觉瞪大了,被这诡秘的氛围吓得打怵:“皇上——”
“好端端的,为什么攀诬夫芫?”徽予用很温柔的口气与郎绮妘说话,“真是可惜了你这张脸。”
郎绮妘抿紧了朱唇,仿佛遭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她的眼是血红的,彼此沉默了良久。
她仿佛没有惧意似的看向徽予:“因为郑夫芫还有整个郑家都拿我当玩意儿,我本是孤女,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我的一生。是否荣华富贵、是否平安顺遂,我都可以做主。但是他们未雨绸缪,把我当玩意儿似的送进宫来,当傅韫姜的替代品。连你喜欢我,也不过是因为我这张脸而已。那我到底是谁?”
徽予一蹙眉,郎绮妘尚未回神,就被一掌掴倒在地,她倒在地上,也不爬起来,反倒呵呵笑起来:“郑夫芫到死都不知道,是我怂恿的再勋,再勋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我随便挑拨几句,他就对皇后还有再阳心生恨意了。可怜郑夫芫为了这事儿,活生生病死了。还有我的四舅舅,被我骗到林子里,促成了他和白氏的好事。结果他到死还以为我是个好外甥女呢。”
徽予闭目:“毒妇”。他居高临下地蔑视着郎绮妘,从她的痛处戳下去:“你真是除了一张好脸,一无是处了。”他旋身走出去,“景安,赐鸩酒。”
“你要赐死我?”郎绮妘怒目圆睁,“我肚子里还有龙子!”
徽予的脚步一听,默然转回头来,蹲下-身扶住郎绮妘的肩,微笑道:“你不配生下朕的孩子。”景安没有多言,等徽予一起身,立刻招呼人上前按住昭充仪的肩。……
到了吃药的时候,愈宁蹑手蹑脚的进来,唤醒了迷迷瞪瞪的韫姜:“娘娘,该吃药了,和大人也过来把脉。”
“唔……”韫姜艰难地抬起了沉重的眼皮,“请和大人进来吧。”
韫姜已经油尽灯枯了,她的眼前总是披着层纱的,雾蒙蒙的。她努力地睁了睁眼,看清楚了来人。和如命竟在不知不觉间憔悴了这么多,想必是夜以继日的劳碌烦心,才致如此。
“多谢你了,和大人。”韫姜撑起一个微笑,“这么多年来,谢谢你了。本宫若是走了,你千万不要自责,是本宫的身子不争气,原不是你不用心的过错。”
和如命神情一动,慌忙低下头,生怕会让韫姜看到自己眼底的泪光:“是微臣无能。”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能活到现在,都是你的功劳。你的尽心尽力,我都看在眼里的。”韫姜喘了口气,声音细微下去,“和大人,永安、阳儿还有枫儿就拜托你好好照看了。除了你还有华大人,我都是不信的。”
和如命终于耐不住,红着眼、抬起头,哽咽道:“微臣定不负娘娘所托,微臣会尽我所能,照顾好公主还有殿下的。”他守了韫姜一辈子,对她的情谊从始至终没有说出口过,他不知道韫姜到底明不明白,但这样就好。
他真的还想让韫姜多活得久一点,哪怕她从始至终都只爱徽予而已。他只要看着韫姜,就心满意足了。
韫姜温柔的视线落在和如命的身上,她细声道:“请大人不要自责,我的命数至此了,没事的。此生,我也没什么遗憾了。”她微微一笑,“还是要谢谢你啊,和大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谢你的恩德,你若有所求,我一定答应你。”
和如命落下泪来,凄哽道:“微臣别无所求,只愿娘娘平安无虞。”韫姜眼中也滚了泪:“我的平安无虞,一半是皇上庇佑,还有一半就是你给的。”她看着和如命憔悴却清秀的脸,有一次无比郑重地说,“谢谢你,大人。”
每一次韫姜醒来,徽予几乎都会在身边,这次也不例外。徽予看她醒来了,忙柔声问她要不要喝水等话。韫姜摇摇头,徽予这才继续道:“你放心吧,郎氏和盛氏,朕都处置了。”他抚上韫姜清癯的脸颊,“婵杏倒是个忠心耿耿的,不过曾经伺候盛氏的太医温愉,倒吐了不少东西。朕已经下旨了,从今以后,不会再有盛家女入宫为妃。”
韫姜羽睫一颤:“你都知道了?”
徽予没有一点怒气,反而十分愧怍:“从前我一直要你懂事,要你隐忍,是我错了。我不该让你这样的,你如今病成这样,一大半的缘故都是心情郁闷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的心愿,我不会说一个不字。何况她们也是咎由自取,没什么的。”他的眼眶泛起红晕,“姜儿,你最近越睡越久了……”
回应他的先是沉重的呼吸声,韫姜缓了缓,才说:“对不起……”
徽予赶忙拦住她继续说下去,他强迫自己压住喷涌而出的悲伤,带上一份勉强的笑容:“姜儿,我命莳花局抓紧培植护养,你院子里的山茶花今儿开花了,我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你快点好起来,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赏花吧。”
韫姜努力地睁了睁眼,挽住徽予的手,微笑道:“我想现在去看看,好吗?”
徽予的笑容僵了一下,犹豫了片刻,他才柔声答应:“好,我叫愈宁姑姑进来为你更衣,我在外头等你。”
不知过了多久,徽予只站在明堂内,无声地望着院内各色的山茶,有宝珠山茶、还有花鹤翎等种种,叫人看了眼花缭乱。因为韫姜最喜欢山茶花,徽予便命人移植了世上最好的山茶种进未央宫里,供韫姜赏玩。
忽而听到了极轻柔的脚步声,徽予一回头,就见韫姜披着山茶红滚绣鸳鸯披风出来了,一晃神,仿佛是十余年前的样子,二人挽在一起,看冬日开的最早的那一蓬山茶花。
韫姜明艳而俏丽,拉着徽予穿梭在花丛中,一切都无比美好。
徽予搂着韫姜,小心翼翼地护着她,陪她慢步围走在花圃边。韫姜伸手折下一朵红艳的宝珠山茶,捏在手里,慢悠悠地转着圈。
回想到曾经,她坐在千秋上,手执着山茶花,给身后的徽予慢慢而幽扬地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她这一生,爱过也恨过,计算谋划着虚无的东西,盘算了一辈子,其实也不过是一场空。她所求的不过是徽予的爱,再阳和再枫的平安,还有安稳的日子,仅此而已。
不知已经过身的歆珩、夫芫、宛陵她们,临走前都在想什么,回望一生,是否追悔莫及,又是否死而无憾?
韫姜想,她虽然不舍,但没有遗憾了。
她有最孝顺而优秀的儿子,有爱她敬她的丈夫,还有彼此信赖的姐妹,这一生虽然磕磕碰碰、有时也无比悲伤,但不失为幸福完满的一生。
花儿落了,她的一生也终结了,但是这明城会继续光耀下去,会有不断如花般鲜活的女子进来,然后掉落……
呈乾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后傅氏崩势,追封为德裕皇后。
韫姜走了,日子还得过下去。
孩子们都过得极好,在韫姜薨逝后两年,徽予便立了再阳为皇太子,之后又亲自为再枫挑选了一门婚事,是一个极好的女孩儿,温婉多情,贤良聪慧,与再枫十分合得来。
而韫姜又答允了夫芫的,在临走前拜托了?诗她们,一定要为定城、寿城择一门好亲事,后来她们都嫁了很好的驸马。不是很显贵的豪门,但是都同驸马彼此情好,敬爱了一生。
再勋的事,徽予没有收回成命,但后来为他挑选了一位家室清明又贤良淑德的王妃,听说他和王妃十分恩爱,这都是后话了。
而后宫里的妃嫔,终究还只能留在明城里,度过她们的一生。韫姜、夫芫还有盛挽蕴的接连离世,让后宫一时没了主心骨。好在姝修容、婧贵嫔与容夫人还算明事,资历又深,徽予便命她们先暂领处理事务之权,并叫?诗和晴妃从旁学习。
没了姨母的庇佑,?诗也成长起来,她聪慧又恭顺,没有偏心谁的道理,很得徽予的心。很久之后?诗、晴妃分别晋为了淑妃与贤妃,彼此协助,成为了统领后宫的女人,但她们是否快乐,只得她们自己知道了。
至于和如命和徽延,他们是爱而不得的,一个谨遵韫姜临走前的嘱托,终身未娶,致力于照拂韫姜的孩子们;一个抱憾终身,终究难以平复,只得倾尽全力,辅佐、教养再阳,略以弥补此生的遗憾。他二人,都是再阳为帝之后,尊敬倚靠的人。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保护着再阳的安康。
徽予他没有一味沉浸在韫姜离世的悲伤之中,除了丈夫的身份,他还是一个皇帝,他还是得宵衣旰食,履行身为皇帝的职责,孤独地活下去。
徽予的勤政拖垮了他的身子,他刚过完四十九岁的万寿节没多久就病倒了,幸在届时再阳业已廿六岁,能力卓群,由他监国,再枫从旁协助,一切都没问题。
侍疾的事是?诗她们轮流着来的,这一日正到了徽予该吃药的时候,?诗便捧着晾好的汤药过来唤徽予。谁料徽予自己醒了,他望着架子床上遮的幔帐,喃喃地对?诗说:“朕梦到姜儿了。”
?诗一下眼眶一红,韫姜薨逝后,徽予很少在人前提起韫姜。但谁都知道,徽予此生忘不了韫姜了。他保留着未央宫的一切摆设,把未央宫的人都留在里头,叫他们每日擦洗未央宫的物什,照料未央宫的花草。他每天都会去坐一坐。
他的太平宫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殿内挂满了韫姜画的花草画,还有她的丹青,听江鹤说,徽予总会在很累的时候,抬头看一看那些丹青,或是望一望窗外的枇杷树,那样他就会畅怀些。
这么久了,徽予始终记挂、思念着韫姜。
?诗抹去眼泪:“皇上是想念姨母了。”
“朕觉得有了力气,你扶朕外头去看看。”有了这话,?诗赶忙招呼起来,徽予不要旁人搀扶,自己忽而有了一股精力,自己一步一步走向了殿外。
他少时读过一篇文章《项脊轩志》,里头有一句,他记得很清楚:“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院子里的枇杷树郁郁苍苍啊,也许是时候,该来找你了。
下辈子,还做夫妻吧。(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