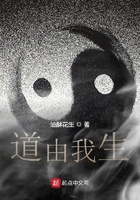打开门,打开灯。打开窗,我坐在藤椅上吹着夜风。
刺眼的白炽灯倾泻在书桌上的那个被折叠成四个方块的米黄色方格纸上,那是她留给我的诀别信,短短407个字,我看了无数遍,那句“我对谁都好”无数次刺痛我的心。信纸上印满我的泪痕和我无数个夜的哀鸣。我写了19封长长的回信,没有一封寄出去。不是寄不出去,而是不敢,我找了无数借口和理由却还是没有勇气迈出一步。翻开日记本,我已有一段时间没写日记了,最近的一次还是两星期前写的,内容如下:
1
还是会偷偷想念,只是再也不会打扰了
2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在微波荡漾里摇曳
我甘心做一只蜜蜂
在芬芳泗溢里飞舞
我甘心做一颗尘土
在融融春光里飘拂
我甘心做一粒沙砾
在无垠大漠里流泪
我甘心做一颗星星
在浩瀚银河里流浪
自我救赎自我迷茫
忘了征程忘了远方
3
你对我而言是唯一,我对你来说不过之一,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之一。爱只有零和全部,爱不是一点点的施舍,也不是一半的有所保留。
十分可笑,我不过在做独角戏,自导自演。
我拿出我最喜欢的那张被遗弃的唱片《八度空间》,装到陈旧的CD机里,发出与时代不符的“呲呲”的声响。播放我最喜欢的那首《半岛铁盒》,叮叮呤呤——“沦落而成美”。
信的结尾,是她留给我的十一个数字,我纠结了一整个夏天。
夏历八月既望,凌晨三点二十七。我昏昏然倒在床上,却毫无倦意。酒精麻痹的作用,我脑袋一片混沌,然而纵使我的每一毫升脑髓都被C2H5OH充斥,我的每一个神经元却还都是清醒理智且活蹦乱跳的。这是大脑告诉我的。我已不能动。我的身躯不由意志支配。我强迫自己做一个极其普通的动作以证明我仍然足够强大。我试着抬起我的左臂放至我的胸前,然而这对我来将却是极其困难,我不能做到把手放到胸前,首先是不能做到把手从侧身下抽出来——我侧身蜷缩在墙角,左臂压在身子下面,姿势想必是极丑的,反正感觉甚是不好。然而悲哀的是我无力改变这一窘迫的处镜,其缘由在于我的意志竟然不能支配我的行动。果然,存在决定思维。我又试着降低难度,然而我仍然做不到哪怕将手指头稍稍移动那么一点点,我甚至懒得眨一眨眼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并非我的意念不够强大,而是我太懒。可恶。我细细感受着时间一秒一秒地从我脑间大摇大摆嬉皮笑脸地走过,它们竟是那样狂妄,全然不顾及我的感受,以一种扭曲的诡异面孔存在——扭曲了的数字:03·29·58、0329·59、03·30·00……扭曲了的时间。莫不是说时间就是以数字的形式存在?那样的时间岂不是没有意义?原来时间的流逝也是早已被规划好的,这个世界不存在超前的时间,也不存在滞后的时间,甚至不存在于人无意义的时间,你去想时它便在,你不想它便不在,也就是说,时间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臆造并强行以数字化的,时间根本不存在!受制于机械数字的时间,想来可怜。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它,我恨透了狂妄的时间,真想将其俘获了来踩在脚底下,这样我便可安稳睡去。然而我抓不住时间,纵使抓住了也只不过是一堆数字罢了。我只能任由其在我的小小世界里撒野。更为残忍且过奋的是,他们偏偏行走的那样慢,硬生生将我尚存的一丝意志摧残折磨,直至消耗殆尽。我终于是睡去了,极其痛苦地。
我做了一个梦。
我的睡眠时间不足两小时,但我的梦却长达两个世纪。我生凭从没有做过这样清晰连贯且长的梦,我所记得的我的梦都是既短又模糊的,并且毫无故事性可言。但这次我遥远的梦境竟那么清晰。这短短两小时内我所做的梦弥补了我数十年来所有的空白之夜,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后半生的梦也都已在这一刻做毕。我不敢相信我仅睡了不足两个,但手机上的数字很明确地告诉我这个事实。
我开始彻底怀疑数字的真实性了,然而桌上闹钟的指针也以不同的姿势显现相同的寓意。
我起身下床,坐在书桌前,开始写第20封信:
一整个夏天,2/3的晴天,1/3的雨天,太阳最早可以在5:47就升起,最迟的一天则八点半以后还有余光在西山一角飘漾。整整一个夏季,三个月,九十来天,没有和你联系,没有你的消息。
我做了七十多个梦,都是关于你;有十几天彻夜未眠,也是在想你;还有几天的空白,留给时间冲淡。我不知道我何以一直都对数字那样在意,我做过的梦,到过的地方,甚至我抽烟的根数和打篮球的次数,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来。尤其是时间,我竟会记录得那样清楚详尽,精确到每一分钟。我想不明白那一个个刺眼的数字背后是什么,对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是否同我的过去的人生有某一种必然的联系?现在看来,不过躯壳罢了,毫无意义,甚至毫无可信度。
我决定不再相信数字了。
我又翻看了我的日记本,跳过那要命的数字和蹩脚的文字,我发现了一条从来不曾注意到的线索: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人生若只如初见;
快乐其实很简单;
生如夏花之绚烂;
七里香是最美的夏天;
愿你归来仍然少年;
当时只道是寻常;
欲说还休,天凉好个秋;
十一月的肖邦;
快乐只在回忆里;
放下;
放不下;
我是你的影子;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一场梦,我是一阵风;
相见时难别亦难;
长相思兮长向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这些都是我用来做文题的一两句诗词,从去年三月至今年七月,每月都有。当初是根据心情随意写下,现在想来倒也奇妙,完美契合。倘若我以后要写自传,定能以此为线索——我这两个半年的完美的情感线索。
我打算继续写些什么,但终究是没能写出来,看看桌上的闹钟,五点零一刻——暂且相信。
我给木槿发了条短信:
想见你。
随即就埋头睡去。没有紧张也没有期待,只想着一觉睡起来再说。
哪知不到一分钟,木槿就回了信息:
什么时候?
我惊讶,但同时也觉得合理。木槿就是木槿。这个世界上凌晨五点不睡的人怕只有我们两个了。
我回道:
天亮以后,老地方。
倒头安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