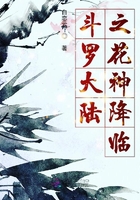在此,我想列举一些我曾处理过的劳资纠纷,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供劳资双方借鉴。
有一次,我们钢轨厂的高炉工人发表联名声明,宣称如果公司没有在周一下午4点前给他们加薪,他们就会罢工。而这些工人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要年底才到期,现在离年底还有好几个月。我觉得,如果有人毁约,那就不用再和他们续约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连夜坐火车从纽约出发,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工厂。
我请主管把3个部门的工人代表一起叫来——有高炉部门的代表,轧钢厂和吹炼厂的代表。他们都来了,我自然热情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这不只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一直喜欢和工人们相处。可以肯定地说,当你越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就越能感受到他们可贵的品德。这就好像巴里说起女人们一样:“勋爵一直以来把事情都做得非常好,只因为他把女性当作行动指南。”工人们也有各自的偏见和容易被激怒的事,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出自不知情,而非敌意。代表们全都摘下帽子在我面前围坐成一个半圆形,当然我也摘下了帽子,大家以非正式的聚会方式出席会议。
我对轧钢厂的工会主席说:
“麦凯先生(他是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先生),我们之间有一个协议,一直签到年底的,是吗?”
他慢悠悠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说道:
“是的,卡内基先生,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们毁约。”
“这不愧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骄傲。”
“约翰逊先生(他是吹炼部的工会主席),我们之间同样也有一份协议,是吗?”
约翰逊先生是一个瘦小的人,他非常慎重地说:
“卡内基先生,我在签每一份协议之前,都会认真仔细地读一遍。如果我认为不合理,我就不会签;如果我认为合理,我就会签,一旦签订了,我就会遵守协议。”
“这又是一位有自尊心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现在轮到高炉部门的工会主席了,这位爱尔兰人叫凯利,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凯利先生,我们之间也有一份要到今年年底才到期的协议,对吗?”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太清楚。他在一张纸上签过字,但没有仔细看,更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的主管琼斯上尉是位优秀的经理,但容易冲动。这时,他突然大声说道:
“凯利先生,你知道当时我读了两遍,并就协议上的内容和你一起讨论过!”
“冷静,冷静,上尉!凯利先生有权作出解释。我也在许多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字——那些文件是我们的律师和合伙人交给我的。凯利先生说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签的那份合同,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解释。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合约履行完,哪怕当时是在粗心的情况下签的,下一次签约的时候注意点就是了。你能不能再坚持4个月,等到这份合同期满,然后,在下一次签约时,你再仔细斟酌,提出自己的要求?”
他对此没有作出回答,我站起来说:
“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如果今天下午4点前你们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就会毁约,离开高炉岗位(这意味着灾祸)。现在还不到3点钟,但已经有答案了。你们可以离开高炉部。在公司对你们的威胁作出让步之前,高炉周围将长出杂草。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工人来说,最糟糕的一天就是自己毁约。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答复。”
工人们缓慢地陆续退出,留下来的合伙人都沉默不语。一位前来洽谈业务的陌生人进来时在过道上遇到了工会代表,他进来后告诉我们:
“我进来的时候,看见一位戴眼镜的人推了推旁边一位叫凯利的爱尔兰人,说道:‘你们这帮家伙,现在明白已经晚了吧,别想在这里玩什么花样。’”
那就意味着事情就此解决了。后来,从一位员工那里我听说了高炉部门后来发生的事情。凯利和委员会的代表回到工人们那里,工人们早就聚集在一起在等着他们。凯利走到熔炉边,冲着工人们大吼:
“回去干活,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都待在这儿干什么?见鬼,刚刚被这小个子的老板狠狠地训了一顿,他不会宣战,但他说会静观其变。真见鬼,快去干活,蠢货。”
爱尔兰人以及具有苏格兰与爱尔兰血统的人都有些古怪,一旦了解了他们,他们也是最容易相处的忠实伙伴。凯利以前是我们工厂最粗暴的人,后来他成了我忠实的朋友和崇拜者。我的体会是,你要永远相信大部分工人的所作所为是合乎情理的,只有他们的立场没有错,即使他们对领导的忠心是错误的,有时也让我们感到骄傲。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能为你做任何事情,他们需要的只是得到公正的对待。
有一次,我们的钢轨厂发生罢工,这次罢工的解决方式非常有趣。有一个部门的134名工人密谋联合起来,要求在年底加薪。然而,第二年经济非常不景气,全国其他钢铁制造厂都开始减薪。这些工人早在几个月前就暗地里商量如果不给他们加薪,他们就停工,并打算坚持到底。在我们的同行竞争者都在减薪时,我们肯定不能加薪,结果工厂停产了。其他部门的工人们也纷纷响应,随后一两天,高炉也停产,这让我们彻底陷入了僵局。
我赶到匹兹堡时,高炉已经熄火了,这是违反协议的。到达匹兹堡的当天上午,我打算见一见工人们,但厂里给我送来一封短信,说工人们已经离开高炉,他们明天再来见我。这就是在给我下马威!
我回复道:
“不行,他们绝对不能这样。告诉他们,我明天不在这里了。什么人都能停工,又玩这套花招。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回到工厂要求开工的,那时我会告诉他们我的决定:必须按照我们的产品价格来制定浮动工资,否则公司不会开工。这一标准至少连续执行3年,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再作出让步。他们已经强迫我们多次妥协,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让步。”
“现在,”我对合伙人说,“今天下午我就回纽约。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我得到工人们的回音,他们问,能否在我今天下午离开前过来见我。
我回答:“当然可以!”
他们来后,我对他们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在这里,他向你们保证过我会出面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件事,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还告诉你们,我不愿发生冲突,这也没错。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预言家。但他有一点想错了,他说我绝不敢与你们正面对抗。先生们,”我盯着班尼特先生的眼睛,举起紧握的拳头,“他忘了我是苏格兰人。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永远都不会和你们对抗。我知道有比和工人对抗更好的方法。我不对抗,但我能击败任何工会组织。除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一致通过要开工,否则工厂不会开工。就像我今天早上告诉你们的那样,工厂将开始实行浮动工资。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
他们退了出去。大约两周后,我在纽约的家里,仆人拿着一张拜帖进入我的书房,我发现拜帖上有两位工人以及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的名字。这几个人说他们是从匹兹堡的工厂过来的,想要见我。
“问一下这些先生,他们是不是关停熔炉、反对协议的高炉工。”
仆人回来说:“不是。”
“如果是那样的话,下去告诉他们,我欢迎他们上来。”
1910年,卡内基一家摄于芝加哥的钢铁厂外,右一是施瓦布,卡内基的得力干将。
他们受到了我真诚热情的接待,我们一起坐下聊起了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
“卡内基先生,我们此行是想来和您谈一谈厂里的事情。”这位绅士终于说到了此行的目的。
“哦,原来如此!”我回答,“工人们投票了吗?”
“没有。”他说。
我反驳道:
“那你们没有必要再和我谈这个问题。我说过除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投票一致通过要开工,否则免谈。你们从来没有到过纽约吧,那我带你们出去看看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然后1点30分回到这儿我们一起就餐。”
我们出去边逛边聊,无所不谈,除了那件他们最想谈的事情。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而且他们午餐也吃得非常愉快。这就是美国工人和别国工人之间最大的区别:美国人坐下来和其他人一起共进午餐时,他会把自己当作(因为他们普遍都是)一名绅士,举止得体。这是非常好的传统。
他们回到匹兹堡,不再提关于工厂的事。但不久,工人们就投票同意开工(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我又去了匹兹堡。我把拟定的浮动工资标准让工会委员会过目。浮动工资标准是根据产品的价格而定,这样,能让劳资双方成为真正的合伙人,利益均沾,风险共当。当然,我们也设定了一个底薪,以确保工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工人们对这些规定已经很清楚,无须对他们再多说什么。这时,工会主席说道:
“卡内基先生,我们接受全部条款。但是现在,”他有些犹豫了,“我们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很好,先生们,如果要求合理,我肯定答应。”
“嗯,是这样的,请您允许工会负责人来替工人们签这些合同。”
“为什么不允许呢?当然可以,先生们,对此我很高兴!同时我对你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们不要拒绝,就像我答应你们的一样。那就是工会负责人签完后,让每一位工人再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班尼特先生,这项规定要持续3年,时间比较久,有些工人,或者有很多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工会领导有权约束他们这么长的时间吗?如果工人们也有了自己的签名,那就不会有任何误会了。”
一片沉默。这时,班尼特先生身边有一名工人悄悄地对他说(我听得非常清楚):
“天哪,我们的计划被拆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