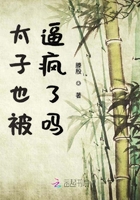出了风月楼,香儿来到一家药庄找了个大夫,说了下那人的情况,大夫说一起去看看吧,于是他们一起来到来风月楼的后院,那人散乱的头发盖住了脸,穿着脏兮兮的蓝色粗布衣衫,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夫把了脉,眼神有些奇怪,“这人看似有重伤,但脉象平稳有力,一点不碍事,我就开几个药方,你试试吧。”
那个躺着的男子也没看香儿一眼,就像睡着了一样。
又随着大夫又来到药庄,大夫开了几贴药和一个金创药,她拿了药来到了风月楼的后院。
“你房间在哪里?我弄药来了,这里不方便。”
那人又不理香儿,她又拍了拍他肩膀,“你干什么,你我都不认识,能给你看病都不错了,理都不理我。”
他斜眼张开一条缝看了看她,“在那个柴房。”指了指那个小破屋子。
“来我搀你进去。”
那人微微张开了双眸,站了起来有点不稳。
好高!这人比百里太尉还高,体格好像挺不错的样子……
走入了柴房,有一个木板床,上面铺着旧棉被,香儿把他搀扶到床上躺下。
“喏,给你自己涂。”香儿把金创药给了他。
这是一间放柴火的不算大的木房,仅有的几件摆设就是一个桌子和椅子,一个简单的木板床,一个旧衣柜,另一边放着堆到半墙高的柴火。格子花窗上的纸已破了好几个大洞,风从窗户中吹进来。
如果她住在这种屋子,也和他一样颓废吧。
不由地恻隐之心油然而生。
可他为什么会住这?而又不是男妓,这也太奇怪了,这体格到外面随便干个活不比在这好吗?
天生好奇心极强的香儿,决定把这事弄清楚。
那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突然笑了一下,“你在看什么?”
原来这冷峻的眸子也能散发出如此可爱的阳光,似乎觉得他不那么讨厌了。
“你就这样让我自己涂了?”
“那当然,你有手有脚,身长八尺,还要我涂吗?”
那人慵懒地坐了起来,原来前面都是在假装,他什么事都没有,打开金创药的小瓷瓶,脱下了外衣,露出了宽阔的胸膛,然后香儿就没敢再看他。
她走到屋外,点了个小炉子,把药放进去,放了点井水,拿着破扇子,扇着火,炉火发出阵阵浓烟,呛得她直咳嗽,眼泪都要熏出来了。
那人在里面竟然哈哈大笑,香儿一生气,走了进去,“你笑什么?”
“你是没点过火的富家千金吧,这也能呛到。”
她又不能说他们那从不用柴火,只用天然气,“不是,就是好久没点了!”
那人又在哈哈大笑,他衣衫也没怎么系好,可能涂了金创药系太牢了会黏住,白皙的胸膛若影若现。
让她怎么看!
只能侧对他说话,边上有块破抹布什么的,“你洗脸的布呢?”
“面巾那就是。”他指了指那块破布。
面巾还油面筋呢!
香儿拿起那块破布打了点水,浸湿递给那人,他竟然笑眯眯的看着香儿,她回过头去,翻了个白眼,继续扇着火,这次聪明点了,离的远了些……水开了,药也煎了一会了,拿了个碗和勺子递给他。
他接过了碗,抬了一下头,吹了一下,透过那水汽,看见了一张冷峻的脸庞。
与刚才那人似乎是两个人,目光依旧有些冷,但长的是真不错。浓密的眉,乌黑深邃的眼眸,透着冷冽的光芒,高挺的鼻,薄薄的嘴唇棱角分明,嘴角有一丝似有似无的微笑,神情是那么慵懒又带着几分放荡不羁。
那人喝完药,一抬头看了看香儿,发现她正在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笑着别过头去。
不好意思,对这种帅哥是没抵抗力的,多看不是她的错,总得找点话说吧。
“你叫什么名字?”
这么问是不是显得有点花痴,没办法,脸全是灰的时候真不想问他,看清了还真想问。
“独孤寒。”
“这名字真雅致。”
那人又抬头看了香儿一眼,四目交会,被他冷冷的目光又吓到了,这真的像一个职业杀手的眼神,目光中没有情感也没有留恋,像一座万年冰山一样寒冷。
“你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
那人又一抬头,像看笑话一样看她,“你觉得谁会愿意来这地方?这问题也太怪了,你又是怎么来的?”
“我吗?当然为了你懂的嘛……为了看看这里的男妓长什么样呗。”
“那看到了吗?有喜欢的吗?”他哈哈大笑起来。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你感觉特别奇特。你能和我说说,你怎么来这的吗?这不是开玩笑,我想知道啊,我不是这地方的人,不清楚这的事。”
那人用一种很异样的眼神看她,“我是被卖到这的。”
“谁把你卖到这的呢?”
“你又是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
“好吧,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是非知道不可。天色已暗了,我要回去了。”
“回你的深宅大院吗?小姐。”
“不是,是其他你想不到的地方。”香儿顺手给了他二十两银子,“明天他如果要打你,给他吧,明天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来,也许不会来了,这里没什么好玩的。”
“你当我是要饭的,还给你。”
“你不要就扔了吧,我不在乎,后会有期。”
香儿走出了风月楼,连个回头都没有,不想再看到那眼神,也许他在看她消失在人群中的身影吧。她一路上想着这人的奇怪眼神。
他长的是不错,但实在太冷傲,管他呢!这又不是她的谁。
街道染上一层夕阳金色的余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小贩们摆着小摊吆喝着,古色古香的小城变得如梦境中那般朦胧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