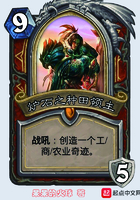沈婳循声往书院门口望去。
打西边升起的太阳比平常更加明亮耀眼,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漏到某人身上,他在金光闪闪里笑得俊逸非凡,笑得草长莺飞,笑得沈婳的毛笔掉到地上……。
见鬼!
居然是徐延珩!
沈婳脚下的方砖连碎几块。
徐延珩脚步雀跃,顶着一脸灿烂走过来,拾起地上毛笔,旁若无人地朝她道:“五妹妹,我帮你捡了笔。”
沈婳想一脚踩死他。
徐延珩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笑意更浓:“想不到竟有机会和五妹妹同窗砥励、舍傍书院。”
沈婳咬牙切齿地回望他:“世子,汾阳候府的梁远彰和梁秀琴也在,难道你也要跟他们同窗砥励、舍傍书院?”
徐延珩眼里兀地浮起杀气,却很快掩饰掉,把毛笔搁回笔架,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为见你,我才忍了汾阳候府的人。”
风过,青绫幕幢随风飘起,他的半边脸若隐若现,眉眼深情专注,难得一见的低姿态,这样的他,总让人不知不觉坠入回忆。
仿若回到前世,她曾是他捧在手心的宝、曾是他拿性命相许的妻……。
沈婳心口一疼,撇过脸去,目光正好对上一脸看戏表情的沈柏棠,她禁不住挑了挑眉,沈柏棠立马做出痛苦状,哧哧呻吟两声,四两拨千斤地道:“果真学海无涯,连延珩也到学院研学,既来了就赶紧坐下。”
说话间让出自己座位,让下人把自己抬去另一排的位置。
徐延珩闻言,理所当然坐了过去,两人一来一往就像早就预谋好的。
沈婳望着和自己并排而坐的徐延珩,眼里都是冷箭。
要是眼神能杀死人,徐延珩应该已经死了成千上万次!
但眼神是杀不死人的,故徐延珩隔着青绫幕幢道:“你刚才提及汾阳候府,可是担心我?”
“不曾。”沈婳淡声道:“我只是担心姓梁的跟你一旦动起手会累及书院,毕竟书院是将军府的地盘。”
徐延珩玩儿着自己桌上的砚台道:“你放心,我要弄死人也不会脏了将军府的院子。”
沈婳支着下颌,缓缓道:“巧了,你要弄死的人正好过来。”
梁远彰今儿穿了身绿衣服,绿油油的摆过来十分招摇,配着青绫幕幢当背景相得益彰,正虎着面皮对徐延珩道:“今天吹什么妖风,你不在瑾王府呆着,跑我跟前寻死。”
徐延珩十分大度地道:“你错怪于我,我只是来附近遛遛狗。”
梁远彰愕道:“狗?”
徐延珩道:“刚在我跟前张狂几声,如今不知去向,怕是代我寻了死。”
梁远彰方才意识到徐延珩是指桑骂槐,搙搙袖子正要干架,却听书院门口谈话声渐近,顾炎和一个头戴金冠的男子并排而行,此时进到书院,众人齐身向来人行礼:“见过太子、顾先生。”
一众人都弯得跟虾米似的,只有一人,随便弯了弯。
沈婳弯着虾米似的腰偷偷瞥了眼没怎么弯腰的徐延珩。
难得徐延珩没有看她,眼睛正朝着太子萧正的方向,眸光如刀,青筋盘腾。
不知道的还以为萧正杀了他全家!
知道的却以为,前世,徐延珩父母的死确实和萧正有天大的关系。
书院一众,也就沈婳一个知情人,就连徐延珩本人也应当不知道。
可他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沈婳出神的当口,萧正已落座,顾炎将手中卷轴放桌上,抚着长须道:“大家可知,太子侍读是个什么样的官职?”
梁远彰抢道:“我以为,太子侍读需刊缉经籍,掌修学史,以天下大义为已任。”
顾炎道:“文绉绉的,可有撸直舌头说话的?”
担架上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口无遮拦的沈柏棠:“太子一个人读书太闷太无聊,所以找人陪着解闷儿,陪的人不用多有才德,只是给太子做个伴罢,这便是太子侍读。”
顾炎顺着话道:“大家今天来书院,可是冲着来当太子侍读的?”
梁远彰又抢道:“从龙之臣,大家都盼着要做。”
顾炎继续抚着长须,目光却停在徐延珩身上:“世子,你也来当从龙之臣的?”
徐延珩嘴角动了动:“不是。”
顾炎悠悠地道:“那你来听我授讲。”
徐延珩依旧道:“不是。”
顾炎奇道:“那你是……。”
徐延珩道:“五妹妹近日避我不见,听闻她来书院研学,我为见她才来的。”
这话说的,也太实诚了!
咣当一声,有人不小心碰翻桌上墨砚。
又咣当一声,有人差点从椅子上摔下。
就连顾炎这只老狐狸也没绷住,目光定定望向沈婳。
沈婳垂着头,拿到手里的卷轴已被内力捻成粉,她是把徐延珩当卷轴捻的。
徐延珩,竟肆无忌惮到这等地步!
在这么多世家面前说,他为她而来。
虽说会稽城民风日益开放,可世家女子名声珍贵,岂容随意泼墨。
她不禁怒由心生。
梁远彰发出一声嘲笑:“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祖上连自己生的儿子也不认,难怪孙子辈孟浪至此。”
徐延珩略扫梁远彰一眼,一派的神态自若:“我无妻无妾从不染指女色,待五妹妹处处敬重,不过盼着见她一面,有何孟浪?”
稍息,整了整衣衫道:“倒是你,有妻有妾有暖床丫环,还要去强占良家民女,把人逼死了就往乱坟堆一丢,何止孟浪,简直是歹毒。”
梁远彰额上汗珠渗出,几年前他弄死个女人扔乱坟堆里,看着野狗撕裂女人的尸体,后来连骨头啃的没肉他才离开的。
事情做的天衣无缝,没人知道。
亲力亲为弄死人,尸骨也无存,徐延珩绝对不可能知道,梁远彰整了整气息道:“无凭无证,信口乱言。”
徐延珩道:“你弄死的人姓高,名如玉,远水镇缪村人,死的时候已有身孕。”
梁远彰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良久才道:“你……你……。”
徐延珩道:“我捡了那女人的白骨,改天就送到衙门去。”
梁远彰闻言两眼发直,已经面色苍白,他妹妹梁秀琴见状,提声喝道:“死无对证,世子说破嘴皮可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