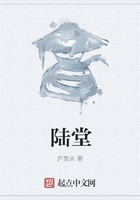正想着再戏耍下牧歌,突见牧歌身后遥远的山那头,浓烟翻滚。那不是刚才我过来的方向吗?我心里暗道不妙。赶紧给他解开穴道,二话没说,搂着他的腰一跃上了马背。
牧歌把我一把推开,惊慌道:“你想做什么?”
我指了指天边,用力的抽了马屁股,道:“牧场怕是出事了,我们赶紧回去看看。”
牧歌脸色一变,在我身前抓着缰绳,不在挣扎。我仅仅抱着他的腰,手感竟然如姑娘家一般柔软。
该不会是女儿身吧?想到他说话低沉有磁性,摇了摇头,应该是我多虑了。
马儿疾驰,风驰电掣,等离牧场近些,漫天浓烟,厮杀声与哭嚎声也越来越近。
等再近些,直跃眼前的画面惨不忍睹,一群穿着黑色盔甲的士兵拿着长刀和长矛如同杀小鸡一般屠杀着无辜的回民。帐篷被拆的支离破碎,熊熊大火从马场东边一直烧到西边。我大脑里突然浮现了林府被屠门的画面,那永不想回忆那一幕,而眼前的场景硬生生的让我联想起最不愿重见的一幕。
牧歌从马背上一跃而下,被我一把拉住。我捂住他的嘴,拉着他弯腰藏着一个草堆下面。
因为我看到了不远处,云鹤的头颅挂在高高的竹竿上,没有瞑目的双眼瞪着苍天。
张英杰俯趴在草地的一个坑里一动不动,两条胳膊却已不在身上,想来是死了。
牧歌瞳孔慢慢放大,嘴被我用力的捂住发不出声音,浑身僵硬,瑟瑟发抖。
这个半尺深的土坑,几有一丈方圆,本来是长满青草的地上,草和土应该是被飞旋的气流给刨起绞碎。
大坑附近的尸体七零八落,大多是双师镖局的人,死状惨烈,看得出临死前有过拼死抵抗。而靠近帐篷这边的被屠杀的回民尸体堆积成山,掩映在草丛里,分不出哪些是鲜血,哪是红色的草。
尸体烧焦的味道让人作呕,浓烟滚滚下,我已无法分辨里面是否有阿木兄妹两的尸体。
这还是人做的事吗?!除了柯宗,我再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惨无人道!
我竟一直小看了柯宗!张英杰是能进一等一的高手,云鹤作为武当关门大弟子,有着江湖名人录前十的实力。他们在柯宗面前,竟然死得如此没有尊严。
师傅鼎盛时期恐怕也达不到这个功力,我现在与柯宗正面交手,必死无疑!
稍远的地方,一个黑衣人从一个焦黑的帐篷出来,向一个马背上的穿着铠甲的头领汇报,他胯下的黑色坐骑异常雄伟,足有一人半高,马背上的人身材高大,带着头盔,浓烟遮挡,看不清脸。哪怕是隔这么远依然能够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杀气。
他就是柯宗!
新仇旧恨在身体里涌动,我却只能强忍愤怒与悲伤。
想来护送镖银的队伍已被屠杀殆尽了,几个黑衣人解开了辎重外面的绳索,逐箱开锁查验,亮晃晃的黄金隔着十几丈远依然刺眼夺目。
一个穿着锦衣缎子的公子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骑着一匹白马,拿着一柄长枪翻动检查着尸体,用手遮挡着口鼻,在这群人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他是谁,他在找谁呢?我余光看了一眼云歌,发现他贴在我身上,颤抖得更厉害。
公子哥找了一圈没有收获,骑着马到柯宗身边向他汇报,虽然隔得远,他好像对柯宗并没有毕恭毕敬。我默念不动明王心法,发挥六识神通的本领,距离太远,依稀听到“唐门”、“叛徒”、“黄金”几个字。
柯宗此次亲自带这么多人想来就是这批黄金,为了防止走露风声,杀了所有的人。听张英杰讲,黄金的目的地是卫辉,应该是与潞王有关。可这和唐门有什么关系?杀了地魔王左手剑不过才一盏茶的功夫,柯宗就赶到了。
我来不及思考其中缘由,因为贴着胸口的天魔铃慢慢变得炙热,如同火烧一般,我暗叫不妙。胸口快要被火烤熟一般,我实在忍不住,从怀里掏出天魔铃,却发现已是通体紫亮,发着如宝石一般的光亮。牧歌看着也惊呆了!
“叮叮”
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铃声,柯宗骑着马朝我们的方向走来,而我怀里的天魔铃蛇头上的铃铛也同时响起,似乎遥相呼应一般。
我的后背顿时汗毛倒数,惊得一身冷汗。在不走,只有死路一条!我自然拉着牧歌的手,幽冥步发挥到极致,向另一个方向飞逃而去,我的白马远远瞧见了,居然像是认得我,也跟着我跑。也不知跑了多远,我不敢停住脚,牧歌更不敢停住脚,两人脸已发青,汗珠已和黄豆差不多大。
天色已暗了,这一趟直跑了不少里路,快到莫说我,我想牧歌一生也没有一口气跑得这么远过。跑着跑着,只见前面有个破破烂烂的小木屋,我也不管里面有人没人,一头就冲了进去。
一冲进去,两人可忍不住全躺下了,喘气的声音,简直比牛还粗,我躺在牧歌怀里,他的心跳的声音像是在打鼓。
幸好这屋子果然没人,只见蜘蛛网不少,显然已有许久无人居住。
两人冲进来时,自然沾得满头满脸。我刚想去弄掉它,哪知牧歌一喘过气来,突然用力一推,几乎将我推得远远滚了出去。
我瞪起眼睛道:“我救了你命,你就这样谢我?”
牧歌脸红了红,道:“对……对不起,谢谢你。”
他说话的声音简直像是蚊子叫,连他自己都听不清。
“他叫柯宗,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莫说你害怕,就连我……连我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怕了她,还有谁不怕她……喂!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眨了眨眼睛,道:“你不会逃吧!”
牧歌道:“我为什么要逃?”
我大笑道:“我知道你不会逃的。”
牧歌果然没有逃,却提着个木桶走了进来。他脸上的傲气已全不见了,突然变得十分温柔,竟真的打水、洗碗,做了些男人不愿做的事,而且做得很仔细。
我向屋子里瞟了一眼,屋子里很黑,过了半晌,牧歌端了两碗水出来,满面笑容,道:“我已尝了尝,这水是甜的。”
我道:“我们喝水,马儿呢?它跑累了让它先喝吧。”
牧歌赶紧道:“不行不行,这……我只洗了两个干净碗,叫它拿桶喝吧。”将一只碗放到井边,一只碗交给我,飞也似地跑了回去。
牧歌眨了眨眼睛,笑道:“你喝呀,水真是甜的!”
我笑道:“我怕这井水有毒。”
牧歌咯咯笑道:“不……不会的,水里有毒的话,我已经被毒死了,我刚才已经喝了一碗,现在,我再喝一碗。”
他拿起井边的碗,一口气喝了下去。
我笑道:“你先喝,我就放心了。”
他喝了一碗,又是一碗,简直比马喝得还多。
天色更暗了,星星,已在草原上升起。
我面色突然大变,道:“不……不好!奇怪,我的头怎么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