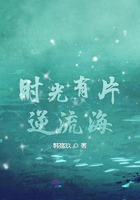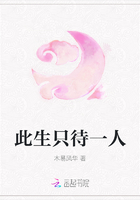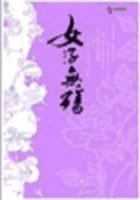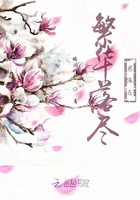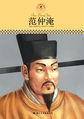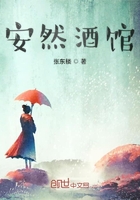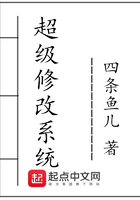明永乐初年,刚刚登基的成祖皇帝朱棣为了巩固政权,对前朝建文帝手下的诸臣残酷屠杀,大肆株连,旧朝老臣人人自危。没过多久,政权初固的朱棣便开始接连削藩,使得各地藩王如履薄冰。王侯将相一时间变得谨言慎行,守业克己,鞠躬尽瘁。然而应天府南门外的刑场上每天斩首的犯人却从不见少。
这日,一群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冲到了翰林侍读许羡安家,在一众妇孺的呼天抢地中抄了家,锁了满门老少。在清检人数时,却发现少了许羡安的幺女许司月,经查此女每年这时都会到城外三十里的清心庵祈福。
当一众锦衣卫赶到清心庵,许司月早已杳无踪迹,因着这是个女娃,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便无人费心去细细搜寻,总算给许家留下一条性命。这个女孩就是月娘。
陪着月娘进香的奶娘带着她星夜兼程,远离应天府,躲在自已乡下的长兄家,无奈长兄胆小怕事,生怕连累了家人,不断地催促奶娘报官自首。
奶娘把月娘自小奶大,又在灾荒年间受到侍读夫人的帮助,让奶娘的家人在饿殍遍地之时得以保全。忠义的奶娘自是不肯,又担心懦弱的兄长暗地里把她们的行踪上报,便再一次带着月娘出逃,投奔远在青州的表弟。
这一路颠沛流离,终是到了青州辖下的一个叫西峪的小村子。可天不遂人愿,在一个月之前,奶娘的表弟家竟起了一场无由大火,一家五口葬身火海,无一幸免。原本餐风宿露担惊受怕的生活已使奶娘身体羸弱不堪,又遭遇这等丧失亲人,无处安身的窘境,终是支撑不下,一病不起。两人此时身上的银钱所剩无几,寄居在村头的土地庙中,艰难度日。
奶娘病入膏肓,终是无药可治,撒手人寰。临终前千叮万嘱,要月娘隐姓埋名好好地活下去。此时的月娘小小年纪,孤身一人漂泊异乡,连安葬奶娘的钱都没有,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勇气。
毫无生意的月娘趴在奶娘身边哀哀啼哭,此时一个青年站在土地庙门口,高大的身影拦住了门外的阳光。
“姑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声音温暖和煦。
月娘回过头,朦胧泪眼中映入一个修长的身影,一步一步从庙门外的阳光中走进来,恍惚得宛若天神下凡。
脑中一片空白的月娘升起一丝警惕,她防备地盯着这个青年,心里猜测着这个人的企图。他出现得这样突兀,又在这个时节。这段时间,她看到太多人用垂涎的目光盯着这两个凄惨的女人,如今失了奶娘这个依靠,这些人怕是更是肆无忌惮。
那人走近,弯下腰来,一双弯弯的眉眼落入月娘的视线里,里面盛满了温柔与怜惜,那一刻,月娘毫不迟疑地相信,他一定是上天可怜她,派他来拯救她的。
他是个书生,帮助月娘葬了奶娘,便带月娘回到了他的家。自那天起,他一步一步走向月娘的一幕深深刻在月娘的心中,那一双充满温柔与怜惜的眼神总是出现在月娘的梦中。月娘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个仗义又温柔的书生。
书生无父无母,孑然一身,靠着在镇上当教书先生为生。月娘愈发觉得自已与书生同病相怜,她更加一心一意地照顾书生,希望书生发现自已的好。话本上不是都说:小女子感谢公子大恩,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
如果世事都如话本上的描写的那样,这是一个多么唯美的书生与落难姑娘的故事啊!可惜,书生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那个人不是月娘。月娘并不知道,她的爱情,只是她一个人的。
书生并不常在家,他住在镇上的学馆里。每次到了书生休沐时,月娘常到村口去等着他。远远地看到书生信步走来,月娘脸上的笑都发出光来。回到家,月娘张罗着照顾书生的饮食起居,虽然她常常笨手笨脚烧糊了她练习了好几天的饭菜,打翻了洗手的水盆,洗破了书生的衣服,可是书生从来没有责怪过她,只是无奈地笑笑,转身自已搞定。
偶尔书生也会有来访的朋友,这时月娘总是躲到自已的房间里,毕竟他们还没成亲,不好让人看到自已住在这里。想起这点,月娘心里就有些郁闷,书生为什么不向自已求亲呢?是自已做得还不够好吗?
很快,月娘就知道了原因。这一日,恰逢书生休沐,天将黑时,一个面色肃杀的黑衣人来敲门,月娘去开了门,黑衣人看到月娘愣了一下,点了点头,便向书生的房间走去。月娘觉得这个人很是无礼,粗鲁无状,又略带着点气势汹汹的样子,转而又担心起书生来,生怕这个人欺负了她的书生,便第一次悄悄地趴在书生门外的墙角偷听起来,她只听到了一句,便被那个肃杀的黑衣男人拎着衣领从墙角薅了出来,一掌劈向她的脑壳,书生从黑衣男子手中解救了她。月娘的脑壳没碎掉,但是她的心却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