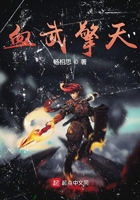罗仲和断鸿泰纵情饮酒的时候,王老虎、张怜民、弓正一行也在一处酒馆饮酒。
在富康街折了面子,王老虎一众像一群猛兽褪去兽的气焰变成一群小狗,在朱富贵面前柔软的摇尾乞怜。
而事与愿违,朱富贵肥硕的身躯本来慵懒的窝在椅子中。
王老虎屁滚尿流向朱贵诉苦时,看到精心打扮成猛兽的狼狗被竟揍回了原形。
一阵咆哮把他们一点残存的面子像罗仲笤帚下的灰尘一样扫了出去。
猛兽当的久了,谁愿意做回狗呢?
王老虎郁结满腹。
尤其富康街那些刁民在他挨揍时居然也沉默的羞辱他。
一阵阵的愤恨在这些猛兽心里像火星遇到干柴,越燃越旺。
要是换做平时早就纠结一帮家丁去富康街一阵打砸。
可是今天可不行,再遇到那尊瘟神,可就真没法在朱府混下去了。
夜色渐渐黑下来,王老虎几个愤愤难平,决定去饮酒释放一下。
于是避开了富康街找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酒馆。
要说酒是个好东西:
酒能让懦弱的人变成勇士,酒也能让该忘记的事像尿一样从身体中流出去。
但是,这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你不能一个人饮酒,你得一群人饮酒。
就像今夜的酒,王老虎和一众家丁的酒。
酒精中他们恢复了跋扈的神情,好像真的已经忘了白天被揍的鼻青脸肿的事。
酒馆中,王老虎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
惊走了一众食客,满坏了几个伙计。
愈是对他卑躬屈膝,王老虎愈加肆意张扬,顺民之不易可知一斑。
酒馆老板安静的站在几人身后,随时听候指示,不得已全程笑脸,心里苦楚难言。
酒确实是好东西,又不见得对谁都是好东西。
酒过三巡之后,夜色更浓,黑夜遮蔽的不仅仅是喧闹的文明镇,也在遮蔽人的内心。
群情激奋之中,谁还记得什么段鸿泰呢。
王老虎几个大摇大摆的走在文明镇,引吭高歌。
夜色动荡被冲击着它的广阔。
不管多大的喧闹,夜色都能将它们消融然后留在他们身后一阵寂静。
人都知道寂静的可怕,寂静勾起的也往往是恐惧。
王老虎它们一直在喧哗,在高喊,不觉走到一处偏僻处。
混沌中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几人停下来,摇摇摆摆的辨别回朱府的路。
在不远处,从一个拐角踉跄的走出一个人,他弯弯曲曲的走了过来。
王老虎趁着酒劲正要上前威风一番,忽然被张怜民拉住,撤回一面墙后面。
几个护院不知道什么事也跟着退回去。
王老虎大怒,刚要发作,张怜民悄声道:“王教头,你再仔细看看”。
王老虎把头伸出墙面,使劲摇头醒醒酒,定神看到那人背附一把刀跌跌撞撞的走着。
那人不是段鸿泰是谁。
王老虎猛的出了一身冷汗,真实冤家路窄啊。
喝了一壶烈酒,和罗仲分别后,段鸿泰觉得酒意上涌,头重脚轻,神志飘忽。
便想趁着夜凉出来吹吹风醒醒酒。
初来文明镇,段鸿泰也不认识路,只是浑身燥热,见胡同就拐,不觉走走远了。
想着不几日前去燕城拜聚龙会的码头,心中甚是得意。
尤其跟罗仲约好见义勇为一把,也算是豪举,宣扬一番,加入聚龙会当不是问题。
说不定能混个头目。
再说自己这把断弧刀也拿的出手。
越想越是酣畅,醉步蹒跚中竟走出了威风八面,好像人生新的一面正款款走来。
而王老虎几人看着段鸿泰得意的神情恨的牙痒痒。
白天的屈辱忽然在一瞬间的酒醒又燃了起来。
他扭头看着身后几个护院和家丁,眼中忽然狼光闪闪。
行至此处,忽然有个人档在了段鸿泰前面,叫了他一声“哎!”
“嗯?”段鸿泰含糊的应了一声。
抬头一看,迷迷糊糊的一睁眼,忽然一阵粉尘扑进眼睛。
“啊呀!”段鸿泰惊叫一声,烫的他眼泪直流。
正是王老虎一行,看到段鸿泰哀吼一声,低下头使劲的揉搓眼睛。
王老虎趁机一脚将段鸿泰踹翻在地。
几个家丁护院围上来便是一阵拳打脚踢,浑身的酒劲都在拳脚之间释放了出来。
猛兽的气势又回到了他们身上,一阵从未有过的酣畅让他们浑身的毛孔为之一张。
像一群不知疲倦的木捶使劲捶打着一头硕大的蒜。
他们要把它捶成碎块,再捶成粉末。
王老虎打的尤其卖力,段鸿泰嚎叫着满地打滚。
这杀猪般的惨叫更激的几人兴奋异常,拳脚更加大雨一样狂暴。
渐渐脚下的段鸿泰平静的像夜色一样没有了声息。
王老虎几个仍旧不尽兴的捶打一阵,浑身的酒意也都散发了出来。
良久,王老虎上气不接下气的蹲下来摸了摸段鸿泰的鼻息。
已经没有了呼吸。
王老虎使个眼色,吩咐张怜民几个把地上的血迹清理干净。
然后趁着夜色,把段鸿泰抬至镇外的一处荒地,挖个坑。
把段鸿泰扔了进去,草草掩埋了起来。
清理完毕,几人趁着夜色溜回到朱府,然后倒头便睡。
酒真是好东西,它能让该忘记的事像尿一样从身体中流出。
今夜之后,王老虎几个对此事决口不提。
仿佛从未有过这事,当夜他们也从未出过朱府,记忆像一滴水滴进了大海。
镇外的一处荒林清风习习,吹动树叶。
盛夏的夜空如此美丽,翻出的新土也发出阵阵清香。